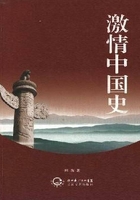引言
经学与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经学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儒家经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史书,如《尚书》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追述上古史迹的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汇集,时间从尧到春秋初年;《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亦是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对《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朱熹等人认为《左传》是史学,不是经学。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的确,《左传》保存的大量古代史料,对研究、了解先秦社会及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有人主张把它看作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把它当作所谓的“经书”。包括《左传》在内的中国“经书”、“经学”中确实包含了史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所以古文经学家以孔子为史学家,认为“六经”乃前代的史料,孔子只是将这些史料加以整理,故按照时代的早晚为序,即按《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排列为序。而今文经学家以孔子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六经”乃孔子作以教人之书,故“六经”的排列以其内容的深浅程度为序,即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为序。
在经学发展史上,有把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视为史籍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如隋王通最早在《中说·王道篇》提出,《书》、《诗》、《春秋》是圣人所述之史。宋代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明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大学微》都有经即是史的说法。王阳明《传习录》提出“五经皆史”的见解,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见解。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易教》、《经解》、《原道》等篇里,系统论述此说,认为六经不是圣人为垂教立法而故意编造的,而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职守专官的掌故记载,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文献,并指出六经皆器。这对于长期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的正统思想是一冲击。其后龚自珍的《古史钩沉》、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原经》,进一步发挥了六经皆史说。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认为六艺经传是对诸子学的发展,不把它当作史料看待,今文学之理想与史学之史迹有别,经学非史学所能取代。又认为经、史有着一定的联系,六经据旧史以为本,邹鲁之言史与儒家经学相关,三晋史学转化为经学之古文学。由此,蒙文通主张研究经学不能只研究六经,要从研究传记、经说中发掘其有价值的思想,如果只研究经典本身,那只是史料学及古文献学,而于经学的思想意蕴有所未及。以下仅就蒙文通关于经史关系的见解,而不是对他的史学思想本身加以探讨。
(一)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
蒙文通在学术研究中,主张经史分途而不可相混,对六经皆史之说提出批评。他说:
今世言今、古学之大本已乖,又何论于改制托古、六经皆史之谈。盖此二说者,文无征于古,义或爽于正,固未可依之以断义。惟一舍此末世之浮辞,守先师之遗训,考其家法,推其条例,以致其密,说虽难备,义尚有归。……古史奇闻,诸子为详,故训、谶、纬,驳文时见。比辑验之,则此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搜其散佚,譔其奇说,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经、史截分二途,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
蒙文通对清代今、古文学均提出批评,认为其大本已违反道理,故今文学的托古改制之说与古文学的六经皆史之说都有问题。此二说从文字来源上无有征于古,从义理上则违背于正理,所以不能依据六经皆史说和托古改制说来断义。主张舍弃这些末世的“浮辞”,而未认同六经皆史之说。并通过考察古史与六艺的区别,主张经、史分途,认为古史于诸子百家说中记载为详,并自成系统,较近于史实;而六艺所陈述的,则有较多的违忤之处,不免于迂隔。故蒙文通通过考察和搜集史料,指出儒家孔氏乃一家之言,在儒家六艺言说之外另有信史可稽,所以他主张把经、史分为两途,就像泾渭之不可相混一样。蒙文通还通过记述三方史说之异、自己学术思想发展的经过,来进一步批评六经皆史之说。他说:
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余旧撰《经学导言》,推论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翻不免于理想虚构;则六经皆史之谈,显非谛说。……至刘知几之《惑经》、《疑古》,更足征经、史之分途。晚近六经皆史之谈,既暗于史,尤病于史;似于刘氏所惑所疑,盖已了无疑沮,而于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更若存若亡;此六经皆史、托古改制两说之所不易明,而追寻今、古之家法,求晋、楚之师说,或有当也。……晋、楚之史,不与邹鲁同科。三系之说明,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
指出先秦时鲁、晋、楚三方史说存在着差异。三方称述之史说之所以存在着差异,是因为各家的思想有异。其中鲁人敦礼义,晋人崇功利,楚人好鬼神,故各地之学对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就晋、鲁、楚三方学术与史学的关系而言,三晋之学的正宗乃史学,即史学是晋学的正宗,而鲁人的六经之学和楚人的《天问》所陈述的,都不免有理想虚构的成分,而与史学之史实有别。就此而言,说鲁人的六经皆史,显然不是真实的道理。蒙文通并引刘知几《史通》的《惑经》篇和《疑古》篇以为同调,更加证明经、史之分途。认为晚清的六经皆史之说,是既不明于史,更有病于史;对于刘知几在《史通》中所惑所疑的经典之内容,似乎已无疑惑,然而对于孔子所传的微言大义,则更是若存若亡,无从把握。这正是六经皆史之说带来的迷惑而使人不易明了。由此,蒙文通主张追寻今、古文学的家法,求晋学、楚学的师说,认为这样则更为妥当。以分清鲁、晋、楚三方之学不同的特色,晋、楚之史与邹鲁的六经之学具有的区别。如果把鲁、晋、楚三系之说明白掌握之后,那么对古史也就大略掌握而可探求了。蒙文通得出的结论是,在儒家言说之外,显然有不同于儒家的史说存在。既然史说可不依赖于儒学而独立存在,故儒家经学与史学分为二途。
在其晚年代表作《孔子和今文学》中,蒙文通强调,六艺经传是对诸子思想的发展,不要把它当作史料看待。这表明在蒙文通看来,经、史是有区别的。他说:
其他各家重在理论的创树而忽视传统文献,儒家则既重理论又重文献,诸子以创树理论为经,儒家则以传统文献为经,只有明确了这种先秦诸子发展的情况,才能把握对汉代经学(主要指今文学,下同)的认识。认识了“六艺经传”是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才不会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在肯定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后,再来分析经学家所讲的礼制,才能看出这些礼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明确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再结合诸子学派作“经”的事来看经师们所传的六经,就可知道六经虽是旧史,但经学家不可能丝毫不动地把旧史全盘接受下来,必然要删去旧史中和新的思想体系相矛盾扞格的部分,这样才能经传自相吻合。
指出儒家既重理论又重文献,把理论和文献二者结合起来,而诸子则只重理论而忽视传统文献,这体现了儒家区别于诸子的特色。认为只有明确了这种先秦时期儒家与诸子发展的情况,才能把握对汉代今文经学的认识。而只有明白了儒家汲取了诸子思想,较诸子百家更为全面,“六艺经传”是对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它的思想体系,而不至于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可见六艺经传不同于一般史料,它是汲取了诸子思想之长,而对传统经典——六经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汲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同时也汲取别家的“经”说,以充实自己。儒家经师所传之六经与百家说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可知六经虽是以往流传下来的文献,具有旧史的成分,但经学家并非全盘照搬照抄以往的旧史,而是要删去旧史中与经学新思想相矛盾的部分,这样才能使经传吻合,而寻得六艺经传中的道。使儒学经说汲取诸子百家之长而得以大盛,在理论上较各家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