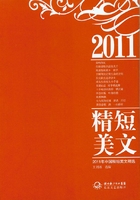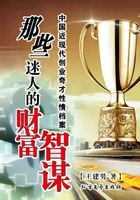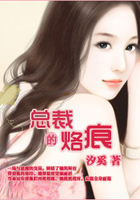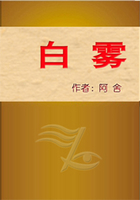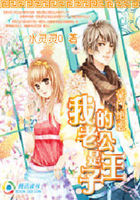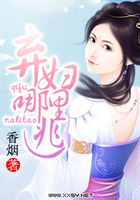指出明堂、辟雍、封禅、巡狩等项制度,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制度。它们在汉武帝时还可以向朝廷提出,但由于这些制度与封建王朝的现行制度发生矛盾,提出者往往遭到厄运,如眭孟、盖宽饶、赵绾、王臧、河间献王等人,他们为提倡禅让或提出明堂议政,要么被诛,要么自刭,要么被忌妒,抑郁而死。所以到了刘歆所在的哀帝时,辟雍、封禅、巡狩之仪,便“幽冥而莫知其原”了。表明这些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制度受到统治者的压制,至西汉末的哀帝时已不传,而莫知其原了。蒙文通客观地指出今文学理想的制度与当时西汉统治者现行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包括井田制与当时的豪强兼并相矛盾,辟雍选贤与当时的任子制相矛盾,封禅、禅让与当时的家天下相矛盾,巡狩、大射选诸侯与当时的以恩泽封侯相矛盾,明堂议政与专制独裁相矛盾。所以说今文学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反抗现实的意识形态,但又不便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反抗纲领,而是托之于古圣先贤,以避难免祸,减轻压力。这样一来,理想的政治制度便和真实的历史陈迹形成一定的背离,今文学者依托古圣先贤的典籍灌注自己的思想,寄托了整套理想制度,把经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到了后来,不仅今文学的这些理想制度不得其传,“而莫知其原”,而且“在东汉中叶以后今文学也就逐渐衰微而终于湮灭了”,整个今文经学也逐渐走向衰落,而为其他的学术思潮所代替。
(四)对董仲舒的批评
蒙文通对西汉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批评主要涉及“革命”说、“改制”论、“易姓受命”,及井田、限田等政治领域,故将其对董仲舒的批评放在“经学与政治”章节下来讨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文通经学思想的特点。
在《孔子和今文学》中,蒙文通对董仲舒作了较为严厉的批评,认为董仲舒使今文学变了质,这种变质了的儒学成为专制帝王的工具。他说:
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但“汤、武革命”,岂非今文学一大义吗?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
文中提到的“曲学阿世”的儒者,包括公孙弘和董仲舒。公孙弘(前200—前121)60岁时作为贤良推举征为博士。因出使匈奴,不合武帝之意,被免职。元光五年(前130),征贤良文学,公孙弘再次被推举,对策者百余人,被武帝拔为第一,拜博士。是汉代第一个以儒学家身份拜丞相、封侯的人。为官用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常屈奉顺承汉武帝之意,深得武帝欢心。他提议为经学博士置弟子员,对汉代儒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为人多忌,外宽内深,凡与他发生隔阂的人,总要暗中报复,曾被汲黯公开指斥“多诈而无情”,表面上却是一片和善。杀主父偃,贬徙董仲舒,都是公孙弘报复的结果。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则与公孙弘有别,董主要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而不像公孙弘那样倾向于政客。董仲舒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为博士,其学以儒家为主,结合阴阳五行说。注重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和宣传《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改制、易正朔、作新王,主张行儒术,讲仁政,“限民名田,以谵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思想不少被汉武帝采纳,从而使今文“公羊学”成为显学。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表彰六经、独尊儒术的建议,被统治者所接受,这在中国经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使儒家经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而由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到汉初的重黄老之学,再到儒术独尊,完成了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的重大转向,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理由。蒙文通以往在作《儒学五论》时,对西汉今文经学曾给以较高评价,认为“先汉经说”“优于孟、荀”,定“百世楷模”,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充分肯定西汉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此时(作《孔子和今文学》时),则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提出较为严厉的批判。认为董仲舒将儒学的“革命”改为“改制”,把井田改为限田,又于“禅让”说未能坚持,把儒家限制君权、与封建专制君主不相容的思想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因此,蒙文通认为“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儒学成为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修改与曲解之后,变了质的儒学,所以被专制帝王所接受并加以利用。进而,今文经学分为讲微言大义、阴阳五行、谶纬的内学,和讲“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章句训诂的外学,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没了。更有甚者,到了后来,今文经学成为御用品,实不足道。他说:
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这就无怪乎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所以像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那些坚决斗争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这种高压之下,一部分人变节,放弃了主张,入于利禄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公开讲的是表面一套,秘密讲的才是真的一套。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内学”。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便成为后代纬书(不是谶记)的来源。在博士官的学者,就入到“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章句之学。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没了。到石渠、白虎两次会议,专论礼制,由皇帝称制临决以后,就成为御用品了。这种儒学本是不足道的。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
蒙文通批评董仲舒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斗争性,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认为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由此能被汉武帝接受并加以推崇。然而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仍有对封建统治者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成分,这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儒家道统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从道不从君”,即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以道对封建君权加以限制。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这一传统,提出天遣说和“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天遣说是董仲舒提出的对君主的失道行为加以约束的一种思想,他认为,天是一种超人间的支配力量,君权乃由天授,天生民以立君,天与人事有着必然的联系。指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即上天对统治者,经常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变化来进行谴责,以示警告,使其改正错误,符合天意。天遣说把本不相干的自然灾变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虽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但在当时君权至上的时代,以天灾来警告统治者的失职行为,在君权之上树立起天的权威,至少是对封建君主的一种约束。董仲舒还继承了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思想,提出“有道伐无道”的变革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变革,起支配作用的是道,有道之圣人伐无道之暴君,由此推动了历史的变革和发展,并将此称之为天理。他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强调“有道伐无道”,凡无道之君被有道之人所取代,这就是天理,即天经地义的事,其所从来已久,而不仅仅是汤、武所为。也就是说,道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原则,社会变革的动因在于统治者是否有道。正因为夏桀王和殷纣王无道,被汤王和武王革其命;秦始皇无道,被汉所取代,完成了改朝换代和易姓革命。董仲舒不同意把汤武革命称为“不义”的观点,他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以对民的态度来区分圣君和暴君,认为残害民众的桀、纣是“残贼”、“一夫”,人人可得而诛之。汤、武讨伐之,是有道伐无道,这即是天理,是顺天应人之举。从董仲舒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以是否有道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居于君主之位作为是非的标准。这与孟子盛赞汤、武伐桀、纣,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比较接近,体现了儒家道统思想限制封建君权的基本出发点。从董仲舒的天遣说和“有道伐无道”的思想不难看出,他对封建君权还是要加以限制的,他认为,正因为夏桀王、殷纣王无道,故被有道的商汤王、周武王诛伐,这体现了天理。蒙文通对董仲舒的批评,尚有可议之处。蒙文通说:“自董仲舒出来以后,变素王为王鲁,变革命为改制,变井田为限田,以取媚于武帝,又高唱‘《春秋》大一统’以尊崇王室,因而搅乱了今文学思想。”认为:“董仲舒的今文学,已经是被阉割了的学说。于此然后知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并不是偶然的。”甚至认为董仲舒“变节”,导致学术阵营的混乱,更增加了后人对西汉今文经学了解的困难。如此用“取媚”、“阉割”、“变节”等字眼来表达董仲舒的今文经说乃变质了的儒学,这与他本人先前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较高评价形成对照。体现了蒙文通经学思想至晚年的变化。这与当时的时代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术思想的政治色彩相关。
蒙文通批评董仲舒放弃了儒学的“革命”说,变“革命”为“改制”,这是值得商榷的。董仲舒不仅提出“有道伐无道”的思想,而且主张“易姓而王”,盛赞汤武革命,这不能说董仲舒未能坚持“革命”说。董仲舒明确指出:
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甫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
董仲舒认为,德如尧、舜,易姓而王者有七十二位到泰山封禅,表明他对“易姓而王”的肯定。他把王位的获得或失去归结为天命,虽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但毕竟在王之上树立起“天”的最高权威,这是对君权的限制。他盛赞汤、武讨伐桀、纣的革命行为,反对将汤武革命称之为“不义”的观点。他反驳说,如果将汤、武伐桀、纣称为不义,那岂不是把德如尧、舜的七十二王都视为“不义”,因“七十二王亦有伐也”。从这里也可看出,董仲舒对“易姓而王”的汤武革命的肯定。
蒙文通之所以批评董仲舒,除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外,与他对齐、鲁学派的划分及评价有关。他认为,鲁学为孔孟正宗、孔学嫡传,齐学则与鲁学存在着差异,齐学虽与邹鲁为近,但齐学已离失道本。他主张通过探明地域流传的儒学流派,来推本邹、鲁正学之宗以明道,修正齐、晋派及受其影响的汉人之今、古文经学“离失道本”的偏差。他说:
孟子是邹鲁的嫡派,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发明的,《孟子》和《穀梁传》这两部书,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孟子以后还有两个大儒,便是荀子、董子。荀子是三晋派的学问大家,董子又是齐派的大家,他们是齐、晋派里面讲孔学的特出者,但是于道之大源不免见得不很明白,便也是齐、晋两派不及邹鲁嫡派的地方。汉人的今文学是齐派占势力,古文学是晋派占势力,孔学的真义自然是表现不出来的了。也和《左传》、《公羊》杂取霸制,不及《穀梁》独得王道的一样。今文派是主《公羊》,古文派是主《左传》,这哪里还见得出什么王道来!
认为董仲舒是齐派的大家,汉代的今文经学是齐派占势力,表现不出孔学的真义,不及邹鲁嫡派。并指出汉代的今文学是主《公羊》,而古文学则主《左传》,但不论是主《公羊》的齐派今文学,还是主《左传》的晋派古文学,它们都未能见得王道。从总体上对董仲舒的齐派今文学评价不高,甚至认为“以董仲舒作为论述西汉今文学的代表是绝对不妥当的”。这与学术界把董仲舒视为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的见解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