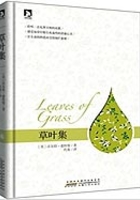蒙文通把禅让与巡狩联系起来,认为今文学家既主张选天下之贤人来禅以帝位,又主张选贤以为诸侯,强调天子和诸侯都须选贤人以任之。并提出对诸侯加以黜陟,而黜陟诸侯则体现在巡狩述职的制度中。然对诸侯的惩奖制度——黜陟,在巡狩的本义中则无,是后来的今文学家提出的。蒙文通对《礼记·王制》作了具体考察,指出《王制》关于巡狩的记述,是君在巡历的过程中,通过“观民风”,“观民之所好恶”,对不敬者“削以地”,对不孝者“黜以爵”,而对变易礼乐和革制度衣服者加以处分,以示贬黜。但对那些“有功德于民”的诸侯则“加地进律”,即加地进爵,以示褒奖。蒙文通认为,《王制》显然是把巡狩的主要作用视为是黜陟诸侯。并在《尚书大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通过对《白虎通义·巡狩》篇的考察,蒙文通认为该篇讲五岁一巡狩,“二伯出述职黜陟”,“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表明《白虎通义·巡狩》是把述职作为黜陟诸侯的制度。这与《孟子》一书的讲法迥然不同,因《孟子》书所载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其巡狩根本没有黜陟诸侯的意思,而述职乃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不像《白虎通》有关述职的说法。蒙文通指出,尽管《白虎通》还有以功德来黜陟升迁诸侯的办法,但这些黜陟的办法,都没有任何史实为依据,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与《孟子》等书所载关于巡狩的史实不符。今文学者在阐发巡狩之义时,加进了自己的理想,主张选贤任能以立诸侯,并对诸侯进行考察,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爵,而不敬不孝者则削地绌爵,在尚贤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选贤和黜陟,使今文学的理想更趋完密。
5.明堂
所谓明堂,指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古乐府《木兰诗》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清惠栋曾撰《明堂大道录》,八卷,叙述明堂制度的内容及其变迁,可供参考,此书收入《皇清经解续编》。而蒙文通则以明堂为大学,认为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宫。他说:“明堂,大学,一也。颖容、贾、服并同此说。东汉以来纷纷争议者,惟五室、九室事,何其陋耶!……夫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也。”认为明堂即大学,而不必局限、拘泥于《考工记》以来周人五室、九室之制的争论。蒙文通指出,东汉学者颖容、贾逵、服虔都称明堂就是大学,即天子国学。而东汉以来的学者在讨论明堂时常常总是纠缠在五室、九室,即五间或九间房子的争论上,而没有注意到明堂大学这一制度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就此,他指出:
从赵绾、王臧和河间献王的事看来,明堂制度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汉书·儒林传》载:汉武帝初即位,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请立明堂,……太皇窦太后……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献王对答武帝的内容,就是指的明堂制度,这就使我们知道,赵绾、王臧以请立明堂而被杀,河间献王也因畅谈明堂制度遭到忌妒而抑郁以死。这不是正显示出明堂制度含有与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政治意义吗?
蒙文通以赵绾、王臧和河间献王的事例来说明明堂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汉武帝初即位时,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两人都是著名今文学家申公的弟子。赵绾、王臧请设立明堂以朝诸侯,由于不能成其事,便称及其师乃申公。于是武帝派使者驾驷以迎申公。申公来后,武帝问治乱之事,此时申公已八十余岁,不受武帝重视。然既已招致,便拜为太中大夫,议明堂事。其时,窦太后喜黄老之学,不喜儒术。她抓住赵绾、王臧的过失,以责武帝。武帝因此而废明堂事,乃罢逐赵绾、王臧。后二人被窦太后逼迫自杀。这是为“请立明堂”而献身。另一为明堂之事而遭不幸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刘德好儒学,罗致山东诸儒,好收藏典籍,《汉书·河间献王传》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武帝时,刘德入朝,被服造次、言谈举止必合于仁义。武帝问以五策,刘德应对自如,对答无穷,其对答的内容包括明堂制度。武帝出于忌妒,恼怒作色而难之,对献王说,商汤王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取代了夏桀、殷纣),你可努力去做。献王知道了武帝的心思,返归后,便纵酒听乐,抑郁而死。蒙文通盛赞赵绾、王臧以明堂而死,河间献王以明堂而废,认为这正显示出明堂制度含有与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政治意义。这个与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政治意义就体现在,今文学理想的明堂大学与周代的明堂大学不同,今文学理想的明堂大学是议政的场所,可议论国政,而周代的明堂大学只不过是贵族子弟的学校。他说:
孟子曰:“民为贵。”无明堂,则民贵徒虚说也。儒者舍《尚书》四郊明堂不敢议,而徒争《考工记》以来周人五室、九室之制,故论益多而义益晦。是不解有周之明堂大学,有儒家所设想之明堂大学,二者固区以别也。《王制》、《公羊》言:“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然则明堂即大学,正诸侯贡士之所萃,布政于是,谳囚于是,师出而献俘亦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是,天子袒而割牲,父事三老以为孝,兄事五更以为弟,上观下听皆于是,则“民为贵”之实备矣。教中失,谏王恶,天子恒规规焉不能有所逾,而听政于众庶,则绾、臧以议明堂诛,献王以对雍宫废,岂虚也哉!
指出明堂大学有周代之明堂大学与今文学所设想的明堂大学的区别,不必纠缠于周人所谓的五室、九室之制。他引《王制》、《公羊》所言,断定“明堂即大学”,乃诸侯贡士荟萃的布政之所,朝廷及国家大事均在此办理,并指谪朝中之阙失,劝谏君主之过错,即使是天子也不能有所逾越,而需听政于众庶。认为孟子“民为贵”的思想正是通过明堂议政而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了明堂,“则民贵徒虚说也”。对明堂议政的政治意义给予较高评价。他说:
今文学家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在“明堂议政”这一点。在论述“辟雍”段中, 我们曾指出过周代的大学和今文学家理想的大学不同。周的大学是一群贵族子弟的学校,所谓大学议政,只不过是贵族子弟的课程实习而已。今文学理想的大学则不然,它已经不完全是贵族子弟的学校了,渗入了从王朝领地和诸侯领地所选送来的大量的秀选之士,……今文学家所称颂的接受禅让的天子既曰虞舜,……是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者。这样,从天子以至太学生,都是来自畎亩之中,同在明堂议政,这种理想就很高了。根据典籍记载,天子朝诸侯是在明堂,颁布政令是在明堂,养老尊贤是在明堂,而断狱、献俘也在明堂,王朝的国家大事几乎完全集中在明堂了。而今文学家偏偏要想在这样的场合来议论国政,而又适遇雄才大略的专制君王——汉武帝,赵绾、王臧怎么会不招致杀身之祸,河间献王又怎么不招致忌妒呢?
蒙文通指出,今文学家之所以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是在于“明堂议政”这一点。他把明堂与辟雍、禅让联系起来,认为辟雍是讲教育平等,不分贵贱、平等地受教育,庶民子弟优异者也可以保送到天子的大学里去。而今文学提倡的禅让,是选虞舜这样的贤者为天子。如此,通过禅让和辟雍来的天子和太学生都出自田间,他们同在明堂议政,自然这种理想就很高了。在明堂之上,天子会见诸侯,颁布政令,而明堂又是养老尊贤之所,断狱、献俘也在明堂,几乎国家大事都集中在明堂办理,可见明堂的重要性。虽然今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并不相符,但这种“明堂议政”的思想与当时封建专制的一言堂相矛盾,体现了儒家评政议政的传统,是值得称道的。他说:“在古代氏族社会时代,凡氏族中比较重大的事件都须交付氏族全体会议讨论。《诗经》所说‘询于刍荛’,《尚书》所说‘谋及庶人’,可能就是这一制度的遗迹。《尚书·盘庚上》记殷王盘庚迁殷就曾‘命众悉至于庭’而反复告诫。《孟子·梁惠王》记周太王去豳也是‘属其耆老’而说明道理。”蒙文通从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孟子》书所引述的关于“询于刍荛”、“谋及庶人”等记载,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发端,也是今文学明堂议政思想的重要渊源。汉代今文学者加以阐发,在当时具有时代意义。
蒙文通通过对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几项制度的分析,以探讨今文学的理想政治,并从总体上加以概括,指出今文学的思想是反抗现实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经学与政治的结合。到后来则遭到统治者的压制而不传。他说:
《史记·封禅书》载:武帝时,“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绾、臧自杀”。《汉书·刘歆传》载哀帝时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可见明堂、辟雍、封禅、巡狩等制度,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制度,是儒生讲论的重要内容,在武帝时都还能向王朝提出,而到哀帝时便“幽冥而莫知其原”了。……我们再就各项理想制度与汉王朝的现行制度对比起来看,就更明显:井田制度和当时的豪强兼并相矛盾,辟雍选贤和当时的任子为郎相矛盾,封禅禅让和当时家天下传子相矛盾,大射选诸侯和当时以恩泽封侯相矛盾,明堂议政和当时的专制独裁相矛盾,像这样处处与时代相矛盾的制度,正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当时的儒者又不敢鲜明地提出来作为反抗纲领,而托之于古圣先贤以避难免祸。这样做虽可使理想制度不至遭到扼杀,但却无法避免要和真实的历史陈迹在某些部分发生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