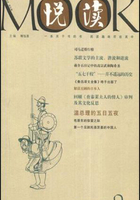引言
儒学的产生早于经学,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儒家学者根据这些经典及解释经典的传记,逐步形成了经学。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对这个过程,蒙文通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在周秦之际,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汲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经说荟集诸子说以为经术之中心,汲取诸子百家之长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使得经学大盛。所以蒙文通强调,六经与百家相得益彰,经学与诸子学不得脱离,离之则两伤。尽管蒙文通一定程度地肯定诸子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与经学相比,蒙文通认为,儒家经学的影响远超过诸子,包括诸子在内的子、史、文艺等学,都是不可与经学相抗衡的。认为经学是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渗透到思想行为、政治风习等各个方面,对儒家经学予以充分肯定。并批评近代以来以西学之学科分类来衡量经学,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力量和巨大成就的现象。
(一)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
先秦时儒学只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是与诸子百家展开争鸣,以求被用于世。诸子百家,其说各异,它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愿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世变持不同的见解,并提出不同的治世之道。从中国文化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各家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有机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文通认为周秦时期,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相互融合。他说:“周秦之际,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邹生晨曦谓:‘《庄书》有诋詈孔氏者,为漆园之本义。《杂篇》中乃颇有推揖孔氏者,为后来之学,有取于儒家。’亦笃论耶!”蒙文通列举战国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韩非虽集法家之大成,但他也汲取了道家的南面之术,也不仅仅是儒学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作为战国末儒家著名人物,他也明显汲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融儒、道、法于一体。即使拿《庄子》一书来说,其书中既有批评孔子儒家之处(这应是《庄子》书的本义),但《庄子》之《杂篇》又有推崇孔子的地方,这是其后学受儒学影响,有取于儒家之处。这表现出儒、道、法等各家在当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情形。不仅如此,儒家还受到墨家的影响,儒、墨、法各家均有所长,儒家汲取诸家,而使自己的学说恢宏卓绝,日趋精密。他说:
周秦间原为诸子学术最发达之时,……《韩非子》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试详究之,知儒之分为八者,正以儒与九流百家之学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法,或取之墨,故分裂而为八耳。先秦晚期各派,法家、道家皆与他派相出入,韩非、庄子尤为显著。儒家之事,正亦如此。汉代经师有法殷、法夏之说,继周损益,二代孰宜,于此不免自为矛盾。及究论之,法家自托于从殷,儒之言法殷者为《春秋》家,实取法家以为义也;墨家自托于法夏,儒之言法夏者为《礼》家,实取墨家以为义也。儒家原为从周,故孔、孟皆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始主于扩张君权,墨家欲选天子,庶人议政,入于民治思想。自儒兼取墨法之义,而理义之恢宏卓绝为不可企及;其人生哲学亦显有取于道家,而义亦益趋于精致。
指出周秦间是诸子学术最发达的时期,而《韩非子》所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儒家与诸子百家之学相激相荡,左右采获,要么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并取之于墨家,由于儒学所取之于道、法、墨等各家学说的不同,受到诸子学的不同影响,使儒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与先前之儒学有不同,所以儒分裂为八派。到了先秦的晚期,法家、道家等各派皆与其他学派相出入,而以法家的韩非和道家的庄子更为显著。儒家也正是如此,在与各家的出入互采中,得以发展。比如就法殷、法夏,继周损益而言,儒家就汲取了法家、墨家的思想。蒙文通认为,在儒家之中,有法殷的《春秋》家,有法夏的《礼》家。其法殷的《春秋》家就是汲取了法家的思想,而法夏的《礼》家,则是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认为儒家原本从周,希望恢复以“周礼”为准则的社会秩序,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社会规范,所以孔、孟儒家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主张扩张君权,用赏罚、法令来控制人民;墨家则反对贵族世袭制,主张有能则举之,甚至连天子也不应世袭,而应由选贤产生,并主张庶人议政,提倡民治。蒙文通认为,自儒家在与诸子的争鸣中,兼取了墨家、法家之义,使得自己的思想理义达到了“恢宏卓绝”的地步而不可企及。就拿儒家的人生哲学来说,也有明显汲取道家思想之处,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安时而处顺”人生观相结合,使其义也更趋精致。儒学在与诸子百家的相互采获中,得到发展,这对于儒家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蒙文通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关系,它们在相互争鸣、彼此攻击不已中,学术界逐步走向统一,为汉代的经学独尊打下了基础,而诸子百家中的有的学术则衰落了。他说:
《庄子·天下篇》把当时的学术平行论述了一番,说是有旧法世传之史一派,有《诗》、《书》、《礼》、《乐》一派,有百家之学一派。这三派学术,在当时都是很有势力的。我们拿他这几句话来仔细推寻,便可知汉人的学术,……六经和百家,他们既和旧法世传之史异派,便要认他们是新派了。……黄帝的学问,从伊尹到太公、管仲,都是一派下来的。到周的时候,周公是和太公不大相同的,一个讲道德,一个讲仁义,一个是讲兵权,一个是讲礼乐,便对抗起来了。太公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周公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从周初直到春秋末年,经过了许多的战争,社会自然便发生了许多变化,旧的学说是不能满足适合人民的思想的,旧的制度也维持不住社会的现况,这便自然会发生新的进步的哲学。儒家有个紧接周公的孔子,修订六经,发挥仁义。道家的学术,便四分五裂,发生了许多的派别,只有老子守着他一部分要约的内容。……九流百家便一齐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但是他们都归本于黄帝。……荀子评论当时的学术,注重的只是道、墨、儒三家,……添入一个名、法,也还只是五家,这才是很有价值的学说。……在百家争鸣、攻击不已的时候,学术界便发出需要统一的趋势了,吕不韦趁着这机会集合许多宾客在那里合作,著出了八览、六论、十二纪来,这便是当时的杂家,他是想集取百家之所长,不专主那一派的。到始皇统一了天下的时候,他把《诗》、《书》、百家语这两大派一齐都立在学官,便禁止民间收藏这两派的书,……他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把百家私学统一起来,从此,百家私学便一落千丈。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诸子学说便从此衰歇,只有官学一派独传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独传了。所谓三大派中,墨学便成了绝学,名家、法家也渐绝灭了。
蒙文通引述《庄子·天下篇》所言,把先秦的学术分为三派,一派是旧法世传的史学派,一派是讲《诗》、《书》、《礼》、《乐》等六经的儒学派,再就是百家之学一派。认为这三派不仅在当时很有势力,而且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汉人的学术。三派之中,旧法世传的史学派属于旧派,而六经学和百家之学,与旧法世传之史学派相异,故为新派。他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九流百家之学都归本于黄帝,都以黄帝为文明、文化创造之源,而不仅以黄帝为某一家的始祖。黄帝的学问,到周的时候,出现了周公与太公的不大相同,其中太公讲道德,讲兵权,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而周公则讲仁义,讲礼乐,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又从周初到春秋末的孔老之时,社会经历了不少战争和变化,旧思想、旧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于是产生了新的哲学。孔子继承周公,修订六经,以仁释礼,发挥仁和义的思想;而道家则四分五裂,只有老子讲到道家的要约。他显然认为在孔、老之前儒、道两家都另有创始人,并认为当时天下大乱,莫衷一是,各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它们皆归本于黄帝。虽然百家之说,争相用世,但蒙文通引荀子所评,看重的只是儒、道、墨三家,再添上名家、法家,认为有价值的不过这五家。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在诸子百家争鸣、相互攻击不止的时候,学术界也出现了逐步统一的趋势。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撰成《吕氏春秋》,以图集百家之长,而不专主某一家,成为杂家的代表作。而秦始皇则把《诗》、《书》之学和百家语之诸子学两派均立在学官,同时禁止民间收藏儒家和百家的著作,目的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统一百家私学,致使除立在学官的《诗》、《书》、百家语外,百家私学则衰落了。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诸子学也就从此衰落了。但蒙文通认为,罢黜百家后,并未独尊儒术,即不仅儒家,而且道家也在传袭,儒、道、墨三大派,只有墨学成为绝学。
这种说法,与人们理解的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史的情形有别,因当时崇尚黄老道家的窦太后去世后,黄老道家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走向衰微。即使按照人们所说的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也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那也不应是道家还在“独传”,“法家也渐绝灭了”。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上的诸侯割据、分封治国的局面造成的,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学术与文化的统一。然而用什么学术来统一思想文化,却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否定伦理道德的价值,很快就激化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伦常关系,结果至秦二世而亡。由此暴露了法家学术的局限和弊病,表明单纯用这种法家学术来统一思想行不通。汉初尊奉黄老之道,借黄帝之名,取老子之学。黄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清静自定”,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它基本适应了汉初社会恢复经济的需要而取得优势地位。但黄老道家崇尚自然,不讲社会人文伦理,这与法家相似,故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黄老思想亦不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它让位于新的思想是必然的。应该说,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争鸣”的反动,而是“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儒术独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诸家思想,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独尊儒术,兼取诸家的实行,是思想完成统一的标志。从此,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
到后来,蒙文通客观地看到儒家之六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相得益彰,不相脱离的关系。他说:“非诸子之出于六经,实经说之能荟集诸子以为经术之中心。究诸子之义理,始觉千歧百异毕有统摄,毕有归宿。六经与百家,必循环反复,乃见相得而益彰。晚周与先汉,离之则两伤也;先秦以往之思想毕萃于汉,而岂特汇儒者一家之说使结晶于是哉!”认为晚周的诸子学与先汉的经说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不是说诸子出入于六经,而是说儒家经说能够汲取诸子百家思想之长而成为经术之中心。汲取了诸子义理之长的儒家经说在千歧百异之中能有统摄和归宿,是对自先秦以来各家思想的荟萃,而并非仅是儒学一家思想的结晶。所以应把六经与百家说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脱离和相互对立,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在互为采获中相得益彰。
(二)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