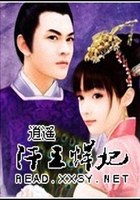(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哭丁在君
(用元微之别白乐天诗的原韵)
明知一死了百愿,
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
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
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
如此风流一代无!
二十五年二月(?)
(跋)此二诗用元微之别白乐天两绝句原韵。民国二十年八月,丁在君(文江)在秦皇岛曾用此二诗的原韵,作两首绝句寄给我。诗如下: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元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他死在长沙。我追想四年半之前他怀念我的诗,仍用原韵作诗追哭他。微之原诗不在《元氏长庆集》中,仅见于乐天“祭微之文”中。这两首诗是在君和我最爱朗诵的,我附录在这里: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应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明年(民国四十五年)一月是他去世二十年的纪念。我今天重写这几首诗,还忘不了这一个最可爱的朋友。
他的诗里,我的诗里,都提到“青眼”的话。在君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上面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什么样子!”他听了大笑。虬怒须也是事实。
民国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适之
(收入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1941年12月萍社出版。
又载1955年11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报自由天地》)
无心肝的月亮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明人小说中有此两句无名的诗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沟渠,
也照着西山山顶。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
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
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你要可怜他,
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
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二十五年.五.十九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二十五年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从神户到东京,道中望富士山
雾鬓云裾绝代姿,
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开是几时?
待到云开是几时?
七月二十一日太平洋船上追记
(原载1946年12月10日《读书通讯》第122期,
原题《车中望富士山》)
廿六年七月廿三日是高梦旦先生周年忌日,
我在庐山上作此诗寄慰君珊、仲洽
九年后我重到庐山,
山色泉声都还如旧。
每一个山头,每一条瀑布,
都叫我想念当年同游的老朋友。
他爱看高山大瀑布,
就如同他爱看像个样子的人。
他病倒在游三峡上峨眉的途中,
他不懊悔他那追求不倦的精神。
他不要我们哭他。
他要我们向前,要我们高兴。
他要我们爬他没有上过的高峰,
追求他没有见过的奇景。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年4月19日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做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1938.8.4在伦敦
(原载1962年3月1日台北《文星》杂志第53期)
追哭徐新六
1938年8月24日上午,新六的飞机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都死了。十日之后,我在瑞士收到他8月23日夜写给我的一封信,是他临死的前夜写的。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他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他的一切已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不敢忘记他的遗训。
二十七年(1938)九月八日
在瑞士的鲁塞恩(Lucerne)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
三书不厌十回读,
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
如今何处有斯人!
1938.10.16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
略有几茎白发,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二十七年(1938)十月三十一日在美京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三十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了。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一枝箭一只曲子
我望空中射出了一枝箭,
射出去就看不见了。
他飞的那么快
谁知道他飞的多么远了?
我向空中唱了一只曲子,
那歌声四散飘扬了。
谁也不会知道,
他飘到天的那一方了。
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
我找着了那枝箭,
钉在一棵老橡树高头,
箭杆儿还没有断。
那只曲子,我也找着了,
说破了倒也不希奇,
那只曲子,从头到尾,
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
1943.6.14夜初译6.23改稿
(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The Arrow and the Song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I know not where;
For,so swiftly it flew,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I know not where;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Long,long afterward,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still unbroke;
And the song,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这是美国诗人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一首小诗,题为The Arrow and the Song,原为三节,我把第三节分做两节,比较明白一点。
这诗不算是朗菲罗的好诗,但是第三节人多爱念。我十几岁时在中国公学念这首诗,就想译他。那时候我还写古文,总觉得翻译不容易。今夜试用白话,稍稍改换原诗文字,译出后还觉得不很满意。
适之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今年1月到上海,才知道南方谈文艺的朋友有所谓“胡适之体新诗”的讨论。发起这个讨论的是陈子展先生,他主张“胡适之体可以说是新诗的一条新路”。后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听说是反对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