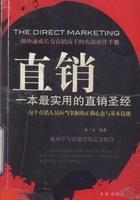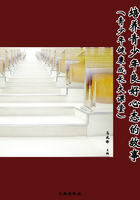以后的日子,出门有了同行的人,林硕,不远不近地跟着,也不说话,她们坐车,他也坐车,他们吃饭,他也吃,离得有一段距离,却总是甩不掉他。
黄子琪有时候也凶他,他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我从找到你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让你再从我视线中消失!”
黄子琪脸色不好,转身拉着锦弦走,他就在身后说:“我又不打扰你,这世界又不是你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如果嫌我烦,就是心里还有我。如果心里没有我,你完全可以无视。”
锦弦听得想笑,可转脸看到黄子琪气嘟嘟地,只好忍住。
在车上,百无聊赖的时候,黄子琪不在她身边的空挡,他偶尔也会过来和锦弦搭讪,问她:“苏楚呢,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
她不回答他,转过脸看窗外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
黄子琪一回来,他马上闭嘴,站得远远地,黄子琪瞪他一眼,他就笑,有时候也会可怜兮兮地望着黄子琪发呆,锦弦碰碰黄子琪的肩膀,黄子琪一回头,他又马上恢复了从前的样子。
有一次,黄子琪拉着她在维也纳的街上跑,在巴洛克风的建筑群中穿梭,跑得很快,仿佛有交响曲在他们耳边回响,她很兴奋,虽不懂音乐,却能在这个音乐之都里感受到宏伟,蓬勃,粗矿又不失柔情的交响乐的奏鸣曲。
跑累了,停下来,以为终于可以摆脱林硕了,便在一家咖啡厅坐了一会,吃了一点东西,准备下一站去参观维也纳艺术博物馆,出了门,马上就看到林硕,他倚在门口,气定神闲地看着她们,两个人顿时无语。
黄子琪可能是忍无可忍,走过去,对林硕说:“好吧,我告诉你当初为什么会离开,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要躲开你,因为你父母动用了关系,把我父亲和哥哥凭着多年做学术的经验才做到的职位上弄了下来,我家人虽不爱好权势,可是这样的事实他们根本就接受不了,我答应了你母亲,以后都不会见你,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再让我的家人受到任何牵累,你明不明白!”
林硕眼睛亮亮地,居然很兴奋,说:“这么说你前些天告诉我说爱上了别人的话是撒谎骗我的?你没爱上别人,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他连说了几个这样就好,黄子琪气到浑身发抖,说了句:“我看你是疯了,以后不要再跟着我,我不想再见到你!”
她拉着锦弦走,林硕这次倒没有跟过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死心了。
那天晚上,在维也纳小镇古老的旅馆里,在扑鼻的葡萄酒的清香里,黄子琪有些微醉,倚在缠枝花纹的金色镜子前,第一次向锦弦讲了她和林硕的故事,她说:“我和林硕交往了六年,六年里我一直相信他能说服自己的父母接受我,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简直是在做梦,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接受我这样一个从小地方来的家世平平的人做林家的媳妇。离开林硕,我也知道他会很难过,我也一样,那段日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不过来,我没有办法,他父母拿我的家人逼我,我的家人他们辛苦供养我上学读书,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也不能置他们不管,让他们因为我的关系而失去一些他们辛苦了半辈子才得到的东西,我承认,我对不起他,可是他这些年闲着了吗?谁不知道他花天酒地,和多少的女子有染,我已经很辛苦忘记了他,为什么他还要不停地来烦我……”
黄子琪泪眼朦胧地,她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的爱情也是一团糟,像是要爱了,可后来发现是一个烂果子,表面很光鲜,香气四溢,但是切开一看,里面早已腐烂。
回到瑞士黄子琪的家,进了铁门,她们都以为走错了地方,从楼梯到走廊上都有一簇一簇的玫瑰,一直到家门口,打开门,从客厅到房间到窗台,都布满了玫瑰花,很壮观,也很美丽。
两个人都是怔怔地,但也都明白是谁做的,很快,黄子琪电话响起,林硕的声音传来:“喜欢吗?我答应过你给你一所种满玫瑰花的房子,然后再向你求婚,不过时间仓促了一点,没来得及准备……”
黄子琪打断了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锦弦在场的缘故,她很忍耐,尽量不让自己发怒。
“我想干什么,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话音落下,林硕也出现在门口,他挂电话,走过来单膝在黄子琪面前跪下,拿出怀里的戒指盒,打开了,说:“琪琪,我想好了,要在这里和你注册结婚,不管以后有什么的困难,我都会和你一起承担,嫁给我,好吗?”
黄子琪像是要疯掉了,抓起桌子上的一杯水泼在了林硕的脸上,说:“我求求你,拜托你,要疯到别的地方去好吗?”
她转身要走,林硕手快,一把就抓住了她,说:“我是认真的,你不答应,我是不会起来的,你知道我说得对就做得到。”
黄子琪还真是犹豫了一下,林硕的脾气她最了解,当初为了和她在一起,盯着父母的压力那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一刻妥协过。
她望了一眼窗口,又看他,赌气般地说:“好,想要我嫁给你也不难,如果你从这里跳下去还没有摔死的话,我就嫁给你!”
林硕笑,连往窗口看一眼都没有,就说:“好,我早想跳了,不过你说话要算数!”
他说完,起身过去推开窗子几乎想也没想地就跳了出去,锦弦一个“不”字还没有出口,窗口已没有了人影。
苏楚倒下了,他去开车门,这个地方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想离开,离开这锥心的痛,可是拉车门的时候,栽了下去,他想,不痛了,真好!
可还是醒了过来,在左耀宗的家里,他的手腕上包过了,白色的纱布层层叠叠地。
老人进来,说:“醒……来了就好,年纪轻轻地,做什么不好,有什么想不开的,学……人自杀。”
他没想自杀,但也没想解释,坐起来要走,瞥到屋子里的物品,喝水的杯子,擦脸的毛巾,还有门口的鞋子……这些都是锦弦的物品。
他挨着看,从书桌到衣柜,痛意又弥漫上心头。
“在……这里住几天吧,等病好了再走,我……认得你,你是锦弦的朋友。”左耀宗留他,他答应了,这里每件物品上都有属于锦弦的气息,她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她一个人,要忍受着怎样的煎熬,就像一朵花开到最盛,却突然凋零。她对这世界可还有留恋,她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愿望,他想知道,只能从这些物品上找。
老人做了一条鱼,在院子里一株海棠树下支起了桌子,拿出一瓶酒来,喊苏楚出来喝酒,苏楚出来了,满上酒,什么也没说一扬脖喝了下去,酒很苦涩,又辣人眼,他咳嗽着,眼角处咳出了泪。
老人也喝,醉了,絮絮叨叨地说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的抱负,当然更多的是说对不起锦弦,让锦弦受苦了,说到动情之处,又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又说:“锦弦命苦,从小没有了妈妈,如今又……,我真为这孩子可怜,我后悔,后悔年轻的时候瞎了眼,怎么会那么对待她们,现在想要弥补也晚了。”老人捶胸顿足,说不出的悔意。
他也是,月亮升了起来,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上天为什么这么残酷,夺去他心爱的人的生命,这样想着,一杯一杯地往下倒,醉死也好,这种五脏六腑都在撕裂的痛楚让他已无法承受。
如果可以,他宁愿死去的那个是自己。
他醉了,趴在桌子上,没有听到老人的呢喃:“她还是回去了,也好,凌东会照顾好她的,我也放心了。”说着,老人也趴下了。
如此静谧的月色,唤不醒这两个烂醉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