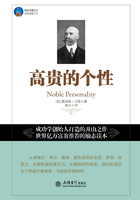那一天他走了很远,远到整个乡大院和周边的藏房都只仿佛草原上一个个微微隆起的土丘。他选了一处水流平静的河段,将蚯蚓穿上鱼钩,抛进溪水中,再点上一支烟,想钓满那只塑料袋,慢慢回去,这时间会耗去大半天。鱼太爱咬钩,不到两小时,带去的塑料袋已快装满。苏医生知道草原的鱼特别多,乡上的人偶尔想吃鱼,拿一张网,骑着摩托去河边,不过半小时,准提回一桶鱼来。苏医生不愿意用网,用网只能解决嘴馋,却没办法消耗时间。塑料袋浸在水里,那些鱼拥挤着在袋内噼噼啪啪地挣扎,苏医生看着它们,正犹豫该不该这样早就回去,这时候他看见两个牧民骑着马从远处走来,他站起身,挥动着手给他们打招呼。这也是他来阿须新学到的规矩,无论是谁,无论认不认识,碰见了,彼此都会亲切地招呼对方。他看见两个牧民越走越近,其中一个非常壮实,面色黑红透亮,长发用红发辫系着,满脸络腮胡更显出他的英武剽悍。他们在苏医生面前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下来。那个壮实的汉子特别高大,加上横别在腹部的长腰刀,只仿佛一座铁塔立在面前。苏医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他眼里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杀气,苏医生再次笑着招呼他们。他发现那个壮实汉子的面色非常阴沉,好在另一个牧民开口说:“喂!你在干啥?”
那时候的苏医生还听不懂藏语,他点着头说:“你们好!”
那个牧民说:“你是哪里的?”
苏医生一头雾水,茫然看着他们。
壮实的汉子一把抢过苏医生手里的钓竿,掰成两段,狠狠扔向对面。又蹲到河边,将浸在水里的塑料袋搂底翻起,鱼哗哗跌入水里。苏医生看见鱼入水的瞬间,用力摆动尾鳍,散成无数黑影,闪动着,消失在溪水里。有两条鱼躺在水面,它们翻着白肚,随水流缓慢漂走。在阳光的照耀下,白色的鱼肚发出刺目的光芒。壮实的汉子待待盯着两条鱼越漂越远,汇入湍急的河段后,只剩两个小小的白点。汉子转过头时,苏医生看见他的双眼红透了,眼白里突然涌现的红血丝显示出汉子的愤怒,他原本英武的面孔这一刻变得极为狰狞,也不知他高声骂了句什么,猛冲过来,一掌将苏医生推倒在地,他紧攥双拳,苏医生的心跳加快了节奏,感觉像要蹦出嗓子眼儿。另一个牧民紧紧拉住汉子,他们相互说了些什么,两人总算骑上马,夹了夹马腹向远处跑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草原里,苏医生才喘出一口大气。感觉心脏有力地敲击着心房,双腿也软得没法站立。
后来他知道那正是绒布。
苏医生一直认为绒布欺生,欺负他才到阿须。苏医生在乡大院里主动打探绒布的事,一提到这个名字,乡院里的人总有许多故事。后来也不需要他再问,来乡大院办事的牧民时常讲起绒布的传奇。那些故事多得像草原上翩飞的蝴蝶,随处可见。苏医生还记得甲马讲过的两件事,说绒布二十多岁时,遇上另一个牧场的五个壮实汉子,在夜里来阿须盗牦牛,得之牦牛被盗走后,绒布来不及等待牧场的汉子们集结起来,只身骑马飞奔着去追赶,跑了几小时,在一个坡地里赶上那几个汉子。绒布把长长的腰刀高举过头,双眼布满愤怒的红血丝。几个汉子围住他,听他高声喊道:“要么把牦牛留下来,要么把你们几个留下来,要么让我留在这坡地上。”几个汉子见这是一个血性的人,一个不顾忌性命的人,被他几乎要喷出火焰的双眼震慑住,强硬下去,讨不到半点儿好处,只好讪讪地骑马离去。赶回被盗的牦牛,这事本该完美了结,绒布还咽不下那口气,要去对方的牧场以牙还牙。他不打算夜晚潜入,他想在他们刚刚苏醒时赶走牦牛,让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从容追赶。去那个牧场有两条路,一条绕开峡谷,翻过山脊,这条路要远许多,却避开了危险。另一条近路得穿越峡谷,那峡谷被草原上的人们称着“黑狼谷”,是狼群的栖息之地,没人愿意从那里过。绒布半夜出发,专拣黑狼谷走,深入谷中,果然遭遇狼群,在月光朦胧映照下,四面都是发绿光的眼睛。绒布手握长刀,双腿紧夹战栗的马腹,一路砍杀过去,也不知砍伤多少狼。到那牧场时,天刚亮开,黑帐篷飘着淡淡的青烟,有牧民已在帐篷外忙碌,他们看见一个满身是血的剽悍男人骑着同样沾满鲜血的白马站定在牧场边,将整个牧场尽收眼底。帐篷外的人越集越多时,他才发一声吼,骑着马在牛群里赶出几头牦牛,扬长而去。那几个盗牛的汉子也站在帐篷外,他们示意牧民们不必追赶,这是绒布,阿须的绒布,怪只怪自己主动招惹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