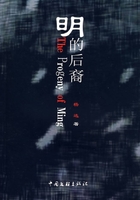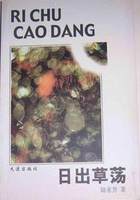国庆节那天宋瑜和张玉琢举行了婚礼。
一大早,迎亲的人来到家里。临出门时,宋瑜敲响了卧室门,母亲一直把自己关在里边,布置新房,采购结婚用品等等,她根本不插一句话,都由父亲领着我去帮忙,父亲说没想到母亲的心这样硬。宋瑜敲了许久,迎亲的人还等在门外,她那天早晨显得极有耐性,始终轻轻地持续地敲着,一直敲到母亲开门,母亲站在寝室里,也不看她,她只说了一句:“妈,我走了。”眼泪就掉下来,她胡乱抹了一把脸,匆匆跑向门外,母亲再次把门关上。
新房布置在张玉琢那三间木板房里,三间木板房用报纸一糊,挂上彩纸再贴上喜字就成了新房,亲戚朋友聚在房里,剥糖吃瓜子闲聊龙门阵。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姐姐宋瑜和年轻理发师张玉琢的婚礼将和无数个康定的婚礼那样平庸和容易忘记,事实上他们的婚礼成了一段时间内康定的经典婚礼,多年之后,老康定人还能忆起张玉琢和宋瑜的婚礼,直到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老康定不复存在,直到经济大潮像决堤的泥石流,才消解了那场婚礼在康定的特殊性。
婚礼本身没别的,高兴、快乐,婚礼的方式包含了藏族的、汉族的,还有别民族的婚庆方式,成为康定的婚礼,这也没啥,在康定结婚,就是这样的方式。白天,两间小屋里并没多少人,都是双方的亲朋好友。夜色漫上来后,小小的康定城里这两间小屋成了最明亮的地方。张玉琢陪着理发师们,宋瑜扎在纺织厂的工友中。那一天宋瑜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忧伤,他们不明白她为啥不高兴,整个婚礼因此显得含蓄和沉寂,所以那一大队人由远至近地走来时,他们嘈杂的声音倒盖过了新房里的喜庆声。听到这嘈杂的声音,宋瑜第一个冲出了门,参加婚礼的人纷纷跟出去看热闹。大街上,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康定人簇拥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慢慢走来。数十年前,康定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开教堂传教,开医院行医,还收留没人照管的婴儿。但后来,没有外国人再来了,像宋瑜、张玉琢这一代康定人,仅仅听老辈们讲起过黄头发蓝眼睛,讲起过他们长满毛的大手。宋瑜一眼就看见了他们,她激动地蹦跳着叫了一声:“外国人!”手都不知该放哪里。那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受这样的簇拥和围观,自然显得兴奋。他们来到新房门前,灯火通明的新房吸引了他们,当他们看见木质方窗和木门上贴着的大红喜字时,男人兴奋地对女人说着什么,女人就走上前来问宋瑜:“结婚?结婚是吗?”女人的汉语非常生硬,宋瑜点着头说:“是啊,结婚。”宋瑜的汉语也生硬起来。女人叽里咕噜地对男人说,男人的表情显得很急迫,手舞足蹈地说着话,女人又和宋瑜说话了:“婚礼!我们参加,让我们参加。”宋瑜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连声说:“好啊好啊!让你们参加。”两个外国人,包括那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康定人,一齐拥进了新房,两间小木屋顿时拥挤起来,好在邻居们见坐不下了,忙把自己的房门敞开,五六间连着的木板房都换上了明亮的灯,坐满了人,帮忙的人赶紧剪着喜字,贴到邻居的门窗上。
婚礼从那一刻开始进入高潮,大家端上酒杯相互敬酒,有了酒意,就大着嗓门儿唱歌,男人有康巴汉子的血性,女人有康巴姑娘的大气,要唱歌谁也不怕谁,你唱了他唱,这屋唱了那屋唱。后来他们把凳子桌子都挪开了,跳起锅庄和弦子,再后来他们嫌屋与屋阻隔了众人的欢乐,不过瘾,就把桌子搬到街上,好在那时候这条街还没有扩展,不容车通行。他们在街上将桌子摆成一溜,围着桌子又跳又唱,人也越聚越多。
宋瑜从那一刻开始,一扫所有的不快,说唱就唱,说喝就喝,让两个外国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时狠抱了对方猛啃。他们把酒一杯一杯倒进肚里。通宵的狂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天光明亮,两个外国人离开欢闹的场面,向他们的旅店走去,走了几步,刚到将军桥,男人一软,就瘫在地上,女人想把男人扶起来,弯了腰一用力,跟着滑到地上,再也起不来,他们醉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喝醉了。那时候宋瑜还兴奋地喊着:“喝吧,再给我端一杯。”她已被人扶到床上不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