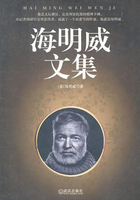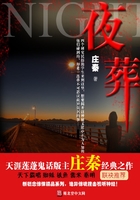到耀武六岁时,耀文只三岁。耀武能带耀文了,父母去上班,耀武就把耀文领出门,耀武待待坐在横木上晒太阳,耀文一刻也坐不住,满院乱跑,什么东西都要动一动。砖厂大院的人一直不懂这亲亲的两兄弟性格相差为啥那样大,一个调皮捣蛋机灵聪明,一个闷头闷脑悄无声息。有时候闲聊,他们问玉秀或谭明康:“这两个孩子差异怎么那样大?”谭明康说:“是吗?差异大吗?”大家知道他不怎么关注孩子,这是男人的通病。玉秀说:“是啊,我也想不明白,耀武屁声没有,放那里你只当他不存在,另外那个整天都有说的,耀武如果像耀文那样淘气,我们也决不要第二个孩子了。”
也有人问:“这俩孩子谁像谁啊?”玉秀说:“小的那个有点儿像我,大的有点儿像他爸。”问谭明康时,他说:“没注意,哪知道谁像谁。”说是说过了,他心里却生点儿疑问,老悬着,咽不下去。他叫过俩孩子,耀文说:“爸,叫我干啥?”他看看耀文,耀文不怎么胖,小小的瘦削的脸蛋透着他的某种痕迹,像许多个轮回中一个熟人的样子。他说:“没事,你玩吧。”耀文就跑开了。他再注视耀武,耀武站在边上,耀武要胖许多,圆脸上泛着太阳的红,他在耀武身上看见了玉秀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坚定地存在。他只是没找到自己的半点儿痕迹,却那样专注地看着,越看越陌生。
夜里他问玉秀:“你讲讲你和你那个男朋友的事吧。”
玉秀说:“怎么想起问这个?”
谭明康说:“没啥,就好奇。”
玉秀说:“有啥好奇的,认到你我就把别人甩了,你该满意了吧,唉,我就不知你哪一点儿让我鬼迷心窍了。”
谭明康没心情开玩笑,说:“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一时又说不出口。
玉秀说:“你想说啥?”
谭明康说:“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谈朋友的?”
玉秀说:“还能怎样?”
谭明康怔了怔说:“你们就没……没亲热过一下?”
玉秀笑起来说:“那时候敢亲热啥,连手都没牵过。”说着,想起那次自己主动拉国平的手,那一手的汗记忆犹新。
谭明康说:“真的连手都没牵过?”
玉秀缓过神来,她撑起身体,狐疑地看着谭明康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想起问这些?”
谭明康躲闪着玉秀的眼睛说:“没啥啊。”
玉秀说:“是不是谁给你讲了我的坏话?说,是谁?”
谭明康慌了神,说:“随口问问,没人说啥,快睡吧,时间不早了,我还得上夜班呢。”
那几天时间谭明康爱出神地盯着耀武,越看越觉得没有像自己的地方,不敢再问玉秀,想等个机会,带着耀武去验血。到星期天,玉秀要去看电影,谭明康说:“你去吧,孩子我带着。”玉秀一走,谭明康忙托周嫂帮看耀文,牵着耀武上街,临近医院,谭明康的脚步越来越慢,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验血真有问题,他该怎么办?他似乎看见两人毫无余地的争吵,然后玉秀带走耀武,一家人从此成了两家人。他被自己的这个假设吓了一跳,他在医院门前停下脚步,看看耀武,他还啥都不知道,谭明康的心软了,猛抱起耀武,想管这孩子是谁的,他现在叫自己爸。想着,在耀武圆脸上亲一口,说:“我们回家吧,我给你买糖吃。”
回到家里,把糖分给俩孩子吃,耀武带着弟弟去院里玩儿,谭明康去叫周光福,在家里摆开了棋局,感觉这日子从未像今天这样踏实而温馨,下棋时,就把棋子摔得天响,以此给愉快的心情伴奏。
到耀武去上小学,耀文也被送到幼儿园去后,谭明康短暂地喜欢上二胡,那是三中全会后一个邋遢老头子带给他的迷恋。那老头姓姜,早年就在砖厂待着,是厨房的炊事员,满脑袋花白的头发,满下巴横七竖八的胡须,像永远没有剃过。老头说一嘴拐来拐去的外省话,没人能说得清他的来历,他也像没有任何亲人,多年时间里,始终蜗居在砖厂大院一角厨房边那间阴暗而潮湿的房里。多年时间里老头没什么明显变化,谭明康觉得那主要是他不能再老了,他没地方能再老下去。厂院里的孩子们都非常怕他,特别在冬天,有时候家里来不及做饭,让耀武去厨房打,耀武端着铝锅,每一步都忐忑不安,到了厨房窗口,他把饭票递进去,尽量不去看老头的脸,老头的眼睛在冬季总是通红的,不停淌泪,活像那些暗夜中要跳出来的鬼魂。耀武却免不了看见老头的手,老头的手在冬季长满冻疮,肿胀得像馒头一样皴裂开来。接过铝锅,耀武迫不及待地逃离厨房,在夜晚的噩梦中,那双手无处不在,四处寻找耀武。
就是这样一个邋遢老头,就是这样一双在冬季长满冻疮的手,却让二胡发出了美妙的声音。
收音机大家都在听,那次会议大家也都挂嘴上说说,感觉像世界从此有了色彩,说过也就完事,该忙啥忙啥,都意识不到遥远的春天会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只有老头听了广播后,从一个巨大的木箱里拿出尘封的二胡,他不与人交谈感受,他只在夜晚让二胡悲凉的声音响彻砖厂大院。
谭明康说:“谁在拉二胡?”
玉秀说:“谁知道哪个发疯了。”
谭明康凝神静听,那曲子水一样浸透了他,让他坐立不安,他甚至在那段时间里忘掉了象棋,他跨出门去,要在黑夜中找出缔造这美妙声音的人来。那一晚谭明康回来后异常兴奋,对玉秀说:“你猜猜,谁拉的二胡?”
玉秀说:“猜不到。”
谭明康说:“打死你都想不到,是姜老头呢。”
玉秀问:“哪个姜老头?”
谭明康说:“厨房里的姜老头啊。”
玉秀感叹地说:“想不到他还会这一手。”
那些夜晚,谭明康不再下棋,吃过晚饭他去陪老头,他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倾尽所学谈世界知识,谈中医,他发现老头一开口,就像汪洋那样浩瀚,他只有待待听着。每天夜里,谭明康都兴奋地回到家说:“想不到,谁也想不到,那个老头太厉害了,没有他不知道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漂亮得很。”谭明康把老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跟老头学二胡,开口闭口谈瞎子阿炳,说《二泉映月》。那一段时间,他急着要寻一把二胡,去卖店里看,要数十元钱,终究舍不得。
谭明康学二胡的时间不太长。有一天高音喇叭里呼唤老头的名字,让他去接电话,听到这个呼唤的人都分外诧异,老头不是没亲戚吗,谁还打电话找他?夜里,谭明康去老头那里,他吃惊地见老头一改往日肮脏猥琐的形象,理了头发,横七竖八的胡须也给刮得干干净净,人看上去特别精神,和往日判若两人。谭明康问谁打电话找他。老头说是同学。谭明康又问,你读过书?对谭明康过多的疑问老头善意地笑了笑,并没回答。
谭明康觉得老头全身都是谜,老头对他尚有保留,这让他微微地失望,也激起他破解老头更大的信心。大约两星期后,一辆北京吉普驶入砖厂大院,停在伙食团门前,直到此刻,老头才打开那个巨大的木箱,把里面一件黄色的呢子大氅披到身上,腰板挺得笔直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活像战争片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老头走得干净,除了小包东西,别的都给了砖厂大院的人们,临出厂门,老头拎着二胡来到窑上,谭明康正在上班,老头把二胡送给他,在他的肩上善意而友好地拍拍,老头穿着黄色大氅的形象再一次让谭明康吃惊,他说那一瞬间他只能仰视老人,他把老头送到车上,目睹小车缓慢远去。
后来的消息都是传闻,说老头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是国民党的将领,为躲避动乱岁月,来到遥远的康定,进了砖厂。知道谭明康和老头好,大家都来他这里求证传闻,谭明康微微晃着脑袋卖关子,心满意足的同时,偷偷遗憾老头对他的保守。
老头走后谭明康短暂地拉过几天二胡,没人教,他拉出的声音像赶一群鸡鸭,听的人嫌聒噪,他自己也失了兴趣,把二胡挂上墙头,又下起象棋。玉秀打扫屋子,见墙上的二胡扑满灰尘,嫌碍事,就扔到了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