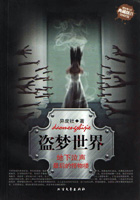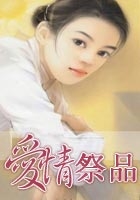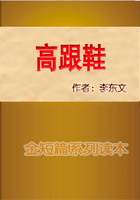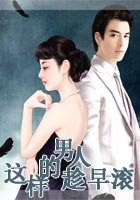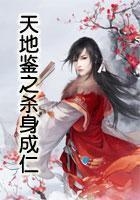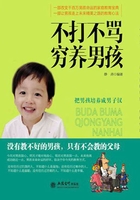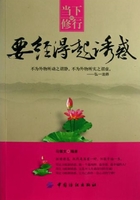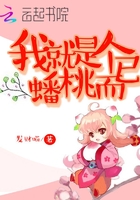“超限”的精要,仍然跳不出古往今来的美学基本准则之一:以少胜多。但区别在于,古典美学可以求助于绝对意义上的“少”,而“超限”所代表的现代美学,则只可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少”——它的“少”相对于那种从容不迫闲散淡定的古典作品而言,已经是“多”,是纷繁缠绕,是五色百味。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尤其是新移民生活的特点,和吕红小说的直面生活的诉
求,决定了古典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只能变身为“超限”。以多写更多。
当年“新感觉派”已经在尝试这条从古典转向现代的道路。上海滩的庞大生活世界,催生了这只小花,但它终究敌不过历史的风云变幻,救亡不仅压倒启蒙,也压倒了新的文学感觉。如今,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越来越被发现不太能处理复杂的现代生活,总是简化现实,于是,对现实的整体把握已经幻为南柯一梦,写实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衰落了。但我们又有可能淹没在这广大的细小繁复的现实之中。
既然不再可以求救于对那些曾经流行的整体概括(比方说,用奴隶社会等五种社会发展阶段,来概括我们了解和感知的历史和现实),这时就难免会祭起“抒情“这件永不衰老的文学法宝,用梦幻来对现实进行补光。从吕红的小说,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特点。
二、梦幻的间离
“间离”是德国大文豪布莱希特的一个戏剧理论术语。布莱希特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现实主义戏剧颇感不满,他在莫斯科惊喜地发现梅兰芳表演的京剧之美学追求要远远大于现实表达的冲动,演员永远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而没有一味沉溺在他所表演的情境中。布莱希特将之归纳为“间离”。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一种艺术自觉对生活的自发表达冲动的超越。
吕红小说的野心,也体现在这种艺术自觉上。面对自己掌握的大量写作素材,吕红没有像很多当代文学作家那样,单靠贩卖生活经历吸引读者(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的范畴内,这种写作也是不乏市场的),而总在试图用自己的精神求索来熔炼这些素材。
这首先体现在作家对各种写作手法的不断尝试。吕红在去美之前,就已经是武汉作协的签约作家,写有在那个时代就颇为成熟的作品(比如发表于1989年的《今天是愚人节》)。移居美国之后,她的写法一直在变,经历了一些不算太成功的过渡作品之后,终于寻找到更具表现力的文学武器,形成了在《不期而遇》、《漂移的冰川和花环》、《微朦的光影》等作品中这样独具特色的破碎叙述。而且这几篇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显示出吕红仍在继续探索。在《微朦的光影》的光影中,叙述的破碎甚至达到单词级别,极富张力。比如这样的句子:
“一连串的独白。你。我。时光。消失。天在下雨。”
女作家的敏感细腻和词句的跳跃融为一体,让人为之爽目。“依旧是回到幽暗的小屋。没有开灯,她无意识地按动电视遥控器。屏幕上迅即闪动的是一张张怪脸,莫名其妙的不能解读。急促怪诞的伴奏音乐引出屏幕画面不断地变动、闪现;城市在路轨交错中迷茫地延伸,男人女人疯狂舞蹈的脚。变幻莫测的舞步,在幽暗模糊的背景里。一个女人完美的脸。惨白的神色。伤感的片断。落雨。”
这是在“芯”遭受海外生存危机、国内男人“抄家”、后院起火及情感幻灭等一连串现实轰然打击之后,几段情绪描写中的一段。在《漂移的冰川和花环》中独具特色的破碎叙述可谓俯拾皆是。
其次体现在吕红作品(尤其是近期作品)中的梦幻色彩。善用文学来造梦的作家不少,但假如没有扎实的写实底子,文学很容易沦为单纯的造梦器。吕红小说恰好是二者的结合,梦幻成为现实的一种折射。
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短篇小说《微朦的光影》。女主人公芯的两段故事本来就无头无尾,前生今世暧昧不清,且又被切割为许多叙述的碎片;用来完成这一切割的,是对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黑白电影《广岛之恋》的极尽抒情但又异常破碎的叙述,它的强烈的梦幻色彩,不仅渲染进了小说的主体故事,而且也形成一种间离的互视效果。小说的人物在看《广岛之恋》,焉知《广岛之恋》里的人物没有在斜眼瞥见小说里的爱欲迷离?非常相近的情绪出发点,所抵达的生活现场却愈行愈远,壮丽、繁复、缠绵的梦幻显衬出生活的琐屑、无奈、庸常。梦幻的间离让人对生活唏噓不已。
与在中国国内的人们一般想象的不同,移民美国的生活,往往并没有那么“异邦”。甚至常常让人感觉,是从一个中国移民到了另一个中国。因为整天打交道的,往往还都是华人。那些熟悉的算计、委琐、粗俗、死要面子,所有那些以为随着一声“American”的呼号就会随风而去化作往事的东西,仍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他们或者是像大刘那样身在中国而持续发生着影响的“过渡移民”,或者是像老拧那样的早就熟悉了美国因而控制欲重新健全起来的老移民,或者是林浩那样胆大心不细让人没法放心的新移民,这三个人物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新移民文学女性形象的生活坐标。她跑不出这个坐标系,要是能跑出,就不会进入华语文学的描写范围了。但是显然,这个坐标系具有一定的噩梦性质,想要跑出却跑不出。
于是“美国情人”皮特出场了。他像一个救世主一样,化解了三个典型人物给我们的女主人公施加的精神罗网。即便是最后的抛弃,也仿佛是精神施救的一部分。
皮特所承担的间离功能,与《广岛之恋》相似。也不难看出,
这个人物的塑造,融入了一些美国电影中男性主人公的影子。
但问题在于,《广岛之恋》只是一部主人公观看并铭记在心的电影,而皮特是一个需要着力刻画的人物,写起来难度更大。施与大刘、老拧、林浩的笔法如此细腻写实,堪称新移民文学的三个人物典型,那么,如何在这种笔法与写皮特的笔法之间进行切换呢?作者沿用了《微朦的光影》中的处理方式,用章节的划分,把皮特的柔情穿插进写实的章节之中。这样的处理是不错的,但对于这样一部内容浩大的长篇,却也不免显得有点不够。省力固然省力,却也回避了应该迎头而上的难度。
《微朦的光影》最令人赞叹的就是梦幻与现实之间的极为细腻敏感的呼应,但在《美国情人》这样一部庞大得多的作品中,这种呼应反而变少,ABAB的蛇行穿插本来应该浑然一体,现在却显得有些裂痕。“间离”就跟“超限”一样,是精密装置,很容易受到过分拉伸而失去弹性。
这种抒情是1980年代文学及此前文学的遗产,但早已经严重透支负债,不值得继承了。所谓的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按照张广天的说法,无非是一个集体理想主义的时代。不管是1950年代还是1980年代。不管是政治理想还是爱情、生命等等其他大写的理想。集体大而个人小。因而催生了一种召唤式的抒情。无须细节的精心营造,只需要进行招魂一般的抒情,就能够引发读者效果。但时代毕竟不同了。
《漂移的冰川与花环》的抒情都建立在扎实的写实之上。现实感和艺术感因而同时生长。吕红的小说,确乎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这种以若明若暗的感觉化叙述、细致精确的心理探幽、潜意识本能的开掘,再加上庞大的信息量,自觉不自觉地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而复杂的世界,以及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撞中的焦虑、迷惘与纷乱。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它与“新感觉派”相似,突破了传统的行动描写,而大量采用感觉主义、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做一种“感觉外化”的尝试,而且使感觉的碎片和生活的纷繁同时喷薄而出,为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提供了探索的范例。
这种写作方式,恰如新大陆的移民,迷失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异国他乡的光怪陆离、病态的繁华和尘世的喧嚣。由于其模糊的身份定位、都市叙事视角切入和审美差异,作品所展示的新旧斑驳景观,在与现代主义精神一脉相连的基础上又表现出鲜明的叙事特色。
当代作家当中,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固然不少,能一直同时怀有对现代生活的强烈表达欲望和对艺术的探索精神的,却并不多。而时势也正在期待一种新的文学展现更大的活力。而这篇小说,不仅引起我们的希望:或许,当年“新感觉派”未竟的事业,会由海外作家率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