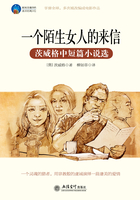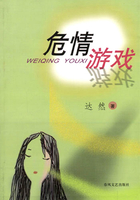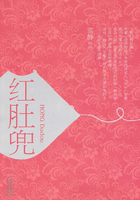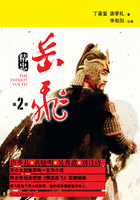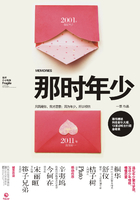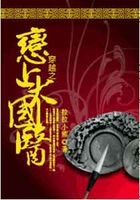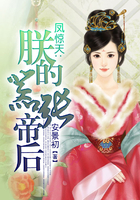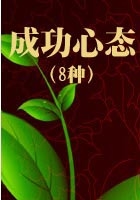在旧金山总图书馆演讲时,我称海外写作就像是孤独的梦游者,在异域语境中,以决绝的姿态默然独行。长长幽暗隧道亦难听见呼应,更鲜有喝彩掌声,当比身在国内的作家更需
旅途小憩。闪烁摇曳在树叶里的啻话。要坚坚U。
今年5月间,南昌小说节的庐山之旅,路上与同行交流,思维火花碰撞闪烁:科学满足欲望,人文提供意义。海外创作的价值也不外乎两点,一是满足欲望,二是提供意义。
写小说的人,似乎总是尝试着打碎点什么(如评论家的解构)揉进点什么(或建构),老是幻想把艺术渗入生活或把生活升华为艺术?就像水依然在流着,但已经不是你最初趟进的那条河了……身处变化多端的世界,人充满了不确定性: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男女相互矛盾的角色尴尬,各种各样的困窘。而小说,就是希望透过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体现的。当传统形式无法表现,便要以新的手法去突破去追求随心所欲之境.挑战原有观念与形式,挑战自我,好比堂吉诃德挑战风车。
生长于都市,书本或影像中生活往往是先于真实生活的。从最初练笔,到读专业书,海外电影节频繁,作为影评人又接触
大量的各国电影,文本具有了多种艺术形式交叉滲透的意味。混合着从东方到西方,小电影到大视角电影;移民生涯时空交错,仿佛人生一场又一场电影。如果写小说是以感性为主、纯属满足心灵探索欲望的话,那么写影评就兼有理性透视和赚取实际补贴的双重意义了。
有媒体采访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时,他认为小说面临很多强大的竞争者。“它整理、命名和提升人们的记忆和经验,但在这方面现在的电视剧可能做得更好;它是新观念和新语言的提供者,但现在网络和大众媒体构成了更有效的公共空间;它勘探新的想象力和艺术形式,但可能多少落后于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小说家应该“到时代的思想和艺术前沿,去重新界定和建立它与生活、与读者的关系”。
就像本雅明一类“侦探家”,无时无刻不在侦察着世界的真相,纂取各种细节,似乎永远在不确定中游走。当其冒死走出黑房子之后,即面临着世界这个更广泛的“黑房子”。难怪有人慨叹,心目中最希望看到的电影,电影史上没有拍出来!你会称这部片子不错那部片子颇佳;皆未必是最想看的那部。峰峦叠嶂,弓丨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见深深触碰到人们心底的作品是多么地难以达到!艺无止境,写作亦是。
回眸幼时,闲暇看父亲阅读古典文学,听他以浓重的乡音,吟诗咏词。甚为奇妙的是,那古老文字竟让一向威严刚硬的男人变得水一般柔和可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最终选择了以文字安身立命,无论在故乡,还是异乡。
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有着丰富经验的刘学明社长对选题的重视,还有王虹——多年前小荷才露的年轻责编,而今已是副社长、一位温婉敏慧的成熟女性。点点滴滴,铭感在心。正
因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执著,对海外华文作家的关注,才使我有信心将散落的文字集结。从湿润海风孕育的灵感,到文友间交流的初稿;文学刊物刊登,华文作品精选;几经推敲,反复修改。资深美编晓军的设计,让这本装帧别致的新书,成为旅美文字生涯一个小结。
诸多专家及读者的关切厚爱,予我更多激情和持久耐力,继续下一段艰辛而美妙的旅程。
【吕红】
2010年7月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