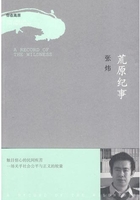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旅美作家吕红小说创作述评邓菡彬
在电影《海上钢琴师》的开头,伴着故事讲述者低沉缓慢的调子,画面中一艘客轮的前甲板上人头攒动,然后,其中一个人眼睛睁大了,用不知带着何种乡音的英语髙喊“America”,霎时人群沸腾了。也许他们望见了自由女神?或者是金门大桥?这一幕是一个缩影。新移民总是带着兴奋、狂喜和憧憬,踏上这块土地。“America”就像一句魔咒,让人在这一刹那,将过去的生活像丢弃一具自己的尸体那样当风扬其灰。不管前途是明或暗,总之,新的生活开始了。过去那些熟悉的东西,将要被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鲜(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压倒。非但亚洲的移民如此。但也许尤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移民感受为深;而又更以从中国大陆到来的、近几十年的新移民更深。
这种冲击或者压力,激发出巨大的表达欲望。这首先是大量的口头文学。无数的新移民故事,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口口相传。新移民的生活是繁忙的,也没有经过文学训练,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对自己生活故事的不断表达。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不表达,人就感觉被生活淹没了。我们需要对生活进行定义、解释、分析,从而掌握它。然后,终于有一批人,拿起笔,预备让他们的故事不朽。他们原来或多或少受过一些艺术训练,但是与祖国的文学创作氛围相对隔绝,又忙于生活,常常
久疏战阵,手头可以利用的文学武器,不见得比那些口头文学的作者更多或者更新,却硬是顽强不懈地打出一片天地。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便是本文传主、《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主编、旅居旧金山的华人作家吕红。
她的作品很多,风格多变,但大都有一种相同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承续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写作之未完成的探索,又汲取了女性文学和海外文学的丰厚营养,即使放到整个当代汉语写作之中,也是相当独特的。本文就以其系列小说为中心,试与读者共赏之。
一、表达的超限
读吕红的小说,常让人觉得目不暇接,信息量之密集,几乎要破纸而出,直塞君面。除了个体情绪的纠结之外,大到政界风云、商海波诡、新老移民的倾乳、法律事务的烦难、华人侨社的古今、族裔之间的近疏,小到一花一景,一粥一饭,凡有涉海外生活的新鲜经验,都不被作者轻易放过。她并不准备写史诗,所有这些材料,总是沿着小说人物的生活和情绪涌现出来。但这些材料,又显然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主人公仿佛只是线索,只是给访问学者开邀请信的教授——这些人得以叩关而来之后,并不见得限于教授的门下。海外作家强烈的表达欲望,在吕红这里格外彰显。有一次跟她聊天,她甚至表示,东西太多,实在写不完;自己已经写下来的仅仅只是冰山的小小一角。但其实读者感受到的,并不止这么点儿。因为,就像王小波那句煽情的语录,“我要把一辈子当做一百辈子来活”,作者笔下的一角,也让人强烈感觉到是竭力在其有限的时间长度里要多活几世。以一当十,画一管之斑而可见全豹。
最初我想到的是“过载”这个词。不是“超载”。超载是贬义,不合规矩,要被开罚单。但“过载”呢?在我的想象中,就好比旧金山这座山城里丁零当啷驶去的古老的有轨电车,常常连车身外的踏板上也站着不少人,手握栏柱,半悬在外,随电车上坡下坡而起落。奇怪的是,看到这副情景时,很难想起“超载”这种充满刻板生硬的现代法律气息的词汇,反而会觉得有种美感,温暖的,有些古典气息。吕红小说里充溢的信息量,常常就给人这种感觉。
但是“过载”不能显示出那些没能搭上车的人。而她的小说实际上是要让那些坐上车的人替更多没坐上车的人把车给坐了。就像巴金名著《家》之三弟觉慧,他一个人背叛家庭,是替包括大哥觉新在内的很多人来背叛,来远走。就像言情小说里那句套语“你要替我好好活着”。因此我不得不几乎生造一个词:超限。吕红小说的许多优点和缺点,都在“超限”的问题上纽结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小说家吕红在积极忙碌的文学活动中,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对创作进行总结。由着一股表达的冲动向前疾进,有时正好充分利用“超限”的优势,箭步如飞而姿态优美,有时却不免因为太急切而有点踉跄了。
分别举例来说。
在近作《不期而遇》当中,作者借一次周末舞会,让笔下的主人公不断遭遇各色人等,而这些人又不断引发以往的记忆,大量的生活碎片仿佛随着舞曲的节奏纷至沓来、喷薄而出,速度之快信息之多让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主人公的情绪、舞会的进行、作者的笔调,三者比较浑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能抓紧读者,让他把眼睛贴近这小小的万花筒,得以想象一个更庞大的世界。颇似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等名作的风格气派,但又更细腻,不显生硬。
另一个中篇《漂移的冰川和花环》节奏稍稍舒缓,所写的时间跨度也较长,但仍然是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反复穿插,在异国艰难的创业生活和与故乡的各种纠缠牵扯,左右开弓,力量绷得很足。而究其成功的关键,是三个主要人物的心态都把握得很准很细,因此,所有生活场景的展开或者转述,都紧扣人物情绪,没有流于简单铺陈。
开篇写丈夫大刘在美国的最后一夜,可谓神来之笔。比很多同类小说写主人公到异国的第一天,情绪层次丰富得多。女主人公“芯”来美国时间并不长,但毕竟不是刚下飞机,而且她还将在这里待很久;大刘在美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但他马上就要离开,将妻子一个人留在这里。两个如此亲近但此刻心情却如此不同的人一起在万圣节的旧金山“观西洋景儿”,就比写一个人逛街,更能容纳信息(无独有偶,《微朦的光影》也是使用类似的开头,让“芯”和一个朋友一起逛旧金山同性恋区卡斯楚CASTRO剧院)。所以,虽然作者从市政府广场写到百老汇红灯区,又到中国城的电影院和公寓,一段又一段,读者却并未逃走,而是紧跟着作者的笔触,把眼睛贴近这小小的万花筒,得以想象一个更庞大的世界。因情绪之丰富逼真,故能抓人。
大刘这个人物一下子立起来,后面再写牵扯到故国的很多事情,比如旁人以为“她”是到美国发洋财,等等,都可以通过大刘来写。这就比单纯地写这些世态要好。不散。就好像写“她”在美国的打拼,也是在与“老拧”这个人物的情绪张力之中来写的。老拧是已经在美国混得不错的老华侨,树大根深,当“她”初到之时,帮“她”积极奔走谋到工作,但是后来百般追求不利,甚至要陷害中伤,把“她”干得好好的工作给搞掉。这就比单纯
写事业的打拼更好。而占据整篇小说正中间的位置的“她”在美第一个新年夜的描写,假如是写她一个人,或者孤单地处在某个群体之中,六分之一篇幅的庞大信息就早将小说压垮了。
而在《日落旧金山》之中,这种微妙的张力就有点失衡了。人物情绪拿捏得不够贴身,对女主人公蔷薇的描绘经常是被偷偷地替换为较为程式化的抒情(作者在这里回避了小说创作应该努力挑战的难度),而两大主要人物之一的林浩更是以大笔勾勒为主,连很多关节地方都是匆匆代过,结果导致生活场景的转换常常勾连不上,巨大的信息量“溢出”于小说之外。就像一片过饱和的云,不再能飘飞于蓝天,却变成天空容纳不了的雨水降落下来。
在长篇小说《美国情人》中大量的生活经验、见闻,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自己,争先恐后地要跳上这班大巴。即便是长篇小说,总容量变大,但局部的饱和度还是和中短篇相似,进入的信息太多,若不能与小说的内在感性过程紧密相连,就会破坏整体的平衡。
“超限”是一种威力很大,但却不那么容易使用的文学武器。但从《漂移的冰川和花环》及其姊妹篇来看,作者显然是有能力掌控这一手法的。而且,作者的文学风格正是由此奠定,她不可能也无甚必要退回一种更传统也更稳妥的文学策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