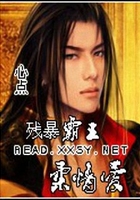芯见两个阿姨用一种异样眼神瞅着母亲的背影,交头接耳唧唧咕咕:哼,资本家的臭小姐,过去还有奶妈呢!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不明白“资本家”是个什么怪物?为什么大人会悄悄地掉泪?无处申诉?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高音喇叭的声撕力竭中;从母亲下农村医疗队、跋山涉水劳动改造无菜可吃硬着头皮去碰生蛆的腐乳;尔后舅舅们的“平反通知”下来、缠绵于病榻的母亲终于露出惨淡的微笑中……她渐晓人事。
在旧相簿里,奶妈抱着芸。泛黄的黑白照片隐隐约约记载了一个女子忧郁而短暂的人生。
十
爹爹至死都不接纳那个硬塞给他的二女婿。(芯也一直想不通外公在这件事情上何以那么倔强绝情?)
二茳总是听到他砰的一声关住房门的声音,刀一样把她的心割得辛辣生痛。老人的愤怒加深了自己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哀叹。尽管别人看她一步步升到局长还挺羡慕,认为是沾了老公的光,她却苦笑,她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二茳是个不喜欢抱怨命运的人。她不得不咬牙忍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最初是组织上日日夜夜轮番轰炸式的谈话,然后是亲人月月年年遗弃般的冷淡。
她宁愿跟随心上人去那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让青春开出血红灿烂的花,也不愿委屈自己窝窝囊囊地活着。她的郁闷情绪不知该怎样宣泄,就沉默,消极地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她憋气,流泪,几天不吃不喝。
区委老张老李都劝她,批评她:二茳同志你这样就不对了嘛,怎么能不听从组织安排呢?你是从封建旧家庭里走出来的,是谁把你培养成为一名干部?是组织。革命大学培养造就了怨你,你就应该服从需要、时刻听从党召唤。你怎么能跟组织使、与小性子?耍大小姐脾气呢?再说老王是个好同志好干部,文化缘虽然不高,但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为革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嘛,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体贴他、帮他解决好婚姻问题吗?你的出身背景不大好,这组织也知道。既然与工农干部在思想上、生活习惯上有距离,那你就更应该彻底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毛病。与老王结合也是向他学习请教的绝好机会。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明白?你不吃饭闹情绪,就是有思想抵触,就根本违背了组织原则。你还年轻,曰子还长着哩,你再好好想想吧!
这样,打了多时的疲劳战,二茳终于想通了认命了。再说,她不认命又能怎样呢?
爹爹就不同。爹爹讨厌谁是做得出来的。这点谁都怕他。他才不管你是谁呢,天王老子都把他没法。
这天,他就让初次登门的二女婿很难堪,吃了闭门羹。他根本不准女婿——事实上他不承认这是他的女婿——走进他的房间,女儿便也进退两难呆在外屋客厅’由娘陪着说说话。那女婿虽说是个区领导,平时呼风唤雨也有些威风八面,在这倔老头面前也无可奈何,只是闷头坐着。
娘也找不出话来跟他谈,气氛沉闷好像大雷雨即将来临的前兆。
偏偏这时爹爹出来了,他目不斜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地穿过客厅,去厕所。然后又继续旁若无人地走过,回房时门砰地一关,仅仅是砰了一下,却惊天动地重复响在了每个人心上。女婿越发坐不住了。
女儿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转,娘也不便多留,就拿了些衣料食品什么的给女儿带去,说,自己好生过吧,你爹爹就那么个脾气你也别怪他。也许,也许过一阵子气消了就会好的,那时你再回来看看爹娘吧。
从轻盈的小鹿到悲伤的背影,只是转瞬之间。二茳从此很少回来,在那偏远的山区,任花开花败。
十一
父亲志清患病的消息传来时,芯漂泊在大洋彼岸。她拼命地打越洋长途电话,一遍又一遍地问:要不要我回来?
父亲说,你回来不就没有回头路了么?那些年的苦不就白吃了么?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呢?我不想你因为我而放弃你的追寻,我心里会不安的。老人在电话那头先抽泣,继而大哭,情绪控制不住了,喊起来,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回来啊!
父亲执意不让芯回。说,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再说就是不行了,你回不回,都没用。
芯叹息,父亲这一生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从未卷入任何斗争旋涡’既是幸运,也与他内敛谨慎有关。在“一打三反”中,他竟连用了公家的几张纸写了封家信都要检讨。讲起来让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改革开放,他依旧不腐不贪两袖清风;握有单位人事大权,却没给子女弄个一官半职;甚至当人家好烟好酒送上门来求他帮忙,他也是秉公办事。直不笼统叫人把礼品拎走。人世沧桑,社会观念瞬息万变,早就乾坤倒转……你在位时人对你点头哈腰,啥事跑得屁颠屁颠的,一旦不在位了,患病就诊连要个车都难矣!一谈起他也是牢骚满腹,可牢骚管暗用?想开了,索性去和一班老友打打麻将,快活一天是一天,得过且过吧。早年无钱买牙刷,他一口牙过早脱落。他口齿漏怨风对女儿说,我们吃过的苦你没吃过。但我也明白你有自己的、与追求,不要轻易放弃。
人生会如此进退维谷,思绪如此纷繁、沉重。是啊,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选择。正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的年轻人也都有他们的激情和梦想所在。可是我们苦苦追寻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那些迟来的,被这样或那样的现实打了折扣的自由?还是曾经有过又幻灭的梦?
她托朋友带钱给老父亲养病。朋友探亲回国,见饱受疾病摧残和精神折磨的老人在秋风中瑟缩,好似一片枯黄的叶子,随时就要凋零飘落。
听了朋友的转述,芯神情黯淡。一番感慨,引出万千苦辣,肝肠寸断却仍不能言说的酸楚。陷入诸多困惑矛盾之中。想起一些留美学生,国内亲人患病,顿时陷入身份未解决和亲情的矛盾撕扯中。一个来美国学美术的上海人,10年后才有机会回国。一说就难过,为没能给父亲送终而抱恨不已。
旧日同事听说芯父亲身患疾病,芯情绪低落,徘徊在走与
留之间就给芯邮来一封信。芯拆开信封,内有一张问候卡,一百五十美金的支票。卡上写道:一点心意,给你父亲多打电话吧!
喉咙哽塞,一片雾也似的热潮骤然涌上她的眼帘。芯在烟雨凄迷的异乡街头疾步而行,流在嘴里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她不停地打电话给亲朋好友,四处联系比较哪家医院条件的优劣,医疗水平的高低,找专家了解治疗方案。给父亲精神动力和参考意见。鼓励他战胜病魔,让他接受手术治疗,加强心理和生理的抵抗力。
那些时日,说是高干病房没床位。父亲的病床就凑合着搁在肿瘤科的走廊门边。寒冬腊月天,人们出来进去的,带起阵阵小风和响动,加上穿堂风,老人直咳嗽,夜晚也睡不了。继母阿姨央求大夫护士帮个忙,说,这样的环境叫好人都挺不住,更何况还是个风烛残年、疾病缠身的老人?他们无奈摊开两手:病人多了没床位,你有啥法子?亲戚便去找熟人朋友帮忙,好容易才搬进了病房。谁料病人住了院,手术却迟迟不进行,也不知何故?一会儿医生检查说有点肺气肿,不碍事;一会儿又检查说身体有炎症,不便手术,这样拖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芯很狐疑’觉得有些不对劲’便频频挂电话询问。
阿姨说,我和你爸爸急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医生光检查,不动手术,这样拖下去怕是不好。听同病房的人讲,一定要送红包,手术医生要送,麻醉医生也要送,护士也要送……大约各是多少,不能不送。亲戚却说不需要送,是通过院方领导打了招呼的,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朋友还要说什么呢?
芯问过亲戚,亲戚说送他们好烟好酒都不收,说要请客吃饭也不吃,医生说他没空,刚买了房子,要装修。
“怎么办啊?,,阿姨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那头哭起来。她不仅担心父亲的病,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以后的生活,伤心忧虑就随着泪水一并流了出来。
这边芯一筹莫展。她对国内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些隔膜了,毕竟出来几年,事事都有了变化。她左右为难想了一阵就给北京朋友挂电话,说医生的情况。朋友说,该给的全得给。打过招呼有什么用?我父亲病重住的还是最好的301医院呢,连看护都得打点。你赶快跟家人说,千万别拖了!
芯明白了医生说“没空,要装修房子”的潜台词。她赶紧给、与家人电话,让把该送的红包全部送到。第二天,医生就安排做缘了手术。
芯后来给父亲电话。父亲感激涕零说她建议很及时。还颤颤巍巍地告诉芯,你大姨,前天走了。
芯半晌没说话,她知道大姨和外婆患的是一样的糖尿病,富贵病,被慢性病折磨了很多年痛苦不堪。想吃,不停地想吃,又不能多吃,总是被欲望和克制欲望的痛苦纠缠着。原本丰盈圆润的身子,最后竟零落成了皮包骨。
其实你大姨早先对我是很好的。父亲告诉芯,当初革大一个班百把学员,吃饭时七八个人一锅饭,一盘菜。因菜少,三夹两夹,盘子就见了底。对狼吞虎咽的青年来说,简直是不够塞牙缝。
你大姨总会悄悄地拨些菜在我碗里;有时是埋在饭里几片肉,还有香喷喷的酱菜。不晓得是她家人捎来的,还是她自己烧的。那年我生病,她也带些营养品来破庙里看望我。父亲很感慨,孩子气地对芯更正补充大姨曾经说过的话。应该说她一直对我是很好的,不光是我对她好。
芯忍不住问,那你是她的入团介绍人?
父亲说当然。
那二姨呢?
父亲说不是,她来得晚,好像是三班的吧?当时是好几个班都是全班都参加志愿军了,除了个别的,像二茳已经报名而没走成,是偶然。
整班人马的上去,零零星星的下来。几十年后,一次老同学聚会,找不到几个熟悉的面孔。大开大阖,九死一生。甚至几乎都没见回来。那都是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渐渐苍凉的记忆和声音模糊了,遥远了。远的就像已经蒙尘的,被人早已淡忘了的历史。
芯坐在旧金山北岸区斜阳西下、尘烟浮动的阴影里,想着父亲和大姨之间、与母亲三姐妹跌宕曲折的爱情故事。缘分依旧,而情已不再。或是情怀依旧,缘分不再。
问世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那么一次,在你放手,转身的一刹那,就完全改变。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远分开了。
一肚子零散细碎的回忆,在孤独的一刻消融。
蓦然就看见,父亲老泪纵横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