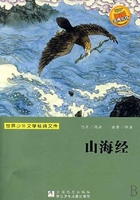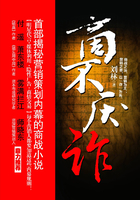椹、枣、桃、橙、橘、蒲萄、龙眼、荔支,都指称水果,除“椹”今称之为“桑果”,这些词一直到现代汉语中基本没有变化。《后汉书》中“桃”、“橘”各3见,“椹”、“枣”、“蒲萄”、“龙眼”、“荔支”各2见,“橙”1见。
小结:汉语中往往指称作物的词通常也指称作物的颗粒,我们把这部分词都纳入“果”的概念下,《后汉书》中“果”语义场包括与粮食作物相关的和与瓜果类相关的两个部分,古汉语对粟、黍、稻、麦、菽各种细致的指称较多,相比现代汉语,我们常用的仅有“稻、麦、豆”了,或是由这些词组成的复音词,如:大麦、小麦、黄豆、红豆等,而对于瓜果的专名,旧有的基本保持一致,同时现代汉语中还增加了很多以前没有的新的名称,人们把目光渐渐从作物中投向了其它方面,比如水果,语言中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物质逐渐丰富的反映。
2.叶(Leaf)
“叶”位于《百词表》第25位。
叶:《说文·艸部》:“叶,草木之叶也。”《广韵·叶韵》:“叶,枝叶。”早在甲骨文时代,人们对植物的叶子就有了认识,如核心词“果”中的成员“禾”,它作为象形字,在甲骨文字形中的枝叶非常明显。《后汉书》中“叶”表叶子共14例,分别是“枝叶6”、“枯叶1”、“瓠叶1”、“漆叶3”、“葱叶1”、“竹柏叶2”。可见“叶”既可泛指,也可与草木连用,表示某种叶,这种组合关系已近于现代汉语。
藿:《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毛传“菽,藿也”孔颖达疏:“菽叶谓之藿。”《史记·太史公自序》“藜藿之羹”张守节正义:“藿,豆叶也。”《后汉书》中“藿”5例,其中“藜藿”3见,如《崔骃列传》:“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
葭:《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非有葭莩之亲”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葭,芦叶也。”《后汉书》中“葭”表示芦叶有2例,可见“蒹葭”、“葭莩”。
桑:《玉篇·叒部》:“桑,蚕所食叶。”《后汉书》中“桑”指桑叶仅1例,见《郑孔荀列传》“桑落瓦解”,这里“桑落”指桑叶枯落,李贤注曰:“《诗·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小结:《后汉书》中“叶”概念下的词较少,只有“叶”、“藿”、“葭”、“桑”4个,而且在文献中的用例也很少。其中“叶”既可以泛指,又可以表示某种具体的叶,这种用法搭配的全面可能是“叶”语义场下词目较少的原因。到了现代汉语中,凡叶子都用“叶”或是由“叶”组成的复音词表示,比如在古汉语中“桑”可表示桑叶,“葭”可表示芦叶,而在现代汉语中必须用“桑叶”、“芦叶”指称。
3.根(Root)
“根”位于《百词表》第26位。有关“根”的研究,已有一些重要的成果。
《说文·木部》:“根,木株也。”“柢,木根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蔓根为根,直根为柢。”可见“根”是树的旁根,而“柢”是树的直根。又《韩非子·解老》:“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是不是在韩非子的时代,“根”、“柢”还存在语体色彩的差异?《说文·木部》:“本,木下曰本。”王筠《句读》:“本,今谓之干者是也。”“本”指树冠以下,包括树根、树干两个部分。《说文·木部》:“株,木根也。”段注:“株,今俗语云桩。”《慧琳音义》卷三“株杌”注引《考声》云:“株,杀树之余也。”可见“根”是树根深入地下的部分,“株”是“杀树之余”,即露在地上的树桩。关于“根、柢、本、株”,很多学者做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来看看《后汉书》中的具体使用情况。
《后汉书》中“根、本”均可以既指树根,又指草根,如“桑末寄夫根生兮”、“麦根”、“树本”、“垂颖而顾本”,其中“根”还可用于泛指,表示草木根,有3例,其主语为“万物”或“草木”,如《五行志》:“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吴延史卢赵列传》:“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而在引申义上,“本”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根”,且“本”的意义系统中,呈现出各种丰富的义项,可表示“根本、终始、原本、农桑、本性”等。“柢”在《后汉书》中共3见,除2例用于通假外,“柢”用于引申义,表示根本,不表示具体的草木根,如《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株”只表示树根,和池昌海先生对《史记》的考察“株”都用作喻体不同,《后汉书》中“株”3例都用其本义,如《朱冯虞郑周列传》“陵树株蘖”,其中“株蘖”即是伐后的树桩上萌发的枝条。尽管有着上述种种的不同,《后汉书》中仍见两两连用或对举的例子,如“根本5、本根4、根柢、深根固本”,其加强了语势,强调了意义,同时也调整了音节韵律,增加了声情美。从总体上看,《后汉书》中表示“草木之根”主要用“根”。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中有“本、株”的量词用法,如下例:
(1) 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李陈庞陈桥列传》)
(2)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余,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备具。(《五行志》)
根据《汉语大字典》,“本、株”用作量词最早援引的是《论衡》和《三国志》中的例子,可知“本、株”名词量词化,是东汉魏晋时期新出现的语法现象,并在《后汉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但并不广泛。
《说文·艸部》:“荄,草根也。”又《玉函山房辑佚书·通俗文》:“韭根曰荄。”可见“荄”可泛指草根,也可特指韭根。《后汉书》中“荄”2见,均泛指草根,如《卓鲁魏刘列传》“养其根荄”李贤注:“荄,草根也。”。
“芋魁/芋渠”特指芋根,《后汉书》中各1例。《方术列传》“亨我芋魁”李贤注曰:“芋魁,芋根也。”又《马融列传》“芋渠”李贤注曰:“芋渠即芋魁也,根可食。”
《说文·艹部》:“蒂,瓜当也。”徐锴系传:“花叶之根曰蒂,树之根曰柢。”《文选·左思〈吴都赋〉》“扤白蒂”刘逵注:“蒂,花本也。”又《文选·宋玉〈高唐赋〉》“朱茎白蒂”李周翰注:“蒂,花根也。”《后汉书》中“蒂”2例,见于《蔡邕列传》“华离蒂而萎”,《五行志》“八瓜同蒂”。
小结:正名辨物,各有殊称,古人常用不同的词表现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后汉书》中“根”语义场下,分为树根、草根、花根3个类别,包括“根、柢、本、株、荄、蒂”6个与之相关的词,其中“根”可泛指根,是所有表示这一概念的词的上位词和基本词。到了现代汉语中,“柢、荄”具有浓郁的文言意味,“本、株”使用更多的是其引申义和量词的用法,“蒂”则常说为“蒂把儿”,“根”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
4.皮(Skin)
“bark皮”和“skin肤”在《百词表》中分别位于第27位和第28位,bark本义指树皮,后来引申可以表示人和动物的皮,而skin这个词正好相反,其本义是人的皮肤,后又引申出植物或动物的皮,因此bark和skin在语义上是有交叉之处的。联系汉语实际,我们将“bark”和“skin”放在一起考察。有关“皮”的研究,已有一些重要的成果。
“皮”和“肤”常相对言。《说文·皮部》:“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段注:“因之所取谓之皮矣。引申凡物之表皆曰皮。”王筠《句读》:“人谓之肤,兽谓之皮。”又《说文·肉部》“胪”下谓:“皮也。从肉卢声。”段注:“今字皮肤从籒文作肤,肤行而胪废矣。”汉武帝时有官名为大鸿胪,据唐司马贞索隐:“胪,附皮,以言掌四夷宾客,若皮胪之在外附于身也。”可见“胪”在西汉还通行。《后汉书》中表皮肤则已用“肤”,而“胪”仅见于官名。关于“皮、肤”,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是指称对象的不同,王凤阳先生(1993:129)指出:“‘皮’和‘肤’最初都是特称,在先秦区分得相当严格,一般不通用。由于‘皮’的应用率高,在使用中逐渐泛化,成为外包表层的通语,所以人的皮肤有时也用‘皮’来表示了。战国、秦汉时期,这种以‘皮’代‘肤’还是个别的,只用于割剥皮肤的场合;中古之后,‘皮’就逐渐取代了‘肤’兼表人的皮,尤其是当‘皮’与‘骨’、‘肉’等泛称对举的时候尤其明显。”我们来看看《后汉书》中“皮、肤”的具体使用情况。“皮”本义为动词,但名词却更常用,《后汉书》中“皮”均用为名词。从上表我们可知,“皮”所指较全,可以表示人皮、植物皮、动物皮,还有引申义的用法,其中以表示动物皮居多,由于“皮”与“被”、“披”同源,所以泛化后一切披覆于物体表层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皮”。而“肤”没有表示动物皮的用例,多用来表示人皮,表示植物皮仅1例,查《故训汇纂》,其征引的例子是《文选·嵇康〈琴赋〉》“清露润其肤”张铣注:“肤,谓木皮也。”据吴宝安对西汉核心词的研究,未曾发现“肤”用来表示植物皮的,我们设想,“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可能有过词义扩大的用法,不过这种趋势最终没有继续下去。
“皮”、“肤”都能表示人的皮肤,所以可以“皮肤”连用,《后汉书》中1例,见《皇后纪》:“先是数日,梦有小飞虫无数赴着身,又入皮肤中而复飞出。”那么当“皮”、“肤”都指人的皮肤时,有没有什么不同呢?《灵枢·水胀》载: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这里明确提出了皮与肤存在“之间”,可见皮与肤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皮”是人体的表面组织,同时也是毛发生长的地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皮毛的关系;而“肤”是皮下覆盖的组织,《论语·颜渊》“肤受之愬”皇侃疏:“肤者,人肉皮上之薄皱也。”颜师古注:“肤受,谓入皮肤至骨髓,言其深也。”可见“肤”是介于皮肉之间的组织,在皮的里面。《后汉书》中如“以绳贯脊皮”、“肌肤横分”,也可以体会出“皮”、“肤”的差别。但到了现代汉语中,“皮”、“肤”的这种差异似乎消失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护肤”、“换肤”、“嫩肤”,其实说的都应该是皮。
《玉篇·革部》:“革,去毛也。”《左传·隐公五年》“皮革齿牙”孔颖达疏:“有毛为皮,去毛为革。”可见“皮”、“革”区别在于是否带毛。“革”在《后汉书》中指皮有11例,如“马革裹尸”、“玉壶革带”、“革囊盛血”、“绨袍革舄”、“缝革为船”等。又《广韵·微韵》:“韦,柔熟皮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五“皮革”注:“熟者名韦,生者名革也。”《易·遯》“执之用黄牛之革”惠栋述:“始拆谓之皮,已干谓之革,既熟谓之韦,其实一物也。”可见“革”、“韦”的区别在于生或是熟。《后汉书》中“韦”指皮有7例,如“韦带”、“弦韦为佩”、“佩韦”、“韦衣”、“韦裤”、“刺韦作文绣”。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革”一般坚韧耐用,而“韦”较为柔软适体,当然有时“革”、“韦”也可以在行文中灵活通用,如上述《后汉书》中有“玉壶革带”,也有“韦带”的说法,分别见于《杨震列传》:“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
“犀”可表示犀皮。《法言·孝至》“带我金犀”李轨注:“犀,犀皮,剑饰。”《后汉书》中“犀”指犀皮1例,见《朱冯虞郑周列传》“驳犀具剑”。
“糠”、“甲”可表示植物皮,《类篇·米部》:“糠,谷皮也。”“糠”指谷皮在《后汉书》中5例,可见“糟糠”、“糠秕”,现代汉语中仍被广泛使用。又《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后汉书》中“甲”指草木之皮的仅1例,见《肃宗孝章帝纪》“萬物莩甲”。
“腠”、“理”表示人皮肤的纹理,《集韵·候韵》:“腠,肤理也。”《慧琳音义》卷八十八“腠里”注引《考声》云:“腠,皮肤内也。”又《荀子·解蔽》“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杨倞注:“理,肌肤之纹理。”《金匮要略》:“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可见,“腠”、“理”是有区别的,“腠”是肉眼不可见的,在皮肤内,而“理”是肉眼可见的表皮纹路;当然二者也常连用,《后汉书》中“腠理”1例,见《方术列传》“腠理至微”,李贤注曰:“腠理,皮肤之间也。”
“胝”、“茧”表示人皮肤上的老茧,《说文·肉部》:“胝,腄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腄,俗谓之老茧。”《广韵·脂韵》:“胝,皮厚也。”又《战国策·宋卫策》“百舍重茧”吴师道注:“茧,即趼字。”《集韵·先韵》:“久行伤足谓之趼。”可见,“茧”为“足胝”,而“胝”表示皮厚,并不仅限于指足,如《荀子·子道》中“手足胼胝”。《后汉书》中表示老茧,“胝”1例,“茧”2例,见《桓谭冯衍列传》“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皇甫张段列传》“士皆重茧”。到了现代汉语中,“胝”仅见于“胼胝”,而“茧”的词义有所扩大,我们所说的“茧子”可以指手掌或脚掌上的老茧,不再仅仅是“足胝”。
小结:《后汉书》中“皮”概念下,包括动物皮、植物皮和与人皮相关的3个类别。我们着重描写和分析了《后汉书》中“皮、肤”的具体使用情况,较先秦时期“皮”用于人多见于医籍相比,《后汉书》中“皮”的使用更为广泛,我们把它作为上位词。而“树肤”一词及《文选》中“肤”用于树的例子,说明可能在魏晋时期“肤”也有过词义扩大的用法,但最终成了古语词,现代“肤”只在“皮肤”、“肤色”、“肌肤”之类的词语里作为义素存在了。程湘清先生(2003:12)从语义的深层分析了“皮”、“肤”的义位构成:皮=属于人或生物+附在人体或生物表面+呈平面形或圆壳形+一层薄的组织,肤=属于人+附在人体表面+呈平面形+一层薄的组织;并进一步指出“皮”的义位能够囊括“肤”的义位,“皮肤”的义素也同“肤”的义素合而为一。“皮”进入基本词汇,“皮肤”是一个不平等联合词。其它如“革、糠、茧”现代汉语中还常用,“韦、腠、胝”则有鲜明的文言色彩,而“犀、甲、理”则似乎不直接用来表示皮了。
和先秦“皮”语义场相比,《后汉书》中与“皮”有关的词大为缩减,表现为具体概念的词在减少,而抽象概念的词使用频率和范围在增多,如先秦表示竹皮用“筠”、表示木皮用“萚”、表示虎皮用“皋比”,而《后汉书》中直接用“竹皮”、“木皮”、“虎皮”,出现了很多以“皮”为语素的复合词,这种单音节词复音化从词汇发展上来看是表达经济简单的需要,从认知上看,也符合人类认识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再如,《后汉书》中表示犀皮用“犀”,而现代汉语就得用“犀皮”表示了。
5.肉(Flesh)
“肉”位于《百词表》第29位。有关“肉”的研究,已有一些重要的成果。
《说文·肉部》:“肉,胾肉,象形。”段注:“生民之初,食鸟兽之肉,故肉字最古。而制人体之字,用肉为偏旁,是亦假借也。人曰肌,鸟兽曰肉,此其分别也。”《慧琳音义》卷七十三“肉团”注:“凡有气血之类,皆谓之肉也。”可见“肉”本指食用之动物肉,借指人体之肉,后则可用于泛称。又《考声》:“肌,皮内肉也。”《玉篇·肉部》:“肌,肌肤也。”“肌”则相反,本指人体之肉,也可指食用之肉,如《急就篇》“肌脯醋鱼臭腥”颜师古注:“肌,肉也。”但这种例子极少,绝大多数情况下“肌”仅用于人。考查关于“肉、肌”的各种注解,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肉”多用于动物,而“肌”特用于人,两者存在适用范围和语用的区别,以段玉裁、王力先生为代表,大多数学者从此说;其二,认为前者的这种区别是“强为分别”,“肉”指动物肉是文意训释非词义训释,以徐灏、杨凤仙为代表。我们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下面来看看《后汉书》中“肉、肌”的具体使用情况。
《后汉书》中“肉、肌”都既用于人,也用于动物,其中“肉”还可表示乐声,并有动词的用法。当用于人时,“肉”用例几乎是“肌”的5倍,这与先秦的情况已有了非常大的不同。王力先生(1980:570)曾指出“肉”用于人的两个条件:(1)与“骨”对称的时候,(2)“肉刑”也不称为“肌刑”。在《后汉书》中,连用20例,对举2例,如《文苑列传》:“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还有“肉袒”的说法,甚至直接出现了“人之肉”、“女肉”、“皮肉”,并有“肌肉”。连用1例指人,见《独行列传》:“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后世“肌”、“肉”渐渐混用,都可用于人,“肉”也就是“月”,成为了一个偏旁部首,所有涉及人体组织的字,都从“肉”。而当用于动物时,《后汉书》中几乎全是用“肉”,并有多种组合,可以作“食、赐、啖、用、割”等动词的宾语,也可以在偏正式中充当修饰成分或是中心语,如“肉羹、牛肉”,也可以和“米、酒、粱”组成并列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肌”与“骨”对称1例,如《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乌抄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猒。”此例虽然带有比喻的意味,但“吞肌及骨”中的“肌”显然也是表示可食之肉。总体来看,“肉”在使用频率、语法功能、语义范围、搭配能力等方面都比“肌”有明显的优势,《后汉书》中“肉”为上位词和基本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