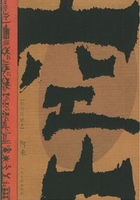1993年6月23日,世界禁毒日。
中国航天城西昌。
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凉山州西昌市公开处理毒品犯罪分子宣捕宣判大会正在进行。在人民法官庄严的宣判下,流窜在成昆线上,往来于云南、成都、广州等地的重大毒品犯罪分子张成华、朱兴华、杨生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重大毒品犯罪分子文德等六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在各族人民拍手称快的赞叹、议论之中,记者听到了人们对罪犯的诅咒,对公安干警的赞扬,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惜;也听到对毒品泛滥、屡禁不止,甚至对罪犯处以极刑也难以禁绝的迷惑和种种疑问。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记者前后花了半个月时间,采访了有关干警,察看了戒毒所,访问了罪犯家属及部分吸毒者,写成这篇缉毒、禁毒的“大扫描”。
死灰复燃 沉渣泛起
中国新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披露,1991年、1992年的两年间,中国在缉毒执法工作中仅海洛因一项就查获六千多公斤,打击处理一万五千多名贩毒犯罪分子。他指出,尽管如此,毒品犯罪仍有发生。其主要表现是:在暴利刺激下,贩毒罪犯持续增多,通过云南的边境贩毒有增无减,内外勾结,结伙作案,手法升级,对抗性强;在边远地区非法零星种植罂粟依然存在的同时,又新出现了制造加工“冰毒”的犯罪活动;吸毒人数正在增加,复吸率高的问题没有明显改变。陶驷驹在解释“这两年中国毒品为何越禁越多”这个问题时说:中国毒品问题的发展,主要是受过境贩毒的影响。
记者在凉山缉毒大队干警的协助下并通过他们的介绍,得出了成昆线是贩毒“通道”或“走廊”的结论,从而解开了攀西地区许多干部群众对贩毒为祸、吸毒成灾迷惑不解的思想疙瘩。
世界毒品三大基地中,位于东南亚的“金三角”位居第一。这个“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的交界处,同中国的云南、广西相邻。它是一个“三不管”且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据专家估计,“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有六七万公顷,年产鸦片达六七百吨,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提炼成吗啡和海洛因后,走私贩卖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价格贩得越远越昂贵,如当地每公斤海洛因卖1000美元,到美国可卖20万美元,如果零卖可达200万美元,是世界上最暴利的买卖。
贩毒、吸毒这股浊浪,近几年来从“金三角”涌进云南,流经攀西,通过成都再到广州、上海,投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广大地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凉山逐渐成为毒品贩运的过境地带。凉山,东连宜宾,南邻攀枝花,西北与甘孜接壤,北面和东北与雅安、乐山毗邻,东南、西南同云南仅一江(金沙江)之隔,交界线长达一千公里,有六条公路,四座跨江桥和近百个渡口。成昆铁路经过全州六县一市,国道108线纵贯全州,还有民航班机往返于成都、西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历史原因,遂成为毒品流入中国的集散地和中转站。记者获悉,贩毒人员逾千,除了居民、农民、待业人员、劳改犯和劳教释放人员外,还卷进了少数干部、工人、学生和妇女。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还有年未弱冠的少年。瘾民比贩毒者高出几倍,各行各业都有。社会上早已绝迹的“烟馆”如今在城乡商旅云集的地方悄然兴起。贩卖和吸食的毒品以鸦片、海洛因、黄皮、盐酸二氢埃托啡为主,有的还发展到阿卡因、麻黄素、咖啡因。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是种植罂粟、盛产鸦片的地方,“好田好地种罂粟,男女老少吸大烟”,是尽人皆知的。那时,在凉山、西昌广袤的土地上,每到风和日丽、雨水充沛的夏季,从平坝至二半山,盛开的罂粟花代替了其他植物。据凉山州文史资料记载,鸦片烟从清代流入凉山和宁属,两百年遍及彝、汉各民族的杂居和聚居区。“遍地烟花,满城烟馆,处处烟摊,家家烟鬼。”有些国民党官兵用鸦片“提神打仗”,人称“双枪丘八”;地方豪绅和奴隶主靠“种烟发财”和“种烟蓄奴”,并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称霸一方,冤家械斗不息,老百姓苦不堪言。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当时的国民党参政员、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民主人士黄炎培,亲临西昌、凉山视察,目睹“满地鸦片,民众为勒索烟款,遮道跪哭,鸣冤诉苦”,悲愤地写下了“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簇拥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的《越西叹》诗句。
1950年后,西昌、凉山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基本上禁绝了种烟、贩毒的犯罪活动,大批“瘾君子”在卫生部门的监督和帮助下,也从“烟鬼”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是,几十年来,经过十年动乱,贩毒、吸毒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贩毒罪犯则向智能化、武装化、技能化、职业化、低龄化、国际化、集团化发展,这些罪犯屡遭打击后不断改变对策,变换手法和活动方式进行贩运,武装和暴力对抗性案件也时有发生。
随着国际毒品消费市场的发展,“瘾君子”成倍增加、蔓延。据国际上的统计,全世界至少有四千万人被“毒弹”打中,按总人口平均每一百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烟鬼”。其中美国是当今头号毒品消费大国,吸毒成为风尚和时髦。在大量毒品过境的成昆线的攀西走廊中、在地区接合部、边远山区、林带边沿等地偷种罂粟的,在城镇、乡村开地下烟馆的,也是屡见不鲜。这些贩毒、吸毒者,盗窃、抢劫、赌博、卖淫,无恶不作,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利剑出鞘 铁警雄风
在凉山,缉毒禁毒,打击罪犯,保障人民健康,维护社会治安,最权威的当数凉山州公安局缉毒大队,其骨干大都是彝族、汉族年轻人。
我们采访了缉毒大队队长、彝族警官马玉松。
马玉松从公安校毕业后,干刑侦和缉毒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在局领导的指挥和战友的密切配合下,他先后参与侦破治安、刑事案件上百起,缴获鸦片三万四千五百多克,缴获海洛因一万七千多克,缴获黄金九千六百多克。此外,缴获赃款四十多万元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赃物。他的事迹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他的形象亦曾在电视荧屏上出现过……
十年来,马玉松对刑侦和缉毒工作,从内到外,从领导到干警,从侦破、取证、缉拿一整套业务乃至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工作制度、财物管理等,他都建立了一套“本本档案”。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还是记在他的脑袋里。下面是有关他的几个事例。
之一:拜师授业
马玉松的授业老师就是凉山州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余柱江。十年前,小马在四川省公安校毕业后分配到凉山州公安局刑警大队,第一个带他办案的是余柱江。余是老公安、老侦察,五十年代初进凉山,熟悉业务,深谙民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待人和气,办事认真,能够吃苦,乐于助人。用马玉松的话说,就像哥哥帮弟弟、教师带学生,无论是分析案情,追踪线索等,无一不是言传身教。马玉松也很用心思、动脑筋,一个案子的分析讨论结束后,他就默默地作一次回忆对比,然后自己出题自己回答。一回生,二回熟,他慢慢学会独立办案了。
之二:办第一个案子
1979年,某县城发生了一起奸杀十三岁幼儿的恶性案件,马玉松上岗不久就跟着老师余柱江投入侦破工作,一头扎进群众中,“泡”了半年,调查访问近百人,同犯罪嫌疑人交“朋友”,从无从下手,到发现线索,集中焦点,直到最后侦破了这一疑难案件。
之三:“你就是那个马……”
“从地上冒出来的?”这句话是犯罪嫌疑人韩某落网后对马玉松和大队的干警说的。事情是这样:1989年,凉山一个省属企业的党委副书记韩某利用手中的权力,往来于县城和西昌,买卖黄金,谋取暴利。当他在西昌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交出一大碗闪光的金子,接到的却是一副锃亮的手铐。韩某这才明白,同他做这笔交易的竟是一位公安人员,所以他惊奇地说:“你就是那个马——玉——松?”
之四:震慑罪犯的“5·18”
凉山公安干警一举侦破“5·18”特大贩毒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个案子,除了毒品的数量大得惊人外,作案的手段、犯罪的人数、涉及的地区等也是罕见的。这个案子,凉山州公安局的干警在上级公安机关和友邻公安部门的支援配合下,于1991年5月18日侦破,当场缴获大量毒品,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擒,跨省区、跨国界的犯罪集团纷纷落网。四川电视台在6月24日播发了新闻,6月26日世界禁毒日,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这条新闻。9月26日,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广场,公开宣判了犯罪集团的九名罪犯死刑。广大干部群众称赞凉山州公安局侦破“5·18”特大贩毒案是“连中三元”,缉毒干警是“三元魁首”。
缉毒禁毒 任重道远
在进入西昌戒毒所采访时,我们目睹了“瘾君子”的种种痛苦和自戕自弃的惨状。
西昌戒毒所设在风景秀丽的城郊的一个四合院内。我们去采访时正是自由活动时间,在那里强制戒毒的几十个男男女女,都在场坝里自由活动。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聊天的、下棋的、看书的、洗衣服的,一派平静的气氛。在干警小罗、小方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各种类型的吸毒人员。
人物一:某女,十六岁,母亲早逝,十三岁被生父侮辱后流落四川、安徽、徐州等地乞讨,打工,卖淫,并吸毒成瘾。到了戒毒所,她想到了她不幸的身世,毒瘾发了更是痛不欲生。为此,她曾用头撞过墙壁,掐过自己的大腿,用香烟头烧过手臂……她一面痛哭,追悔,一面撩起衣袖让我们看她烙下的伤痕。她在回答为什么要这样自戕自残时说:染上毒瘾,一旦瘾发了,又没有毒品吸食,就用这种方式来转移痛苦。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引起了记者的同情和联想。我们曾读过一本书——《世界毒品风云》,书中有这样一段:“那些高贵的美妇人当你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她都会觉得是对她的一种亵渎时,她却突然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像最下流的娼妓似的脱下衣服,浑身发抖地跪在你面前,求你随意摆布她,只要给她一包粉。”可见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灵魂被扭曲了,就会道德沦丧,尊严和人格荡然无存。
人物二:某女,二十多岁,前几年与沿海一商人成婚。从那以后,虽然谈不上平步青云,腰缠万贯,但南来北往,游山玩水,却也不愁钱花。就在这个时候,她因听人说吸毒如何如何舒服,并会进入“欲仙欲死”的神仙境界等而吸了毒。她告诉记者:她是因为好奇而吸毒,是因为操档次而吸毒,结果上当了。
据管理人员介绍,这个女人已进戒毒所两个月,基本上没瘾了,不日即可回家。她说要感谢缉毒干警及时抓获并强制她戒毒,把她从堕落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人物三:这是一组年轻的男性。我们在同他们的接触时气氛和谐,摆谈中他们的谈吐自如,但话语有时显得粗野。我们拉开了话匣子。
青年甲:某单位职工,平时纪律性极差,并有赌博的恶习,在哥们儿的引诱下他开始吸毒,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只好被“请”进戒毒所。毒瘾发了就用刀子在手臂上割了许多道口子,用香烟在腿上烙了许多疤痕。经过几个月的强制戒毒,已有悔改表现并开始悔恨自己的作为。
青年乙:是父母亲送他到戒毒所的。两个多月过去了,已经基本消除毒瘾。摆谈中,他悄悄告诉记者,登报时千万不要写出他的名字。由于他的毒瘾不甚严重,表现较好,所以戒毒所的同志对他的管教是施以“宽大政策”的。
我们结束了对戒毒所的采访,正准备驱车回城时,一辆警车驶进戒毒所,嘎的一声停在面前,车上下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一问,才知道是一个吸毒兼贩毒的重罪犯。她已经八十岁了,精神却很好。当小罗他们把她送到所里时,她先是装出一副可怜相,企图求得宽恕,续而又觅死寻活、赌咒发誓,企图蒙混过关。就在她横扳竖跳、呼天喊地时,从她的下身掉出一块用玻璃纸包着的湿漉漉的大烟土,她开头的那股泼劲一下子消失了。当记者询问其贩毒的历史时,她供认不讳地回答:“黑”的(指鸦片)卖了几十年了,“白”的(指海洛因)最近才搞到手,贩卖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
上述事实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吸毒贩毒是祸水,是杀人的软刀子,是罪恶的种子,是各族群众和全世界人民的公害。联合国第四十四届禁毒特别会议通过反毒品《全球行动纲领》,宣布1991年至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十年。我们国家已作出决议,采取行动,积极配合,取得显著成绩。当前,极需协同作战,综合治理,群起而攻之,将那些吸毒贩毒的罪犯淹失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注:此稿同罗桂英同志合写。罗桂英,彝族,凉山州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外宣办副主任。
(1993年10月26日《攀西开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