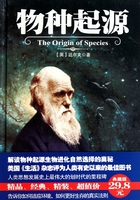我的命运在1994年的春天出现了转机。一天,我途经多伦多郊外一家餐馆吃饭,发现女老板说一口醇厚的安徽话。在多伦多的洋气氛和华人聚集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到熟悉的乡音,我立刻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女老板也差点“两眼泪汪汪”。这位名叫夏虹的女同乡,先是嫁到香港,后随丈夫移民到加拿大的,近十年了。她的丈夫是位医生,两年前一个大风雪的晚上,医院来了急电,要求他出诊。他因习惯了冷天生活而疏忽了,只披了一件单衣便驱车出外应诊。没料到路上一阵大风雪,将他的车子盖住,“死了火”。因为他住在人烟稀少的郊区,很少有巡警和路人经过,等到发觉的时候,他已经冻死了。成了寡妇的她,就带着六岁的女儿靠开这么一间小餐馆艰难度日。
我对这位同乡非常同情。那间餐馆,位置偏僻,饭菜品种单调,每天的营业额不过二三百元,应付了店铺开支但不够支付工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只好自己一脚踢又当厨师又当服务员。
我主动提出和她各出一半资金合开这家小餐厅,夏虹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因为我曾在其它餐馆打工几年,对餐馆管理和菜品制作有较丰富的经验,我就负责厨房烹调,夏虹则负责店面服务。两个人配合十分默契,营业额直线上升。一年后,我们赚了一万多加元。然后我们又扩大了店面,招了新服务员,生意越来越红火。
夏虹虽不是很漂亮,却有难得的温柔善良。一年多的患难创业,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中秋节晚上,多伦多上空的月亮明亮似银盆,我们都想家了。那个夜晚,夏虹扑到了我的怀里,我紧紧拥抱住了她,感到的不是情欲,更多的是温暖。
夏虹更信任我了,她把餐馆全交我负责,自己一心一意照顾刚上小学的女儿。她还上了一个夜大学,学习服装设计。她说她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而不是餐馆老板娘。夏虹渴望和我结婚,组成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永远在加拿大生活下去。
但我却不想留下。我一年比一年更深切地体会到,在加拿大没有我的位置。我的事业是摄影和艺术,在加拿大我就永远会和我喜欢的工作擦肩而过。我越来越想回到祖国来,我思念我的双亲,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事业。
泰戈尔说:“我们一次次地飞走,是为了一次次地回来。”
只有出国多年,饱尝那份“洋插队”辛酸苦辣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家乡对自己生命的意义。1997年的岁末,我把已有十几名员工的餐馆交还给夏虹,并与她依依话别。我说,如果我们有缘,就回国来找我。夏虹噙着泪水,频频点头。
我走时是双飞双栖,回来时却是孑然单影。我在多伦多机场走上舷梯的那一刻,猛然回头,整个多伦多的背景,全是郭莎莎放大到极致的面孔,美丽又冷漠。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仍然是那么爱她,那么难以将她忘怀。
Δ酒别
□野风
盛夏的黄昏里我下班回家,丈夫酩酊大醉地躺在房门边。我只好像滚酒桶似地将他弄进屋里的沙发上,整个过程中他的鼾声不住。
刚弄停当,他腰间的BP机响了,我拨通电话问谁CALL的机时,一个女孩操着一口带着方言的普通话说找南海有事。我说我是他妻子,有什么事我能转告,电话的那端声音有些慌乱地说:“不!不麻烦。”电话就挂断了。
第二天,丈夫醒来,谈到那女孩时,他将视线从我的眼睛上移开说:“那是一个朋友的女儿。”就背过脸去,不再说话了。而我知道他那朋友与这女孩住的城市相隔有好几百公里,他为什么撒谎,丈夫的回答更加深了我的疑虑。从此,我便开始有了警觉,注意他的BP机和电话来。
南海是一所大学的教师,业余广告员,今年40岁。他的外貌在众多的人群里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但他与你交谈时方能显出英雄本色,他会吹得那些男男女女失去重心,在云雾里飘飘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和南海同窗六年,当时他是班上的才子,我是校文艺队员,读书时我们从没有说一句话,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几年后在班主任家里拜年时我们偶然相遇,在长长的回家路上,我请他谈谈毕业后的学习与生活,他却说要讲故事给我听,我说:“好哇,我特别喜欢听故事。”从此他便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开了,直讲到新婚之夜,他才悄悄地告诉已经成为他新娘的我那些故事都是他编的。
以后多年无论我怎样央求,他都不再讲故事给我听了,但他喝酒、醉酒的故事,却是愈来愈多了,使我感到惶恐不安。酒徒南海与我的距离正渐渐地远去。他知道我恨酒,但他却偏要喝,他是故意在伤害我,而我不知这是为什么。
几天后的星期日,南海出差到女孩居住的那个城市去搞广告,临行前,他极不情愿地将BP机放在家里。他走了几个小时后,BP机响了,一看果然是那女孩的电话号码,我马上回了电话并说你不要放下电话,我想跟你谈谈。电话的那端还是挂断了,再怎样打她的电话,她都不接。没办法我只好晚上打电话给已在那个城市的丈夫,希望他这次出差能将他与那女孩的事情有个了断,并请他转告那女孩,我想和她谈谈。电话的那端没有声音,我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那端才远远传来一个“嗯”。我想跟那女孩谈是想知道那女孩是否真爱他。我曾经大病过一场,看到日夜守护我的南海,我暗下决心要好好爱他。现在,他和这女孩如果是真心相爱,为了那医院里的日日夜夜和我心底的诺言,我一定成全他们。
他如期而归。
晚饭后,我问他广告搞成了吗?他说:“都办妥了。”“那女孩的事也办妥了吗?”他沉默了一会低着头说:“那是个很纯洁的女孩,是个好女孩,我们是和朋友一起喝酒时相识的,她很能喝酒,酒后我们一起去了歌舞厅。”尽管我心里早有准备,但听到这儿,我的头还是嗡的一下响了起来,下面他说什么我都没听见,眼前只幻化出南海和那个女孩喝酒的情景。丈夫对能喝酒的女孩情有独钟我早已知晓,所以这几年我用尽一个妻子温柔的心去感化他,为的是他能找回自己,看重自己,谁知他还是没有将自己超脱出来。他什么时候说完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木讷讷地问他爱她吗?和她在一起感到幸福吗?他却用外交方式回避了我的问话,说:“我们今后不再有来往,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是真的吗?
直到有一天,我去缴电话费,发现长途费特多,我想是不是邮电部门搞错了,于是我去查询。当我看到查询单上全是那女孩的电话号码时,我差点晕了过去,那上面记录的时间有时是一天一次,有时是一天三次,而且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打的。我被激怒了,决定用我的方式来解决。
回家后,我拨通了那个曾经让我痛苦的电话号码,“喂,你找谁?”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说:“我是南海的妻子,想找那个用这部电话的女孩。”“哦,你是南夫人,你找我妹妹,”电话那端顿时热情起来:“好人啊,真感谢你的丈夫,如果不是他四年前帮助我妹妹,她早死了。”“你妹妹怎么啦?”我关切地问,“怎么您不知道?我妹妹的双腿被汽车辗断后一直想自杀,是您丈夫启发她,教育她,跟她讲了许多人身残志不残的事迹,还经常带她到歌舞厅唱歌散心,使她树立了对生活的信念,去年还帮助她办了一个执照租了一间门面做鞋店。”“那你妹妹呢?”“她现在正在鞋店里忙乎,要不要我去叫她?”我忙说:“不!不要去叫她,以后再说吧。”在她哥哥一声接一声的谢谢声中,我挂断了电话。南海这种拯救灵魂的壮举,实在让人感到意外。如今,许多健康的身体里都只有残缺的灵魂在游荡,他却让一个残缺的身体里具备了一个健全的灵魂,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多么地不容易啊!我除了敬佩丈夫的伟大行为之外,也深深地为自己感到悲哀。我一直信任的丈夫在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为一个女孩隐瞒得那样严实,如果不是他酒后露馅,至今我还蒙在鼓里。相爱坚实的基础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真诚相待。他对我如此不信任不理解,他烦恼时喝酒,痛苦时喝酒,快乐时也喝酒,他会舍不得浪费一滴酒,却舍得让我心中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可见我在他的生活中连他杯中的酒都不如,还敢奢望有爱吗?这使我想起他的父母,一对七旬老人,一辈子不曾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大半辈子都在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如今疾病缠身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我不想重蹈他们走过的路,是分是合,是生是死我们要明白地解决。
我打了几个电话,就等着南海。晚上十点了他未归,我只好留封信给他,又留封信给女儿,然后走出这个既让我幸福过,又让我心碎的家。昏暗的路灯下,雨在不停地下着,下着雨的夜整个世界都在流泪,我边走边想着那封给南海的信:南海:
那女孩的事我已知道了,我不想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和那女孩一起来瞒着我,为你救人成功我感到敬佩不已。你没有错,你按你的原则在活着,只是我没有耐心等到你信任我、理解我的那一天。你为了一件说得出口的好事隐瞒了我四年,那谁知道你不会一边在外与你喜欢的人约会,并喃喃地说着“永远爱你”,一边回到家里和我拥抱。我为了爱,曾经恨过你身边所有的女性,漂亮的、有才华的和无才华的,会喝酒的和不会喝酒的。今天我不再恨她们了,因为如果不是你用心去接近她们,动心思地制造机会,我相信没有哪个女性敢走近你的身边。
和你在一起的15年中,感谢你给了我几年的幸福时光,我不后悔当初嫁给你就像我今天不后悔离开你一样。生命是有轮回的。当我从你身边消失时,希望你能斟满酒举起杯,为另一个人的生活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