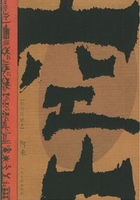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蜜月生活。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分离和等待之后,有情人能终成眷属,我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都忍不住流泪了。郭莎莎在多伦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她住在多伦多大学里的留学生公寓,两间居室,带卫生间和厨房。在多伦多,房东在每个新房客到来之前,都要重新给地板刷油漆,粉刷墙,连床单都要换上雪白浆洗过的。那里成了我们的新房,多伦多面对安大略湖,湖面波平如镜。我和郭莎莎在那里拍了许多优美的照片。接着我们又到唐人街和尼亚加拉大瀑布,参观游览。
蜜月度完,郭莎莎继续回到大学里攻读学位,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陪读丈夫”。为了适应加拿大的移民生活,郭莎莎为我联系了安大略新移民英语班去“恶补”英语。她计划,我的语言关过了之后,就到约克大学念书。我原打算,一到多伦多就去打工,我已三十多岁,对再啃书本,自知力不从心。再说,我俩的生活全靠郭莎莎的奖学金维持,一个男人怎能“吃软饭”?但莎莎坚决不同意我出去打工,说她读完硕士后,还要继续攻读博士,我这个做丈夫的连一个普通学位也拿不到,岂不让她太没面子了吗?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补英语,由于基础太差,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作业弄不明白,只好向妻子请教,尽管多次遭到她讪笑,但总算在半年后拿到了一张结业证书。
那段时间,家务活都由我负责。洗衣、做饭、收拾房间,这在国内我是从来不干的,由我的前妻包了。郭莎莎不以为然,还像小姐似地说我老土,吃不惯西餐,尽烟熏火燎地烧中餐,弄得厨房油腻腻的。还嫌我衣服洗得不干净,衣领袖口也不事先搓一搓。
我想跟她发火,可一想到她的学业压力大,又是新婚,权当她跟我撒娇了,也不跟她计较。她每天都要在大学图书馆呆到很晚才回家,即使在家也要在书房里工作到深夜。这段时间她不许我打扰,不许我碰她和她亲热。开始,我纠缠她,她便拉下脸,说你真俗气,一点也不理解我学业的艰苦性。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只好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可语言又不通,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寂寞孤独的感觉芒刺般折磨着我。我开始想家,想念那种温馨和热闹的生活。半年后,我进了约克大学的艺术摄影系。该系知名度非常高,能进加拿大一流大学深造,我感到格外兴奋,觉得做“陪读”丈夫也值了。
没料到,我仅上了一年就自动退学了。原因是我的英语太差,老师用英语授课,我听起来完全不得要领,脑子里一团浆糊。上课时,老师讲了笑话,本地学生轰然大笑,我听不懂,便问人家。本地同学耸耸肩,双手一摊:“嗯哼,连这个都不明白吗?”一副不屑解释的傲慢表情。
我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没跟郭莎莎商量就退了学。事后,她对我大发脾气,说我胸无大志,没有卧薪尝胆的精神,令她太失望了。我反唇相讥:“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爱情,不是来镀金的。”
郭莎莎也不示弱:“既然你爱我就得为我着想,围着我转的男人、洋博士和博士后一大把,而我的丈夫却是唐人街的打工仔,我的脸往哪儿搁?”
郭莎莎的话使我意识到,我在她心中的位置原来不过是个不拿工资,还能过情爱生活的男仆而已。我伤心透顶,打工挣钱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三
我很羡慕那些从大陆、香港和台湾来加拿大的劳工阶层的移民,他们身无长物,一踏上多伦多,顶多休息三天。第一天逛唐人街,第二天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第三天便要上班。埋头苦干,直到退休,便如此这般地买了屋,买了车,并养大了子女。
但我并不想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想赚足四万加元就回国去,继续我热爱的摄影事业。可是,在加拿大,工作机会极少,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稍有才干的也都要移民到美国,才可以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出来。所以,赚钱谈何容易。但生活又逼得我不得不努力去想法挣钱。
我打工生涯的第一步,是当小贩摆摊。因为只需向政府申请一个小贩牌(牌照是免费的),入这行的人很多,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连香港去的电机工程师因找不到合适工作,都去摆摊了。尽管别人告诉我,在小贩中心摆摊相当辛苦,我仍充耳不闻,反而责问对方,赚钱哪有不辛苦的?我拿出从国内带去的部分存款,到批发中心批发了二十多种货物,多是一些家庭日用品,例如玩具、厨房用具和家庭小摆设之类。我在小贩市场辛劳一天的结果是为我带来64元的收入,但除去批发价,除去摊位费,我仅赚回了7元,真令我欲哭无泪。
于是,我草草收场。又到上海人开的一家名叫“翠园酒家”的餐馆打工。初到那儿,负责刷碗洗菜择菜的粗活,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下班,先乘地铁再转车到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多了。郭莎莎对我天天这么晚回家极其厌烦,说她因功课负担太重,失眠严重,好不容易睡着,又被我进门吃东西、洗澡、上床这一连串的动作吵得困意全无,特别影响她第二天的学习。让我更无法接受的是,从我“下海”后,她开始冷淡我,拒绝和我做爱。偶尔做一次,也是很不耐烦,仿佛遭强奸。想到自己为了她放弃热爱的摄影事业,抛妻舍女,远涉重洋,来到这异国他乡,没有学业,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只有这少得可怜的爱情,她也要收回,我感到心灵深处从未有过的凄凉和悲哀。
有一天,我在餐馆被烧菜大厨不小心用热油烫伤了手,老板就让我提前回家休息。到家时都十点多了,郭莎莎还没回来。我以为她又去了图书馆,就先冲了淋浴,然后冲了一杯咖啡,坐在阳台的一把藤椅上,望着星星,抽着烟,想心事。这时,一辆漂亮的奔驰轿车流星般地滑到楼门前。车门开了,先跳下一位个子高高大大的金发男人,接着,金发男人走到车门另一侧,很绅士地从汽车里搀出一位年轻女人。我定睛一看,那漂亮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郭莎莎。他们用英语交谈着,然后,金发男人拥抱住郭莎莎,两人很缠绵地接吻了好一会儿……我的眼前一阵发黑,愤怒使我的骨骼嘎嘎作响。
郭莎莎一进屋,我就扭住了她,劈手抽了她一记耳光。她捂住脸,往日明媚的眼睛充满惊恐。“你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恶狠狠地吼道。
片刻,郭莎莎平静下来,高昂着头:“你再动手,我就报警。”
我顿时泄气了。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因妻子(陪读夫人)不甘寂寞和清贫,到多伦多的按摩院从事非法卖淫活动,愤怒之中动手打了妻子。那妻子报了警,朋友立刻就被警察抓进监狱。还是我借给了他一千加元,才把他保释出来。郭莎莎知道这件事,所以借此威胁我。不过她自知理亏,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郭莎莎向我坦白,那个男人是她的指导教授,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后,已和妻子离异两年。他迷恋上了她这个来自东方的漂亮姑娘,执意要和她结婚。
“敏德,原谅我,我只是对我们目前的婚姻不满意,感到失望和彷徨,还没有打算离开你……”她哭诉着。
我冷冷道:“明天我就从家里搬出去,你什么时候要离婚,就来找我。”
1993年2月13日,也就是我离家出走的两个月后,我和郭莎莎闪电般离婚了。
四
多伦多的贫民区,犹如大陆廉租屋村一样,多层的廉租屋,聚集了不同肤色的众多人口。我就在这里租了一间简陋的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日子过得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倒霉时非常相像,穷困潦倒、孤独沮丧。餐馆因竞争不过,倒闭关门,我失业了。可我越是艰难越是不想回国,因为无脸见家乡父老乡亲。那段时间,我到处找活干,曾送过一段时间外卖食品。多伦多市内的小街道没有街灯,找门牌得靠眼力。我常常是一面驾车,一面打着巨型手电,照着找路。当时正值冬天,冰天雪地。餐馆里有暖气,可一有外卖,便得马上冲出餐馆,开动汽车引擎。一般汽车需要五至七分钟才可将机件暖上来,不然开在途中就熄火了。耽误了顾客,拿回去,老板就发脾气,自己还要“倒贴”,真是苦不堪言。
为了早日实现赚足四万加元就回国的梦想,我想方设法多赚钱。我看到冬天落大雪的日子里,好多汽车“死火”坏在公路上,此时便有人提供私人拖车服务。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干这个赚了一些钱,我请他们有活时分一些给我。只要能赚钱,我什么苦都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