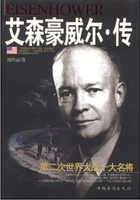我不好争辩,这样的事又最无法争辩,因为那样只能越抹越黑。我不愿听她哭闹,转身就走,离开家之后原想去单位,又怕谌华跟着我会闹到单位,只好在大街上走到半夜。心里渐渐冷了下来。
后半夜回到家里,谌华仍在抽泣。我对她说,你也不用再哭,你怎么怀疑我都行。我不打算跟你再过下去,我们离婚吧。如果说这些年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给你补偿。家里的房子,还有存款,统统留给你,我们好离好散。
她当时就停止了哭泣,眼睛瞪得老大,好久好久没有说话。
四
谌华不同意离婚,她坚持认为我与小飞早就串通好了的。她找到了所辖区的妇联组织,找到我所在企业的上级领导,控诉我喜新厌旧的“罪行”。尽管组织上对我这个人是了解的,但这件事还是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当时我又刚刚评上本系统优秀企业家称号,这多少对我的名誉是有影响的。
在家里她总是啼哭,我若回家,就会被她揪住不放,一遍遍地追问我:我们过了十六年,加上认识的时间,整整二十年,我们的儿子都十五岁了,你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要把我像扔一双破袜子那样扔掉?
谌华还认为,这些年间是她培养了我。她甚至这样推理:没有她父亲,我不可能留在大上海;留不了上海,就不可能有出国机会;出不了国,更不可能有以后的发展。总之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她辛苦栽下的一棵树,现在树上要结桃子了,她决不允许别人来摘。
她非常憎恨欧小飞,恨到死而后快的地步。
但她坚持不同意与我离婚,甚至用自杀来威胁,我无可奈何。
她到我的上级那里和区妇联告我以后,回过头来反倒把我看得更紧,无时无刻不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甚至不惜时间一遍遍地找到我的办公室,坐在外边等,要跟我谈话,弄得我简直没法工作。我曾经从家里搬出来一段,住在办公室。但因为她要死要活,也要搬来同住,后来又急得生了病,我不得不又搬回去。在家里,她像中了魔症,一次次跟我谈,问我是否仍爱她。
这一段同样让我感到难办的还有小飞。本来我们间并没做什么越格的事情,但这场风波却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她也时时想见我,她说她在单位也被谌华闹得名誉扫地,她十分痛苦,需要找一个人倾吐。而我内疚她的痛苦因我而起,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抚慰她。我这哪里像在上班,本来单位的工作一大堆,我却不得不放下公事,来处理我的家庭纠纷。
单位女工委员小黄专门找了一次谌华。谌华对她说:“离开老高等于是我这二十年人生的大失败,我怎能不委屈?为了他我已经放弃了我的事业,也放弃了我众多的同学和朋友,儿子又在外住读,没有了他,我还拥有什么呢?单单的几十万块钱、三室一厅,又有什么用处?”小黄说:“我不是劝你离婚,我只是认为你们先暂时分开一段也好,双方可以冷静一下。”谌华非常快地答道:“不,暂时的放弃,便是永久的失去。我不会答应的!”小黄又说:“那你也不该到处去诋毁高总啊,那样不是把他推得更远吗?”谌华说:“我也不想打击他,打击他实际上就是打击我自己。可是一个女人面对离婚,还能有什么武器?”最后她叹了口气说:“拥有一个优秀的男人,对女人不知是祸还是福啊……”
当小黄告诉我这些时,我感到一股来自心灵的悲哀。
为了让我“回心转意”,谌华想出很多办法。她给大学同学写信,公布我的“丑闻”,要他们规劝我“改邪归正”。她甚至还安排我跟她重返了一次大学校园,所有的日程所有的活动,包括和谁见面,谈什么,见哪位老师,怎样劝说我,都是由她精心安排的。最后她还安排我们重游了当年谈恋爱时走过的地方……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唤起我生命的一丝激情。我知道,我的爱情是真的死了。
Δ写给丈夫的告别信
□朱玲
明,亲爱的:
让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之所以这样称呼你,并非想唤醒我们之间早已泯灭的爱情之神,也不想缀补这支离破碎的家庭之帆。我只想乞求你,乞求你!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死死地、僵硬地纠缠在一起相互折磨、相互残杀。如果这是对我曾向你乞求爱情的一种残酷报复,那么我愿承担这种残酷报复的早日来临。
昨天晚上我又辗转反侧,彻夜不眠。泪水一次又一次浸湿枕巾。这是第几次失眠我已记不清了,而你在我身边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望着你紧闭着的双眼,紧锁着的眉头,我的心再次如同刀绞。你真是睡着了吗?在这种情形下,你真能入睡我倒也感到欣慰一些,然而你是在做给我看的,我深深知道。因此,每次我都只能是强压悲痛无声无息地暗暗抽泣。我的心在悲苦中剧烈疼痛、痉挛……我们共枕入眠,看似多么亲近,可是我们的心却相隔那么遥远,如同相隔一个洪荒的世纪。多少次我想对你讲出我心里的话,可是我没有那份勇气。这种心态已经折磨我十年了。3650天啊,多么漫长而难熬的岁月……如果没有婚前七年如一日的相恋的炽热;如果没有2555个日日夜夜的相思和患难与共,或许,失望不会这样撕破我的心,搅碎我的梦。
爱得越深越容易失去,也许这句话总是对的。多么残酷的生活,多么凝重的感受。难道爱永远是同苦难联在一起的吗?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中没有一个完整的爱梦呢?明,我们为什么要亲手毁掉历尽苦难建筑起的爱巢呢?我当然不忍摧毁它。但,我更难以忍受这囚笼,墓穴般的桎梏,灵与肉的桎梏啊,尽管我们有过震颤心身的爱的时候……
记得,在我们举行的结婚典礼上,你讲述的我们的恋爱史震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你为我代唱了你的同学为我点的《马路天使》中的主题歌,婚礼在“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声中结束。婚礼谈不上豪华,谈不上富丽,同时风相比甚至是寒酸的。然而,新婚之夜我如同掉进蜜罐中,醉了又醉。
蜜月是在隆冬中度过的,可我却似在阳春三月的花丛中徜徉、陶醉。我们的恩爱被其他人视为楷模。你为我的娴淑温柔被小青年视为择偶偶像而骄傲。我在忘掉一切享受爱的同时也在忘掉自我地付出爱。我自称自己就是夏娃,你是亚当,我们那个简陋的家就是伊甸园。绚丽、迷人、温馨的婚恋哟,几乎要将我彻底溶化,宽厚、强有力的拥抱哟,几乎要将我揉碎……我被爱所吞噬,我为爱而晕眩,我为爱而震颤,如痴如醉的我在爱河中畅游……
可是,这仅仅是一个残缺梦的开始,我并不知道,或许你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上帝在缔造亚当和夏娃的同时也为他们缔造了苦难……
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是一个真正的阳春三月时节。风和日丽的那一天,你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什么都不要我插手,亲自下厨,为我做了丰盛的晚餐,并亲手为我点燃25支蜡烛。在此之前我说将弟妹们都接过来热闹一番,举办一个家庭舞会。可你说你要同我独享这婚后的第一个生日之夜。你为我吹奏了一支美妙的曲子,我们的晚餐一直在明快、悠扬的轻音乐中进行。我始终沉醉在绵绵情丝之中。最后,为了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为你唱了一支情调极其深沉的歌。唱时我的双眼一次次潮湿。你说“这情调太凝重了”,我说“我对你的爱就是如此”。你,还记得那支歌吗?
就寝时,你要我闭上双眼,然后你如同以往就寝时刻一样,将我用双手托起,把我抱到床上轻轻放下……再后来你搂着,抚摸着,亲吻着我说:“凌,我们……”我很内疚地说:“今天我的例假来了。”
你的手停止了抚摸,长叹一声说:“怎么又来了呢?”
我说:“今天不正好是16号吗?每个月例假都是今日来的呀。”不知何故,当我说完此话时一种莫大的困惑偷袭进我的心房。
“我说,我们该有个孩子。我满认为这个月有希望了哩。怎么……”你显得极为不耐烦地说。说完将搂着我的手抽走,转身将背对着我。
面对着烦躁不安的你,我惊骇惶惑,如坠入云雾之中。稍顷,我怀着胆怯的心情用双手扳着你的肩,柔柔地说:“明,你……你,你,求你别这样对待我行吗?我好冷啊,好冷,好冷啊。”你仍给我一堵墙。我哭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们悲剧的开始。
自此以后,每次,每次我的例假来,我就不敢对你讲。我怕你的冷漠,更怕你的自我折磨,你的……我总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避你那询问的眼光,尽量将时间向后拖着不告诉你为的是让你能多高兴些时日,能多吃一点饭,多睡一个安稳觉。长时间的自我抑制,严酷地摧残了我的身体,从而造成内分泌紊乱。而你却总是将这种不正常的例假紊乱侥幸地当作是我怀孕的表现。从而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要我多吃一些营养品,你说这是为孩子而吃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怀孕了。你的种种言行举止不亚于拿着匕首在剜我的心,不亚于带刺的鞭在鞭挞着赤裸裸的身子。心是血淋淋的,身子是血淋淋的,唯独脸颊是微笑的。那是惨淡、带血的微笑你是看不出来的。
为了让你高兴,我忍受着这自欺欺人的悲苦的折磨。强装笑脸,强装呕吐,强装贪睡,强装要吃酸的、辣的,强装出孕妇所要反应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为了赢得你的舒心,赢得你的一笑,赢得你的吻。冷淡的吻我也是需要的啊。谁叫我是女人呢?谁叫我是个女性化十足的柔弱女儿身呢……我在饥渴与克制中煎熬。痛苦的茧在煎熬中一层层加厚。我怕,我极怕这茧的增加,我极怕自己对爱对你失去信心,我怕极了。可是,爱,终于还是被那厚厚的茧覆盖侵食了。
开始,我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