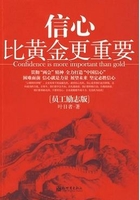燕子吃着峻送来的小点心,很诧异的说,我们是好朋友呀。然后,给男朋友打了电话,说,想你。
放下电话,峻就过来了,满脸幸福的看着燕子一点一点地吃着他送来的东西。然后,他们牵手出去。
我开始着急,那么,这个成了燕子的男朋友?
毕兴说,你真傻,怎么会。
后来,峻终于选择在一个很浪漫的演唱会上,对燕子表白了。燕子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非常无辜地说,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呀。我有男朋友的。
很好的一个玩笑,我不由得大笑。
不知道是真是假,也不能将这个joke转给丁强。
只是,我想,我不能够太热心的去促成他和燕子,不能的。
然而却也好奇,我记得丁强曾说过冰沁长得很一般,不知道燕子,又是何等人物呢?于是,我向毕兴要了燕子的pic。
原来是她。高高的,蛮丰满,挺成熟,擅长西藏舞的那位。想到了丁强,似乎有些姐弟的感觉,不由得觉得可笑起来。
于是,我给丁强留言,告诉他,我所能够客观陈述的一切。
关上了笔记本,打算睡觉,却又有电话。
那一端,有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平静的声音,他说:“你今天快乐吗?你微笑了吗?”
我知道他是谁,我在静夜中问:“你呢?”
“我刚刚到了莫斯科,听,你听雪花飘落的声音了吗?”
我侧耳听,却只听到呼吸。我说,晚安。
第二天,却收不到了信件。
有淡淡的失落。
下午,上课,在课堂上修改一份报告。
下课后,走进学生会,将申请礼堂的报告交给曹弘,他接过去,斟词酌句,然后盖上印章,告诉我,送到团委。
丹骏正和一个赞助商争论着什么,他看到我,转身说:“晚上一起去腐败一下?弘哥,还有我。”
好主意。我点头。
“嗯,那你先坐坐,等我一下。”
比较无聊的,听曹弘和丹骏和统一集团的人争论一项一项的预算。
我来看策划书,那时我逃了几天的成果,遵照了吩咐,做得格外细致。光是海报,就有A4黑白,A3黑白,A4彩打,A3彩打,A2彩印,分发折页六种,每一种海报的用途不一,A4的在各个宿舍楼,A3的在三角地,A2的在橱窗,数量精确。黑白和彩色的配合也分了各种时段,总而言之,呕心沥血。
“Annie,走啊。”
我正在计算一个数据,却发现曹弘和丹骏已经整装待发。
在家园边上的师生缘坐下来,点了一些菜,丹骏和曹弘开始喝酒,我喝椰汁。
说着这个那个的玩笑,讨论着这位那位的艳遇。忽而,丹骏指着我说:“Annie,你很好。”
曹弘笑着去和他碰杯问:“怎么个好法?”然后,又对着我说:“你还是蛮尽力的。怎么说呢,文化部是袁野分管的部门,我还是要让他有这个人事自主权的,是不是?”
我笑道:“都一样啊。没关系。况且,袁野和李诗音都很有能力的。”
我看到曹弘眯着眼睛开始笑,有着狐般的迷离。
我惊。难道,又说错了什么?忽而想起来,文化部的工作仿佛都是曹弘直接来找我,而我几乎也不通过袁野和李诗音。莫非是架空?我在心里暗暗的想。
只是,分管着文化和体育的副主席,向来是下一届主席的人选,因为,大型的活动容易出彩。而今,袁野,正是分管着文化和体育呀。和曹弘有过节?曹弘想扶持别的人选?只是,这是我所不知的了,也不该问,因为无益。
于是,我也跟着笑。
丹骏凭了三分醉意,依旧点着我说:“Annie,你知道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到要拉你一把?”
我开始有些许的忸怩,我说:“大约是看我太笨?”
“笨?有一点。”丹骏和曹弘相视而笑,然后他说,“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漂亮的女生不开心,哈哈。”
是了,大约,我只是他们无意中的灵光一点,或者也许只是因为适合操纵,而且,我也乐意被操纵。
“不过你倒是个蛮好的人。”丹骏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掏出名片,“拿着,我新开的公司,以后我大约不大会来这里玩了,有空就找我玩。”
我接过名片,看到他的Title是:中关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
吃完饭,他们两个要去打球,于是我和他们告别。
回到宿舍,我存了几分好奇,不知道袁野的故事,会如何地往下写,我看到他经常有着自信满满的脸,也经常的有事没事的往团委跑,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成功。开始慨叹自己的麻木不仁,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硝烟从何而弥漫。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大约,我只要会微笑,能够把策划做好,就是了。
我感觉到有些累,于是,就来看那些信。它们总是能够让我平静。
然而今天,它仿佛也不能够让我平静,我想知道,写出这些信笺的人儿,他到底是谁?而他又为什么会去莫斯科?
我看到他说自己“敏感、忧郁、害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喜欢好书和好女人。内心和外表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多数的时候,也就忘记了自己的实际年龄。一旦想起,又倍觉委屈,仿佛年龄是岁月加于我的一个污点。”
却有些像李敖,然而我,却并不是太喜欢李敖,大约是我不大喜欢那些太过于刻薄的文字,哪怕那是事实。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多大,然而他却能够说出:“我知道你有一颗如同罗曼·罗兰所说的,清明宁静而非常关注的灵魂。”
他用的信笺,都有着北大的字样,大约,是一个北大人。
一天又一天。
还是没有信件。我仿佛有点焦虑,连说笑的声音,都开始有些刻意的大声。
丁强却仿佛进展得很顺利。我看到燕子做了丁强的副手,也在劳动经济学课上当助教,有时候能够在图书馆,看到丁强在帮燕子温课。
从校园里走过,也时时的看到燕子和丁强,我想看到燕子很娇憨的样子,却在猛然间能够感受她凌厉的眼神,是我的错觉吗?心里一惊,再抬头,燕子就是我想象中的燕子了,微微的笑着,很朴实的样子。有时候,也能看到燕子和一个高高的男生,相拥着走过,大约,那就是她的男朋友了。
还不到一周,E时代,是一个快速的时代。
周末,到了周末,算来已经是七天没有了信件,而除了那天晚上,也没有接到过其他的电话。日子在不紧不慢中,显示出了单调,幸而,有了同乡会。这是我们在北大的同乡例行的节目。除了吃饭,大约就是随意地玩。
秦杲是一如既往地缺席,仿佛,已经很久不见他了。我慨叹。
吃饱喝足,他们居然选择了去打牌!我不喜欢太费神的游戏,所以,我老是输,所以,我不想加入,但是,我也不能离开。
在那里东张西望,觉得还是来上网。突发奇想,想来装一个GG,去会会网上的姑娘。于是,就要过来张琦的QQ密码,开始在他的机器上,恶作剧的,胡言乱语。
张琦的昵称叫妖精,他有着一串的好友,只是,现在,夜未深,不是聊天的时间,QQ上的头像,灰成一片。只剩下了一只孤独的企鹅叫##**。于是,我Message他,好呀。
很不客气地回答说,滚。
我皱皱眉头,微微撅着嘴,表示委屈,仰头看着张琦。
有些尴尬,他摆摆手,说:“没什么呀,隔壁的兄弟嘛。随便惯了。你随便骂。”
于是,我Message说:“不要这样嘛。孩子。”
小企鹅变成了灰色。我有些扫兴。正想过去看打牌,却又有了回音。
Message说,听说你们宿舍有个漂亮姑娘呀。
我回一条,是呀,我老乡。太普通,我从不正眼看她。
他送过来一个笑脸,道,是暗恋对象,不敢看她?
我一本正经的信马由缰,不是呀,她暗恋了七年,送了情书无数,鲜花一片。只是,张琦我怎能如此没有品位?
越来越不像话,张琦在一边发话,他说:“好啦好啦,姐姐,那位兄弟刚才来过,你的游戏,已经没有了意义。”
这样呀,太扫兴。
我问张琦,这是谁呀?
张琦简简单单的介绍说,高枫,一个帅哥呀。北师大的女朋友每周来给他洗衣服,还有袜子。
非常的强!我瞪大了眼睛,仿佛是唐时明月汉时关,此时借尸还魂地回来了。在Mobile的年代里,我只看到男生在女生楼下痴心的等待,却未曾见贤妻良母伸纤手,寻袜子,化腐朽为神奇。
暗暗感叹于此帅哥的魅力。一屋子的男生更是倾慕的五体投地。
5谜底揭晓
回到宿舍,看到了一枝玫瑰,只是一枝,而且是很平常的那种。但是,这样简练的风格,我大约知道了是谁。我想,应该是他从莫斯科回来了。
我知道,今天会有电话。
我有些激动。我又开始翻看那些信笺。
“调情是轻松的,爱情是沉重的。风流韵事不过是躯体的游戏,至多还是感情的游戏。可是,你可知道,当真正的爱情来临的时候,灵魂因恐惧而狂喜而颤栗了。”
“被爱之前,我们是未启蒙的婴儿,被爱之后,我们是一方开启的古玉。关于爱情,我们有没有可以达到的语言?”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者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那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关于爱情,叶芝说了什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听懂什么?走进爱情,我没有了衰老的理由,只愿携了你的手。”
有一点心跳,也有一点的红晕,我在宿舍里,快乐的如同孩子。
果然的,那个宁静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来,他说:“Annie,我现在,在你的楼下。”
我奔到楼下,在楼门外,站立的,是一个有些单薄的男子,很大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有些闪烁,我看不到我所期待的宁静,有一些失望。
他微笑地看着我,但是神色却有些焦虑,仿佛是感觉到某些不安。他开口叫我:“Annie,前几天,去莫斯科大学研究普希金的诗歌,所以没有给你写信。”
然后,他左右环顾着问我:“我们去未名湖,好吗?”
我点头。他急匆匆的在前面开路,我想,他多大了呢?二十五或者三十?我向来不善于分辨年龄,大约没有发言权。
在正大国际的门口,他问我:“你可认识我?”
我摇摇头,我仿佛曾经以为我有些认识他,这些认识来自于他的信笺,但是,如今,我又仿佛觉得,我完全不认识他。
他在正大国际的门口,郑重的转过了身,对我说:“我是玠羽。”
是他!那个住在四十七楼的文坛黑马!我想起他桀骜不驯的文字,我有些惊讶。他的文字已经出版了六七本,都是杂文,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是大陆的李敖,是北大的骄傲。可他给我的信笺,满纸的,都是宁静,是一个出尘的形象。然而眼前的他,没有那种桀骜,也失却了那种宁静。
我难以将他们糅合起来,我目瞪口呆。
他站在那里,依然是自豪的问:“如果,我早告诉你,我是玠羽,你会不会很崇拜我?”
我心中的玠羽不会这样问,我心中写出那些信笺的人也不会这样问,我于是低了头,往前走。
他喋喋不休的依然在那里说:“你知道,有一些名气,却也不是好事。每日里,有了一堆的信。润笔不多,也有几万,唉,当然,学文学的,比不上学计算机的有钱,但是却也有麻烦。唉,去签名售书的时候,手都写酸,出版社居然还要克扣版税……”
站在那里,我忽然找不到了自己,我想起卡门说过:“我爱过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而且我为我爱过你而恨我自己。”
我爱过吗?大约只是期待?但是,我爱的决不是眼前的人。
我的失落,生生的写在脸上,而玠羽也毕竟是玠羽,他终于停下了他对出版社的埋怨,他问我:“你的眼,为什么,仿佛莲子的心?”他是一个敏感的人。
我笑。
他说:“你连笑起来,都那么不快乐?”
我叹息。
他说:“你的叹息,是不尽的海。”
仿佛有了诗意,只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是他先前的味道。先入为主,大约,是没有办法的。
未名湖边,他问我:“你知道中文系的千禧女孩吗?那一个和盲人相爱的女孩子。”
是的,一个是盲人,一个是北大的研究生,为给他们的爱情做铭牌,北大用了办公楼为那位盲人开音乐会,只是我想起人生理论课上,一位男生曾经愤怒地说,那个女人,根本不把人家当人看!于是我只是说:“难道她不是为了出名?”
玠羽的脸色霎时间有些改变,他讪讪的说:“爱情,其实还是很美好的东西呀。”
然后他停下脚步,问我:“Ann,做我的女朋友好吗?我是认真的,我会让你幸福。”
“可是,我不叫Ann,我叫做Annie。”我淡淡地说,“再见。”
我回到宿舍,看着玫瑰和信笺,觉得迷离而梦幻。我将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的撕下来,扔进垃圾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丁强,又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那端,他永远是手足无措的焦急,他说:“她哭了,我惹她伤心了。怎么办?怎么办?”
“别急,你慢慢说。”想起他那稚气而甜美的脸,我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
“今天我们去了未名湖边,我问她,你爱我还是爱他,她看着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的逼她?我是不是很坏?”
感觉的出已是方寸全乱。
也是未名湖,不知道每日里,未名湖要目睹多少这样的故事,如果湖亦能语,大约只有它才是情感的大师。
我有些惊讶的是,居然,丁强也会这样的表白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呢。即使是遭到拒绝,也比无疾而终要踏实一些吧。
嗯,我沉吟着,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女孩子的眼泪,是一种武装,我没看到燕子的眼睛,我不知道燕子的眼泪里有多少的真切。我只是说:“不要紧,你做得很好呀。但是,现在开始,给她一点时间吧。”
丁强在电话那头安静下来,他说:“好的。我等。可是,我没有时间了,我快要去剑桥了。”
“你要去剑桥啊?”剑桥这个字眼,对于我,很明显的比燕子有吸引力,我在漫不经心中有了一点兴趣,我问,“交换生?”
“是呀。学术交流。我下学期去剑桥。”
实在是为自己的明天担忧,心里有些羡慕,一时没了话语。
“我想知道她究竟爱不爱我啊。”他那里又开始了急切的话语。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或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呢,我暗暗想。我说:“你应该告诉她,你快要去剑桥了。”
“为什么?”他茫然的问。
我想,燕子会在乎,但是,我却也不想说,忽而又想起了什么,我问他:“燕子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
“你也应该告诉她。”我说,一点点冷冷的笑,开始浮现。
“为什么?”还是那种茫然的语气。
唉,我叹了口气,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于是,我说:“你们要增加了解。”
“这样啊。”
那一边是恍然大悟的语气。我说:“是啊,是这样的。”
我发现我俨然是前辈,在丁强面前。
我的建议,总是非常的灵验。没有一周,丁强用了很兴奋的声音告诉我:“燕子说,她爱我,她说她爱我。”
简直都快要被他的幸福感染,真是一个可爱的少年。
只是,顺利如此,是幸福,也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