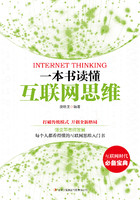在美国受到抵制的戴明去了日本。戴明教导日本企业家,制造过程中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客户流失,因此不断降低缺陷率才应该是生产目标。日本企业家将戴明的思想与工人控制制造过程的“看板哲学”结合起来。看板的意思是“卖场”,生产一线的工人们必须像顾客在杂货店购物一样挑选零部件。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永远是如何生产出更好的零部件。这两种思维结合产生了一种新事物,一种“第3选择”: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也相应提高质量的“全面质量管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心态:我的产品还能怎样改进呢?
与此同时,受“两种选择”心态困扰的美国制造商们不得不与更可靠、更便宜的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苦苦竞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恶性循环对美国的重工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两种选择”的思维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缺乏“第3选择”心态是达成协同的巨大障碍。对特定问题持有“两种选择”心态的人只有承认协同的可能性才能达成协同。“两种选择”思维者只看到竞争,看不到合作,在他们眼中永远是“我们对他们”。“两种选择”思维者只看到“虚假的困境”,在他们眼中永远是“没得商量”。“两种选择”思维者患有某种程度上的色盲,在他们眼中只有蓝色或黄色,永远看不到绿色。
“两种选择”思维随处可见。战争是其最极端的表现,除此之外,它还会以“大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由党对保守党的演说充耳不闻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选择”思维,反之亦然。企业家为了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利益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选择”思维,同时,在企业家坚持“长远眼光”而公司却因为他们漠视短期收益而倒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选择”思维。在宗教人士反对科学、科学家认为宗教毫无价值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选择”思维。(在伦敦一所大学里,科学家们甚至拒绝与神学家在同一个职工餐厅里就餐!)
“两种选择”思维者往往无视他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而只看到别人的意识形态。他们不尊重不同观点,因此不会尝试去理解别人。他们也许会假意表示尊重,但他们其实并不想倾听,而只想控制。他们时刻准备着攻击,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的领地、个人形象以及身份认同都经受着威胁。最终“搜寻并摧毁目标”成为他们处理异议的策略。对这些人来说,1加1等于0或为负。在这种环境中,协同是无法茁壮成长的。
你可能会问:“与每一个人都达成协同有可能吗?”这对于缺乏自我控制、有认知与情感障碍的人来说会非常难。当然,你无法与精神病患者达成协同。但大多数人是普通人,理性的普通人最容易陷入偏执一端的“两种选择”危险思维中。就像表2–1所示,在我这一方的符合A列,在你那一方的符合B列。
我曾经以为大多数成年人不会这么狭隘,因为他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多复杂。但是看看我们的媒体,看看身边这些对“两种选择”思维乐此不疲的人们,我真没那么肯定了。
此外,当我们面临两难(所谓的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的时候,“两种选择”思维会给我们增添烦恼。我总是听到这一类的问题,相信你也是。老师说:“我跟这个学生相处不来,但我不能放弃他。”企业家说:“不追加资本我们就没法实现业务增长,但是没有业务增长我们又赚不到钱——这是典型的第22条军规。”政客说:“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保险我们负担不起,但我们也不能让付不起医药费的人民受苦。”销售总监说:“我的两位顶尖销售一直在相互攻击诋毁,但是没有他们我们会丧失最好的客户。”妻子抱怨丈夫:“我不能和他一起生活,但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他。”
两难的牛角
当只有两种同样可怕的选择时,你会非常痛苦。古希腊人称之为“两难的牛角”,因为它就像面对一头冲撞的公牛:无论被它的哪只角顶到,你都会被刺穿。
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两种选择”思维者具有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选择举手投降。有些人会扑住其中一只角,拖着其他人跟他走。他们对“保持正确”如此痴迷,以致即使遍体鳞伤也要极力捍卫自己。还有一些人情愿被角刺中而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这样。他们都看不到“第3选择”。
我们在面临“虚假的困境”时往往无法识别——这太糟糕了,因为其实大多数的两难困境都是纸老虎。“虚假的困境”随处可见。一些调查会问:“你支持共和党的解决方案还是民主党的解决方案?你赞成还是反对毒品合法化?将动物用于科研是对还是错?你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这样的问题不允许我们思考时超越两种选择思维(通常这正是提问者的意图),然而,在“两种选择”思维者之外,几乎永远有超越两极的选择。我们很少问自己是不是有更好的答案——第3选择。民意调查者永远不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中立者
放弃希望是一种对“两种选择”思维的弱化回应。在所有“大辩论”中,都存在不支持任何一派的“中立者”。他们通常对“两种选择”思维的极端化感到厌倦。他们相信团队协作,理解对方的观点,但他们看不到第3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并不认为工作冲突、婚姻冲突、诉讼冲突或巴以冲突真有解决方案。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合不来,我们不相容,但我们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他们信奉妥协,将妥协视为可以实现的最好选择。妥协表面上看不错,并且有可能阻止许多问题的恶化。词典上对于妥协的定义是,对立双方为了达成某个协议而“承认、牺牲或放弃”某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双输”——与“双赢”相对。妥协可能会令人满意,但永远不会令人高兴。妥协关系是脆弱的,争端往往会再次爆发。
生活在“双输”的世界里的中间派不会抱太大希望。他们往往是在职场中年复一年埋头苦干却没有太大贡献和潜力的人;他们往往以工业时代的过时的眼光看待生活;他们的工作就是机械化地履行职责,而不是改变世界或创造崭新的未来;他们是很好的执行者,却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当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怀疑态度是对“两种选择”思维的一种防御。“除旧布新,我们要成为更精简、更高效的组织”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弃保险/接受减薪/干两个人的活,让我们的账面看起来更好看,这个主意挺不错的吧?难道你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放弃吗?”他们当然不会反驳。从来没有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只是被视为通用零件,而他们自己早已经学会了不抱希望。
因此,玩世不恭往往是中间派的悲哀结局。在他们看来,任何热情都值得怀疑,任何新想法都应受到蔑视。听到“协同”一词时他们会有排斥反应,他们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协同。
寻求协同思维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越两种选择思维、获得协同心态的人——如甘地、戴明和支持孩子学音乐的家长娜迪亚——很少,但他们有着高度的影响力、创造力和效能。他们自发地设定每一种两难境地都是“虚假的困境”。他们是另辟蹊径者,是革新者,是破局者。
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获得“第3选择”思维,我们必须分四步转换思维模式。请记住,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它们是违反直觉的,它们将引导我们远离自我中心,建立对别人真正的尊重。它们会使我们不再总是寻找“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要寻找“更好”的方法。它们将引导我们走向不可预知的道路,因为没有人预先知道第3选择是什么样子。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心灵愈合与成长的首要条件是“真诚、真实、和谐”。我们伪装得越少,达成协同的机会就越大。因此,达成第3选择的第一步是“我看到自己”,意思是具有自我意识——我已经自内心深处认识到我的动机、怀疑与偏见,我已经检验过我自己的设想,我已经准备好与你真诚相对。
第二步是接受、关怀、赞赏。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心目中的英雄卡尔·罗杰斯,将这种态度称为“无条件积极关注”。它是我对你的一种外向、积极的感觉,因为我视你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态度、行为或信仰的集合体。对我来说,你不是一种东西,你是一个人。“我看到你”,我视你为姐妹兄弟、上帝之子。
第三步是同理心,只有在接受前两种思维模式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同理心的意思是体会并真正理解别人是怎样的人。同理心很少见;你和我都很少付出,也很少得到。相反,正如罗杰斯所说:“我们会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截然不同的理解——我理解你错在哪里。”相比之下,“我找到你”从而充分掌握你的内心、思想和灵魂,而不是以批判你为目的,则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新的观念只有在真正相互理解的气氛中才能最自由地呼吸。
我们必须做到前三步才能抵达第四步,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了真正的“双赢”解决方案——一个对我们来说崭新的解决方案——而共同学习和成长。当我给予你真正的、积极的关注并对我们的内心与思想有清晰的理解时,当我超越“只有两种选择并且其中之一是错误的”这一思维定式的局限时,当我以“有无穷多种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有益的、激动人心的、创造性的选择”的思维模式思考时,才能达成“我和你协同”。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了解每一步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1:“我看到自己”
这是认知的第一步,将自己视为有独立判断力和行为能力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个有思想、受尊敬、有原则、开明豁达的人?抑或看到了一个什么都知道、对冲突的“另一方”不屑一顾的家伙?我是被思维限定着的,还是独立思考的?
我不只代表争议中“我这一方”,我不只是成见、派别与偏见的集合体,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决定,我不是萧伯纳笔下抱怨世界不按我或“我们”的想法行事的自私鬼。我能够在精神上脱离自我,客观评价我的思维模式对自己行为的影响。
认为自我是由外部定义的思维是无效的思维,其结果是“我”的所有价值观都来自外部。被定义就是被禁锢或限制,然而,人类本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和要做怎样的事,这是人类的基本原则。当一个人说自己是一名环保者时,她的真正意思是她与某些人对自然环境持有相同的观点。她当然不只是一名环保者——她还是一位女性、某人的女儿,或许还是谁的妻子或女朋友,她还有可能是一位音乐家、律师、厨师或运动员。
关键是这些角色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定义她。如果她够聪明,那么当她照镜子时,她会看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外的东西。她会看到自我——一个超越了镜中影像的有思想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人。
当一位领导者将自己定义为理性、实际而冷静的商务人士时,他可能正走向没落。他可以根据自己所受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但依然会失败。这种事屡见不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超过2000家公司进入过全球500强行列,然而其中的大多数如今都已不复存在。我们曾亲眼目睹这种所谓的冷静思考在过去几年的经济灾难中多么不堪一击。经济观察家们(如知名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教授)担心,傲慢的MBA文化将是导致下一轮金融危机的根源。
当然,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是被我们的文化所限定的。我们倾向于和我们所认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穿衣、说话、吃饭、玩耍和思考,而无论我们是企业高管、芭蕾舞演员、牧师、政客还是警官。我们穿着制服,服从着权威,看着电影,说着行话。
哲学家欧文·弗拉纳根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出身的家庭和社会赋予了我们既定的形象,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既定形象往往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先于我们而在……当我们成长到有一定控制力的年龄的时候,我们在根植于体内的形象、背景的驱使下工作,于是这些也成为我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成为自我形象的坚定捍卫者,即使它已经越来越与我们自身无关,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被强加的外部形象。
真实身份盗用
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身份盗用的故事:有人拿了你的钱包,冒充你刷了你的信用卡,但更严重的身份盗用是沉浸在别人对你的定义中不能自拔。你对外部事物、文化背景、政治与社会压力过度关注,对自己是谁、自己这一生能做些什么反而漠不关心,我称之为“真实身份盗用”。这种身份盗用是非常真实的,它一直在发生着。原因很简单,人们无法区分个人思想与文化思想之间的区别。
我们的政客们对于身份被盗用变得越来越麻木。即使那些初时本意良好、意志自由、有着高度正义感的人,都对自己的身份被盗用无动于衷。“两种选择”思维取代了他们的独立判断,驱动着他们的行为。正如一位前国会议员所说:“他们无助地聚集在党性路线背后,看起来似乎别无他法。”
人类发明了镜子,却开始丧失灵魂。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影像,却忽略了自我。于是人们开始对自己讲述与自己的社会形象一致的故事:
“我讨厌这些政治会议,但是作为优秀党员,我应该参加会议。”
“那家伙来自其他党派。轮到他发言了,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浪费时间。”
“人们怎么能相信那样的东西呢?他们怎么一点儿常识都没有?我就是个坦率而且懂常识的人。他们怎么不能像我这样呢?他们瞎了吗?”
“嗯,在那一点上他有些道理。但是,等等——他的话怎么可能有道理呢?那是不可能的,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
“真不知道这么明智的人怎么能那么固执。”
一旦承认反文化形象的价值,就是对自我文化形象的抨击。(“你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的正义与真理都掌握在我们这一方?可能有一些掌握在对方手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超越自我文化形象的能力。我们可以超越我们所穿的制服,超越我们的传统观念以及其他所有千篇一律的符号。
我们不是预先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与汽车、钟表或计算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超越文化编程的独特天赋。我们具有自我意识,其含义是,我们的精神可以超脱自身之外,评价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我们深思熟虑,我们可以质疑武断的假设,机器不能。我们拥有自我意识,可以不受约束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有创造性,有良知,这种对自身的了解赋予了我们信心。
但同时,我们永远无法全面看清自己。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只能看到部分自己,我们有盲点。面对冲突,“两种选择”思维者很少质疑他们自己的既定程序,他们信赖看似完全合理实则存在缺陷的文化模式。协同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别人,还要了解自身。拥有这种认识能够让我们变得谦虚。
如果我能够认真地审视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倾向。我可以看到自己需要弥补的不足,因为我并不完美。我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压力,我可以看到别人对我的期望,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真正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