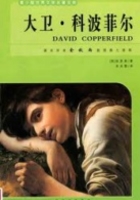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远地,一个人影慢慢从河堤下面升上来。逆着天光,小米只能看清来人的轮廓。 这个人高大,黝黑,像黄昏中一座移动的铁塔。小米——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米这才看清铁塔是村西的建社舅。建社舅是外地人,村里的上门女婿,论起来,算是娘的堂兄弟。小米看了一眼建社舅,他背了一只大筐,里面是堆尖的青草,颤颤巍巍的,很危险的样子。建社舅小心地把草筐卸下来,放在地上,有几蓬青草掉下来,滚到小米的脚边。建社舅说热,真热,一边把身上的背心脱下来,快速地扇着。小米看了一眼他的肚子,圆鼓鼓的,像扣了个大面盆。小米就笑起来。小米穿了一条布裙子,浅米白的底子,上面撒满了鹅黄色的花瓣。建社舅看了她一眼,说,米啊,建社舅给你打个谜,看你猜出猜不出。小米说那你说。建社舅把汗淋淋的背心甩在肩膀上,从筐里拽出一根草,把它弯成一个圆,说这是啥?小米说还用问,傻瓜都知道。建社舅又从筐里拽出一根草,说,这个呢?小米扑哧一下笑了,草呗。建社舅也笑了一下,说傻。他把这根草从那个圆里穿过去,说,这个呢?小米想了想,说,这个,啥都不是。建社舅把那根草在圆里来来回回地穿进来,穿出去,穿出去,穿进来。他看着小米的脸,手下的动作越来越快。这个呢?小米感觉他的样子很滑稽,忍不住笑了。天色正一点一点黯淡下来,田野里,渐渐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夹杂着庄稼汁水的青涩气息。远远地,村子上空升起淡青色的炊烟,和茂密的树梢缠绕在一起。建社舅,回家了。建社舅不说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两根青草。建社舅今天有点怪。小米想。她不想理他了。她要回家了。
暮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一点一点把小米包围。小米看了一眼树桩一样的建社舅,转身往回走。小米。树桩的声音从暮霭中穿过来,小米听得出他声音的不平常。她忽然有些害怕,撒腿就跑。
小米醒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太阳透过槐树的枝丫照过来,在窗户上描出婆娑的影子,画一般。小米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
姐,吃了?
建社舅!小米感觉自己马上变得僵硬起来。娘说吃了,建社你坐。
这天,也不下雨。
可不是,干透了都。青改还壮吧?几个月?
八个多。
快到时候了。
可不。
这一晃。
建社舅打了个哈欠,问米哩?
这闺女,长懒筋啦。娘在哗啦哗啦地洗衣裳。还睡哩。米——小米——
建社舅说睡呗,有啥事。
小米忽然一下子就从炕上坐起来。拿手指拢了一把头发,噌噌两步就打开门,把帘子撩起来。院子里的人都没防备,吃了一惊。小米靠在门框上,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阳光打在她的脸上,一跳一跳地,看不清她的表情。这闺女。娘嘟哝了一句,又低下头摆弄盆里的衣服。建社舅脸上讪讪地,一时没了话题。一只板凳横在门口,小米飞起一脚,把它踢个仰八叉。正在闭目养神的芦花鸡吓了一跳,嘴里咕咕叫着,张皇地走开去。招你惹你了,这闺女。小米不吭声,往盆里舀了水,豁朗豁朗洗脸。建社舅说那啥,待会子说是收鸡蛋的来,我回去盯着点儿。娘说你忙,也叫青改过来坐坐,老闷家里。建社舅答应着往外走,小米洗完脸,抓起脸盆,哗啦一下泼出去,建社舅的裤脚就湿了半截。这闺女,怎么就没个谱。娘歪着头,使劲拧着衣裳,嘴巴咧得很开。老大不小了都。
这程子,小米心里老想着建社舅的那两根青草。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有一回,一家人吃晚饭,电视开着,是一个没头没尾的电视剧。男人和女人在说话,说着说着就抱在了一起,开始亲嘴。他们亲得很慢,很细致,像是要把对方的五脏六腑都吸出来。小米心里有些紧。她盼望电视里的人快点停下来。电视里的人却越来越有耐心,他们像两株蔓生的植物,彼此缠绕在一起,越缠越紧。小米不敢看了,她感觉手心里湿漉漉的都是汗水。屋子里的气氛也慢慢变了。有那么一会儿,大家停止了聊天,谁都不说话。电视里的人继续亲着,男人开始脱女人的衣服。屋子里静极了,只听见电视里的喘息声和模模糊糊的呢喃。小米感觉时间像是凝滞了,她木木地吃着饭,全然吃不出一点滋味。这时候爹终于站起来,他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说这蚊子,挺厉害。他准备去拿蚊香了,可是又停下来,对着娘说,还有吧?蚊香。娘回头看了爹一眼,就起身到抽屉里找蚊香。抽屉乒乒乒乓开合的声音,把电视里的声音淹没了。哥哥回过头来,看了娘一眼,小米注意到,这一眼里似乎有些愠怒。趁着乱,小米走出屋子,装作上厕所的样子。一阵风吹过,院子弥漫着树木和蔬菜的气息,夹杂着人家的饭菜的香味。小米一直找不到借口出来,她怕大家知道她的害羞。害羞,就是懂了的意思。小米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她不好意思。回到屋里的时候,电视上一切都过去了。画面上,是繁华的城市街道,阳光明媚,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还有轻松的音乐。小米心里像有一根紧绷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一家人也恢复了正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气氛轻松。黏稠的空气开始慢慢流动。大家都暗暗舒了一口气。爹终于没有把蚊香点上。此刻,他神情自在,不慌不忙地卷着旱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