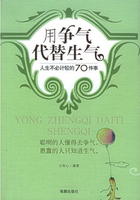午后的大楼寂寂的,仿佛是盹着了。走廊拐角处,一棵肥硕的巴西木,绿得恣意。周一洲的办公室半开着,郁春的孩子气上来了,躲在门外,半晌,屋子里没有一点动静。郁春在走廊里立着,一时有些茫然。走廊里光线幽暗,只在顶头那一端,有一线亮的光斑,像一块灰蒙蒙的绸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郁春循着那光斑走去,只听见有人在说话。最近人心浮动,还不是为了那个位子——周一洲!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周一洲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两只手还在那个女局长肩颈处揉捏,一时忘了收回。女局长郁春是见过的,在一次酒会上。那一回,周一洲也没有给她们互相介绍。女局长生得矮而肥,像所有绝望的老女人一样,对年轻貌美的女人怀有深刻的敌意。周一洲私下里曾跟她提起,说人不可貌相。这女胖子,能量巨大。
后来,郁春总是想起那一个场景,想起周一洲彼时的神情。三月底的天气,房间里暖气开得很足。周一洲穿那一件烟灰色薄毛衫,袖子挽起来,因为努力,额上已经有了一层细细的油汗。他半弯着腰,立在女局长身后。郁春也不知道,后来她是怎样离开了那间屋子。她只记得,周一洲很客气地问她,请问——啊呀——转向女局长,电视台的记者,要给我做个访谈的——看我这记性——郁春冲出那道白亮的口子,从那块灰蒙蒙的绸缎的裹挟中逃出来。大街上,阳光慵懒,人们来来去去。路边的玉兰,正在盛期,经了雨水,是那种污了的白色,软塌塌的。郁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让人颓丧的花。周一洲。有时候,郁春心里会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这个男人,他到底是谁?
对面的报纸又响了一下,接着,又是几下,悉悉索索的,不太分明。郁春望过去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把报纸折起来,放在小几上。或许是累了,男人微微欠起身,伸手把小几上的一瓶水拿起来,慢慢地拧开盖子。郁春心里又是一跳。怎么会这样像呢。头发,脸颊的轮廓,下颌的线条,还有额头,在幽暗的光线下,闪着晶亮的光。尹剑初。尹剑初的头发,还要短一些。直而硬,发质极好,发际线清晰整齐,把一张国字脸很完整地托出来。郁春至今记得他在水龙头下面洗头的样子。那时候,还在大学。正是夏天,打完篮球,尹剑初就那样把头伸在水龙头下面,哗啦啦冲洗。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照着他满头满脸的水珠子。他把头甩一甩,再甩一甩,水珠四溅,整个人看上去,又蓬勃,又清新,像一棵春天早晨的大树。后来,当郁春第一次见识周一洲的身体,四十六岁的男人的身体,肥厚的肚腩,松软的胸肌,脖颈和肘关节处,令人心惊的皱褶,郁春总是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哀。岁月这东西,真是无情。郁春也知道,这联想的无理,可是,她管不住自己。其实,现在想来,同尹剑初,或许就是命定。郁春一向是不信命的。当然,那是年轻的时候。什么是命?不过是对生活无能为力的人的一种借口,简单,方便,且易于说服自己。命就在自己手心里握着。就在自己手里,郁春坚信这个。当初,郁春从那个偏远的家乡小镇来到北京,她同命运打了一仗,漂亮的一仗。她赢了,完全靠自己。那时候的郁春,踌躇满志。世间所有的路,都在她脚下,延伸,静静地延伸,等待她选择,启程,去往远方。说起来,郁春是幸运的。毕业,留京,工作也还称得上体面。感情呢,有尹剑初。两个人,都是从偏远的外省来到京城,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腔子里那股子青春的血气,热腾腾的,随时等待着泼洒出去。当然,还有爱情。他们那时候的爱情,是青枝碧叶的树,繁华葱茏,在春天的太阳底下,可以听得见绿色汁液流淌的声音。雨也是细雨。绿色的雨丝落下来,是湿漉漉的闲愁。热烈的时候,也是有的。在校园里,河边的小树林,电影院昏暗的椅子上,相爱的人,怎么样都是好的。后来,郁春想起这一段的时候,一颗心忽然就柔软下来。和尹剑初,更多的,似乎是精神上的相知相契,仿佛一坛酒,青梅黄酒,有甜有酸有涩,只一口,就醉了,再也不愿意醒来。
那时候,郁春住单位宿舍,筒子楼,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安静倒是安静的。可是郁春究竟嫌乱。都是单位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最容易生出是非。卫生间和厨浴都是公用,尤其不便。夜里,穿着睡衣在走廊里,迎面碰上起夜的男同事,睡眼惺忪,脸和脑子都是木的,擦肩而过时候,才想起来要招呼一声,可是嘴巴却是迟钝的,像生了锈的锁,一时且打不开。更要命的是,没有了一点隐私。办公室里衣冠楚楚的男女,忽然就彼此窥见了盔甲后面的真面目,让人在尴尬之余,不免生出人生的悲凉。只有一条,象征性地交两百块房租,几乎是白住。水费电费,一律是全免的。这在房价飞涨的北京,就非常难得。尹剑初呢,在一个亲戚家借住。亲戚是远亲。至于多远,连尹剑初的母亲都一时算不过来。那亲戚做小生意,发了一笔财,在北京购房置业,家境倒是不错。只是有一点,因为自家的出身,对读书人,便格外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时冷时热,让人不好消受。尹剑初的母亲,当初是心疼儿子,腆下一张老脸,硬是求人家点了头。每年寒暑假,都让尹剑初带来家乡的土产,左不过是一些地里生长的东西,不值几个钱,却也新鲜别致,算是一份心意。尹剑初呢,究竟书生本色,脸皮薄,心性高,寄人篱下的滋味,也不是那么容易下咽的。就同郁春商量着,在五环附近租了房。偏远是偏远了一些,好在有地铁。禁不住尹剑初的百般劝说,并且,也实在是住够了单位宿舍,郁春也就搬过来。
现在想来,那一段日子,是多么好的日子!每天早晨,郁春都会悄悄起来,在那个简陋的小厨房里,把早点弄好,然后,叫尹剑初。两个人双双立在洗手盆前,刷牙。你挤我一下,我碰你一下,忽然间,也不知为了什么,郁春就被得罪了,含着一嘴的牙膏沫子,把尹剑初追得满屋子逃亡。早晨的阳光照过来,落在凌乱的床上,像水纹,轻轻荡漾着。窗台上的那一盆吊兰,垂下来,衬着淡黄的墙,一直垂到床边。这墙是两个人自己动手粉的。为了省钱。两个人各戴一顶报纸糊成的帽子,穿着围裙,铲墙皮,刷漆,一遍,又一遍。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后背上都是汗,痒刺刺的,像是无数的小虫子在蠕动。搬家的时候,也舍不得叫出租。都是尹剑初,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把两个人的零碎家私搬过来,像蚂蚁搬家。真正搬过来那一天,晚上,两个人都很有些兴奋,虽然已经是筋疲力尽,可到底还是满怀激越。郁春做了两个菜,买了啤酒,算是庆祝乔迁之喜。尹剑初喝醉了,抱着郁春,跳起了探戈。郁春也有些微醺。灯光恍惚,眼波流转。世界飞起来了。凌乱,眩晕,甜蜜,动荡。一屋子的草长莺飞。后来,在周一洲的别墅里,莫名其妙地,郁春总是会想起这一节。
关于这别墅,周一洲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当初,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城,看遍了所有的大小楼盘。比较,甄别,权衡,论证。这是周一洲的风格。为了窗帘的手感,书橱的明暗色泽,甚至,一只花瓶的形状,博古架上一个难以察觉的疤痕,周一洲可以一趟一趟地跑居然之家,跟设计师反反复复地探讨,沟通。郁春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周一洲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自己在三里屯的一些咖啡馆,还有高档家具城,一转就是一天。他是在观察人家的装饰,地板,落地灯,壁挂,那些颇有风味的小饰物,那些细节,无微而不至的琐碎细节,古典或现代,充满浪漫的艺术气质。他在这些细节的缝隙中辗转,流连,他享受这个过程。有时候,郁春也在电话里跟他赌气,半开玩笑,有些警告的意味。郁春说,等你一心一意装饰完你的杯子,酒却早已经流走了。周一洲在电话那端笑,怎么可能!我只有先把杯子备好,才能装起你这美酒。午后的阳光照过来,是周末的阳光,慵懒,落寞,迟迟地,掠过床的一角,有一多半落在地上,被窗纱笼着,切割成细密的格子,明明暗暗,像一个谜。郁春把手边的电话线一下一下地拽着,银灰色的电话线蜿蜒曲折,一下一下弹着她的手,有一下弹重了,她咬住唇,不让自己出声。你怎么了——周一洲在电话那端问,不待她回答,便说,你好好的——更衣间的壁纸,我还得再去看一看,车子在外面等着呢。郁春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半晌,方才把电话挂上,却发觉由于用力,右边的臂膀已经酸麻了,仿佛有一群蚂蚁在细细地啮咬,一直咬到她的心里。
周一洲的房子,整整装修了一年。后来,郁春第一次走进这幢漂亮的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他们认识的第五年了。那一回,其实完全是偶然。差不多一年了,同周一洲的关系,一直是阴晴不定。怎么说呢,认识了这么久,对周一洲,郁春自忖是十分了解了。可是,有时候,看着眼前这个人,郁春竟然会感到陌生,那种可怕的陌生感,仿佛是一根刺,生生扎进自己的血肉里,一动,就疼,疼得让人忍不住弯下腰来。郁春不笨。在同周一洲的关系中,郁春是清醒的。郁春也懂得,男女之间,那种应该拿捏的分寸,进与退,抑和扬,收与放,张与驰,其间的种种微妙曲折,她如何不懂?可是,她做不到。在周一洲面前,她尤其做不到。这一点,让郁春十分地恼火。怎么回事呢。在尹剑初面前,在众多追求者面前,她郁春的矜持,可是有口碑的。怎么一遇上周一洲,这个中年男人,郁春就不是原来的郁春了?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周一洲两只手把着菜单,认真研究一回,把服务生召过来,开始点餐。郁春从旁看着,他杀伐决断的样子,让人心里又气恼,又有一些莫名的欢喜。比方说,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有自己节奏。郁春落在后面,高跟鞋敲打着地面,急迫而激烈。深秋的京城,已经有了寒意。可是郁春的背上却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想来,那时候,似乎一直是郁春在说话,不停地说,絮絮地,同学的房子,单位的职称,隔壁老太太养的狗,老是把卷毛散落在门前的垫子上面,缠缠绕绕的,真是烦人。周一洲一面听着,一面拿一柄小镊子,仔细地拔胡子,一下,又一下,很是耐烦。周一洲几乎没有胡子。下巴光光的,只偶尔有稀疏的几茎,往往被周一洲及时清除。也有时候,周一洲一面听,一面修指甲。周一洲有全套的修理指甲的兵器,韩国货,既精致,又好用,只那漂亮的盒子,就让人看了喜欢。周一洲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指甲修得圆润整齐,像工艺品。周一洲从容不迫地做着自己的事,耳边是郁春的絮叨。那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让人止不住地心生懊恼。后来,郁春常常恨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