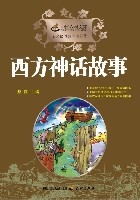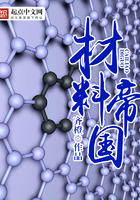你要爱我,要真的爱我,因为我是一个好姑娘。每次你离开中国,我就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你。当然必须悲观地让我也这么想:你也在一天天失去我。
看完《肩后》,萨冈的自述令我平静。
少女的确是有力气挥霍和被人误解,少女大哭后还是可以去劝慰失落的朋友,少女相信,爱人即文本。文本一旦严肃,该溃烂的应当立即溃烂。
美好时代需要屏住呼吸。
你送我一枚戒指,一束鲜花,不向我求婚,回个神,走十里路就可以做一个古人。
真愿意写一本日记画一本画藏在你的坐垫底下。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写作?作态与姿态反差太大,同于坚说,我应该写一首诗,列一堆不喜欢的人的名单也列不完。
遇过让助手代自己画画的人,自己坐在沙发上沏茶聊天,闲下则指挥别人怎么画。此人可以头头是道地讲自己艺术生涯何等艰辛。也遇过批评家一边上网讲道理一边对暧昧对象说女朋友不好。
在年轻人面前,信手拈来,羞。
把写作太当回事的人是无能的。写一套做一套就是有病。
有时只是为了莫名其妙的陌生感觉。
读伍尔芙读得很慢,一天没读上几页,她说早上的阳光,把叶子一片一片化成透明,她说你说的话是白色的,像海边拾来的石子那种素白,我常常看见她的句子,忘了她的故事。
山里的风吹得呼呼,拍打着窗,像咆哮山庄的首回,似乎窗外随时有一只精瘦的绝望的女人的手,要爬进来,找它的前生。
随便在山间走,反正没有地图也不怎么认得路,走进了无际的葡萄园,接壤是同样无际的苹果树园,苹果累累,采一个吃了,清脆甜美,但吃了后不久嘴巴上有麻痹的感觉,才想起,和平时在野外胡乱采捧的不同,果园内定喷满了杀虫剂。
不想走回头路,便按直觉在山林里走,果然迷路,迷路自然要遇雨,遇雨自然没有雨具在身,一身湿冷,走了三个小时,晚上九点才回到人间,风仍是拍窗的风。
千回百转。
看美剧《HOUSE》,我喜欢看,它没有做作的善良,看它时,有时我想生活真是一片不值得的闹剧,我不明白什么叫健康,有时故意让难过更难过。然后让难过不难过。
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琐事,不靠谱。我不喜欢起点,不喜欢终点,两者都太虚无。
真奇怪,我们不相信事物不变,我们也不相信事物总在变。生活不是一种虚构吗?好像酷热的武汉的空调一般虚构。虚构的东西很有力,你的字,你的画,你的肤色。
你的植物没能等你回来,可能它本没认真想要等你,它只是不期然地等待,在没有目的的期待中安静枯死,没有流泪。
我是想念武汉的,虽然你说你不想念。我想念的事情真多,因为我是不懂哭的人,我是拾碎的人。
你选用的照片太悲伤,不是你在照片里悲伤,是因为你选用它的决定。
今天看一位女作家说她的迷茫,她说当代的女人没有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的爽快,今日的女人,要面对的是能有欲望,能注视,能被穿透,能进入,能受孕的身体,而手足无措。
你可以明天就对其他爱你和你爱的男人说你不想爱他们的任何一个,以后也不爱。
你不需要看着镜子说你不爱她。
你在武汉时我总觉得你是比较小的女孩,可能你在外地时我爱想你比较倔强的样子,以为把你想倔强点,你在外地会轻松点。
世上不仁不堪的事情太多,安静像萤火虫般稀有,早阵子读精神分析的书,旧理论说人会做梦是为了保证睡眠,新理论说人要睡眠是为了可以做梦,两种说法都很靠谱。
我的节奏一步步回来了,我不想再惹你担心。
上星期你问我你去死好不好,再早几天你问我你开的车我愿不愿意坐在你身旁,我知道很多事情只能想及不能发生,我仍是想了很多,想了很多情景。
他这个星期学骑马,他要学习和马儿相处,照顾他的马儿的起居,他的马儿伴侣叫Nova,新星的意思,他乐不可支,上星期他对你说他苦恼,因为他的小女朋友黛丝提出和他结婚,他很纠结,他不愿拒绝,又说,他太小了,不该这个时候结婚,你没给他意见,叫他自己决定,他更苦恼了。
嗯,你说这就是我敏感的小儿子。
你教他要爱生命,家里除了蚊子苍蝇你会为他拍打,外来的小昆虫,蜘蛛、野蜂、蚂蚁,你只让捉了赶回花园里去,他乖,习惯了雨后小心避开爬了一地的蜗牛,在学校,他的小男同学太皮,喜欢追踏甲虫,他每天小息时便杯水车薪地先把路旁的小甲虫捉起丢回草丛里,免它们遭祸,他是好孩子。
在看萨义德的书,他是开拓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是他说他至死不忘的巴勒斯坦故乡,我老套地期待温良,在这善忘嚣张的世界。
你之前没有穿上衣在海边的照片,想多说几句,在途上看到时,反应是,好像听到照片无声地喊,“看,看,这个女人”,好像是你把身体剥落下来,像呈现一道伤口那样呈现她,你用一种难过的眼光看着她,也让她被注视着,所以后来我说我不忍心看,所以我求你不要不爱她,因为爱她和爱你不可分离。
我爱你裸露的皮肤,乳房的曲线,爱你的一切。你不用觉得羞涩,美丽都是大方不羞涩的,就像你爱不穿内衣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买不到去美国的机票,她就叫她儿子开着一辆直升飞机出来带你上天兜风。从天上兜完风回来,她在游泳池边等你,你又重复了一遍“我想去美国”。话毕,她把唾沫吐到了你的右腿上。结果,你没有去成美国。你的腿烂了。
醒来时明明听到下着雨的沥沥声,出门却看见天蓝云薄,淡黄的阳光,一下子没能回过神来,一辆自行车在旁边掠过,有一小段路和火车轨平行,刚好火车经过,加速和它并排行驶了一会儿,心里像孩子般快乐。
你沿着暴雨泥路跟朋友讲:一个每天忧郁的艺术家,不是天才,也不是领袖。
复杂的感觉你不要,你要,就要最复杂的感觉。你总心事重重,其实这非常简单。
一个简单的女人的生活,就是保护自己。
有人说你变了,你就天天涂口红。
本来就有异样的幻觉,大半天甩不开,后来你说感觉什么都没有意思,吓了一跳。
生活每一次露出它的底色我还是会被吓一跳,像在远方忽然遇上不友好的故人那样,黏稠的恶心的熟悉感。热带的闷热气味,是该要逃开的。逃到还有想象的地方去。
朋友母亲跟男人结婚搬走了,他庆祝自己终于拥有独立的私人空间,可以不穿衣去洗手间,可以在客厅吸烟,可以带女孩们回家,可以随意摆弄家具位置。这时你在想什么是私人空间,你想迷失在丛林的录音机里。
一旦进入睡眠,梦境自然绕道行驶到别处。拥有太假。
很久没有看见什么有才华的人了,只能给朋友写信抱怨,直到整个过程变成自己为不好好写作感到耻辱诸如此类的语境中。结果,你自己也没有才华了。
做创造的事情情绪不稳定,是有才华的,我坚信这一点。
看完萨冈《肩后》很愤恨,国内大多译者太自负,没才华之外,都要开始怀疑他们的人品。
想着你和看着自己,像蒙太奇的剪接画面,如果是韩剧的老套编剧,我们会平行地生活和想念但老死终不能相见,幸好生活不是电影,生活不完结,即使你我都不在了,也不完结。
读的文章谈的本不是杜拉斯,而是“二战”后的人心深处的痛苦,和它的文化表现,拿了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情人》,因为她常常说死亡。痛,和自愿的禁锢。文章里说:“悲痛是自足的,它超越因果,它抹去所有主体和客观,悲痛是跨越失去目标的现状的最终门槛吗?悲痛不能加以形容,但能被感受,在眼泪里,在呼吸边,在字词与字词间的留白处。”
我不知怎么说我的妒忌,我感到害怕,怕你像是薄玻璃做的那样的那种怕。生活奇怪的地方是,相反的东西不抵消,它们只是一直在相反着。
转走大路,沿湖的一段阳光洒得很大,我天天看着太阳量度日子,像奥亨利的平庸小说。
看Carter的小说令我很烦躁,她写人深处的情欲太直白,不是那种下半身写作的张狂,是那种用针挑出来的痛与尴尬,一针就够了。
我知道你读不下去杜拉斯,你有时觉得她是用暴露来说谎的女人,她说的话你一句都不想相信,我也知道你读不懂萨冈,你有时觉得她是想说谎却不懂说的小女孩,每每读她的故事更心痛。
你不能忍受晦暗的情绪,往往把它翻来覆去,把它提到意识的阳光下,即使是伪装也好。
你越长大会越来越不懂得随心而哭,我不觉得这是好事情。
我的预感是将来的你可能不是我知道的女人,知道的小女孩,我经常为此绝望,只是不曾明白告诉你。
你的逃避与矛盾我都知道,真的知道,有时我顺着你,有时把持不住难过而失调,我把你和自己都看在眼里,我们是雪地的两个剪影。
能哭的时候放心哭吧。我说不出爱你有多深,或者多荒谬。
下午他在公园和一个比他稍大的女孩玩耍,分手前女孩问他明天还会否在公园见面,他答应说会,之后你问他忘了明天去夏令营吗,他说他是故意这样说的,否则女孩会失望,你问他女孩明天见不到他不也会失望吗,他说,女孩明天可能早忘记他了。
是有点不对劲,但你也没说下去。
小路旁一地像橡树的果子,附近可没有橡树呢,还是有呢,拾起一颗把玩了一会儿,丢回林中,想象它长大破裂成小苗子的一天,在小飞侠的故事里,彼得潘第一次见到温黛,温黛为他修补失落的影子,彼得潘说要给温黛一个吻,可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吻,便从怀里掏出了颗橡树果子给她,温黛很高兴,用绳子穿起来挂在颈上,对彼得说,我把你的吻,戴在身上了。
或者你说得对,那令我的品位和你很有差距,我没有对文本那种直接的体会的欢悦,文字对我来说不特别神性,它总是想说出与不想说出的两种冲突的欲望的妥协,它犹疑不决,它因此令人不能自已地爱上,它迷人,迷惑人,它美。罗兰巴特喜欢说文字的性感,他是个令人总想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的同性恋叔叔。
傍晚的阳光斜进来把我的桌面所有能反光的东西照成菱镜般的耀目,又一个夏天将老,老去的夏天不啰嗦,它像洒在湖面上的亮光那样自在,退却无声。
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我不很在乎,我在乎你在,我们以一种难喻的方式同在。
难道你不知道脆弱有多脆弱吗?你是知道的,我又有什么好诧异呢?这几个月来,一直有个想法,你要成为一个女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了,有女人的渴望与空虚,我觉得很难在你的女人的世界里活下去,我想起又否认,否认又压抑,压抑又难过,我拒绝,也因拒绝而好几次情绪低落,那是打开一道门的咒语,那是一个新的国度,你的新国度。
我为什么要说烟花亮丽呢,我最不喜欢在黑暗中消失的东西。
还想说什么呢,当我很老很老的时候,如果再碰上你,我会说。
你对生活的无力感,我的无力感,悲伤也是一种传染的恶疾。
我仍克服不了那种在溶解的感觉。
你不在了,我也不在,没有人能读懂你的字。
我真的很难过。难过是病。
也是药。
人是很年轻的动物。人是会想到死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