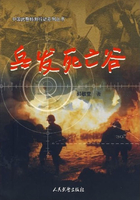翻杂志读到一位美国女诗人说:应付孤独的良方就是独处;觉得她说得有理,便搜了她一些诗作看,她居然写了一首叫“有关鱼”的诗,她说:事实说明它能活/活在即使不回来的青春/海在它身上长老。
读了篇书评,有关女作家丧夫后写的杂文和回忆录,谈到丧偶后第一年最难受,因为生活多年,事事有了陈规习惯,忽然落下自己一个了,同样的事,该装作继续还是故意改变呢?无论哪种,都特别难过。
年年月月,同而又不同,最伤人。
你不可能不写作,就算你是分裂的,就算你在现实里失控,就算你总被某种怪异的情感包裹,就算所有人误解你,你承认,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平静的统一的。
看到你说的难过,你难过,有时没有具体的理由,这次我相信你有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事情,就是总会过去的事情,你好好待待。
看了不少但丁的东西,你喜欢但丁,年轻时读他的《神曲》,很叹服他的想象力与气度,他上天入地,走遍天堂地狱,只为了证明他爱一个十几岁女孩的心意,真是可爱的男人。
我知道你此时在昆明。阴天。留恋双廊、束河。
我是你的安全的秘密盒子,你可以把难过与眼泪寄存在我手心里,放久了,你将忘掉你每颗眼泪背后的神秘。
在昆明早睡早起,昨天在毛旭辉的画室看了很多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速写本,很疯狂,很喜欢。你想,若那时和他们在一起玩就好了。
在花园,说起很多感觉陌生的名字,也有一些不陌生的名字,夜亮,云朵,无月,星出没。
近来看到你字里的激动,不一定一下子明白你的用意,激动不要紧,但不要激动得昏头,要勇于说明自己,坚持想法,也要知道聆听,无须急于把别人推到不喜欢的那些典型里,明白真的不喜欢某些人,便坦然地不喜欢,不喜欢永不嫌迟,只有错失的喜欢,才是可惜。
从印象主义到塞尚再到毕加索,由色彩的舞蹈到几何组件再到空间的抽象,有脉络可循,是我最爱看的一条线索,我近来常常回到古典去,像回乡那样的感觉,有时看出很多新奇。
特别不爱胡兰成,他是个不真诚的人,读他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很恼火,张爱玲作为女人,很笨。
Chagall的画常见上下倒置的人、空中跑的马、睡着漂浮的女人和很多很多的蓝。
看窗外,以为天气还好,经过走廊,见玻璃天顶上爬满水珠,看了电影《前度》,戏里有一只知道流泪的水杯,懂干涸的喝,吃掉记忆的乡下小屋。
我喝了两杯红酒,白黄的灯光也是,染成粉橙颜色。
种下的籽长成两寸多高的短苗,天天浇水,他说六月会开花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胸有成竹,他也为另一盘种了胡萝卜的拔去野草。
跟树木打招呼,它们每天的颜色样子都不一样,多年前看一出拍画家在花园画树上石榴的影片,每天只有晨光或黄昏的瞬间光线最美,画家每天捕捉,总不满意,终于果子熟透了掉下来了,画家把它们放在陶碟上,看着,很自得其乐的样子。
我们的屋顶是蓝天。
尽管我也很奇怪地在想“遥远,沉默”。
他的剪刀、椅子,有造型、爱、无能为力。不知道你为什么也开始画画?行了,你把Love story太当回事了。
他在翻看他书架上的旧书,读了一本叫《天使的灯火》的翻译小说,和日本作家写的《窗边的小豆豆》;他之后告诉我,《天使的灯火》故事的起始很忧愁,但结局很快乐,《窗边的小豆豆》原是快乐的故事,但结局很难过,他说,故事真是奇怪的事,生活真是奇怪的事。
我一直想着你。你为什么要问我生活是否快乐?我回了你的信后觉得自己很虚伪。想你是很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不一定使生活快乐。生活真是奇怪的事。
一辆锁在柱子上的自行车,真的是被锁住了吗?主人会觉得自己的自行车不会被偷走吗?我觉得主人被观念严重干扰了。如果真想自己的自行车不被偷走,我会把自行车挂满锁,直到它看上去不像一辆自行车。主人,主人啊,我是小偷,我根本不用破坏柱子就可以把你那把锁解开,很多人都可以。我也可以跑。只要我不穿裙子的话。
赫拉巴尔的自传写得很奇特,他用他的妻子的角度写自己,有不少是自吹自擂的,颇受不了;有些局部也有趣,例如他说他邻居的一个茨冈女人,她丈夫是个酒鬼,有时打她,她跑到赫拉巴尔那里睡觉,她的小女儿便睡在柜子的抽屉里。
像童话故事,但没《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的茨冈女孩那么美;我仍不时看看赫拉巴尔,你仍不喜欢他。
苍山绵延,洱海富饶,美云浮躁。
我设想我是我,是山,是云,设想山需要云停下,设想山跟云去远处寻找毁于一旦的美感,这美感残酷得无语。
一天,山见云,对云说:你能停下来,陪我吗?
云说:我不能陪你,我只是一片云,你会看见很多其他的云。
山说:好吧,你走吧。
又有一天,暴雨来了,雷鸣来了,它们像疯了,它们疯了。
很多云变成了一朵云,它们从明变暗,直至黑。黑云变成了雨露,它覆盖了整座山,并滋润了它。这时,山对云说:你不是云,你是雨露,我不爱你。
知道本拉登被捕杀的新闻,心情很复杂,我没有廉价地亲美国或者反美国,只是仍然常为政治的阴暗而难过,我很怕听到那些侃侃而谈指指点点的话,人心的恐怖,不是什么人都懂得。
真希望把头埋在小说电影和其他艺术品的世界里,只喝酒,不喝现实。
你知道你用文字写就的天地,多么干净怡人。
希望每个人都能多点看到美,珍惜美。
他有天问我可不可以有一天不喝酒,之前我跟他说但丁的《神曲》的内容,他担心我喝酒太多将来上不到天堂。
假如天堂像博尔赫斯说的是个偌大的图书馆,我会考虑申请移民进去的。
关于拉登,再说一句,一个弱势民族的执着的人往往只能选择恐怖,也终被恐怖拉了去,对美国特别不顺,在战争状态中故意杀害平民来达到威慑的政治目标,美国做过,它把两枚原子弹丢在已经战败的日本平民头上。
读书,听的是Glenn Gould的钢琴,Glenn Gould是神人,他弹的固然是古典名家的作品,但常不按谱,随心所欲,不管名家不名家,呼来招去,潇洒得很,有时他边听边哼唱,在他自足的世界里,多美丽。
你要大度,大度便能挥洒自如。
看了维斯康提拍的《魂断威尼斯》,看得反反复复,画面真美,演少年的那位瑞典男孩,像天使,难怪在片子里的想念,是命定的。
汤玛士·曼不是合我脾胃的作家,也禁不住找他的原著小说来读一下。
今天,第一轮盛开的花开始瘦下来,花粉的狂欢也快完结了。
剪了一小捧白色小野菊,玻璃瓶,淡白灯,它们伴我读书,野花剪下来要早谢,我有些怜惜,它倒无所谓地,开放着。
回来时在车子里听列侬的《Imagine》,想这几天的国际新闻,我们对生活的想象力真的很贫乏。
该找一个下午什么也不做,只躺在天空底下。
今天看的电影《黎明前与你相遇》,有法国电影一贯的冷静,和冷静底下冒出来便阻止不了的压抑,很简单的故事,对故去爱人的想念,不受日常生活的洗磨,变得凶猛,化成魅,迷人。
爱你的,都想你少走弯路,真的走了弯路,想你不受伤害,受了伤害,想抚平你的痛。
在读纽约书评,知道了一个没读过他作品的美国作家,他自杀死了好几年了,读了一页,决定先不读下去,反正他已在没有时间那边等待。
有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你跟你前男友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每一段感情,无论悲喜,都该是独特的,不容其他人评说,一方面,爱着一个人时,总带着不少的自我,不容从容的客观姿态,我矛盾地想,我希望,你得失之间的总和,是个正数,希望每一个人对你的每一种想念和爱情,都将是你的正面的得著,尽管之中有难过,有懊悔,有怅惘,尽管它之中也有欢喜,感恩,与曾经的幸福感受,尽管你还是矛盾着,不知道心里的反映该是哪种模样。
我还相信,每段真正投入的爱情都能经得起洗涤,都藏着泛润光的珍珠,只是,一时未必明显,时日可证没有白付的心,美丽的东西还是美丽的。
有时不知除陪着你外还能给你什么,除想着你外还能给你什么,希望你觉得有伴,不孤单,希望你勇敢长大,希望你能安心,因为你脆弱难受时,你总是我拥抱的小女孩。
途上柳絮纷飞,想起那曾沾在你帽上的,柳不是吉祥物,有柳树的花吗?没有,却明明听到花落的无声。
有命运这回事吗?有的,但它没有比日月升沉更多更美或更冷。
每天的景物依然,令人担忧。路上堵车,爬行乡村的小路上,看骑单车的在身旁呼啸而过,听的仍是钢琴独奏,昨晚的电影还是看不完,时间像空气,悄悄。
几年前,在莫斯科的一个早上,你负责的谈判失败了,心情不好,清早在普希金广场散步,没一会儿,下起大雪,沿路迎着雪铺满一身,衣衫不足抵冷,你躲进刚开店门的酒馆里要了热咖啡,店员是年轻有文身的俄罗斯男孩,为你煮了咖啡便自己忙去,你在店里待着,在时髦的酒吧里,看见壁上一角,挂了东正教的圣母画像。
你最爱看的圣母画像,是东正教的悲伤圣母,她的眼神放远,眉目无情;伤感是一种距离,一切宗教,提示的都是这种距离,想要克服的,是失去的空洞;天主教后来把圣母绘成柔情低怜的女性,便没有了灵光。
忽然也想,拈花微笑真是难过的刹那,慈悲是复杂的迷宫。
你想晚点回住处,回去后你肯定会是失眠的,你会洗澡、看书、画画,可能还会胡思乱想一番,因为你知道,你今天的心情的确是糟糕透了,你每天都在坐出租车,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有时开心有时忧愁,你知道自己忧愁什么,你就是这样反复起伏不定的女孩,很多男人都会受不了你,是不是有一天,你也不会理解自己,会觉得这个姑娘怎么这么难搞定,你也觉得自己是挺难对付的,你知道吗,你总是对付不了自己,你想开辟一个小地方,躲在那里写东西、生孩子、做爱,太难了,你总是待不住,你待不住,你早已预见了命运,你是一个会飞的女孩,你是命运缥缈的女孩,你从这里飞到那里,你也不知道最后究竟会飞向哪里,你不知道命运要给你什么,你知道给命运什么,你是喜欢北京的,它其实没有错,错的是你,你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采访,为了跟每一个你选择的对象对话,只是你高估了自己的本能,有的根本无法交流,这些其实也不是他人的错,谁对谁错都不重要,你应该勇敢面对这些,坦然面对自己的心绪,你老是这么不肯定是不好的,总之你是错的,你该预见这些要面临的问题,你面对过许多问题,你忧郁无助地坐在房子里哭,你是一个无论何时在哪里都哭的女孩,这一点也真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爱哭呢?你为什么总是关在房子里看各个美丽的人写的小说呢?你太喜欢那些能写出美丽文字,那些悲惨命运的小说家了,你的朋友S不希望你的命运像杜拉斯和萨冈那般不好,你不知道什么是好和不好,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说,我们需要虚构一封情书,你在咖啡馆待了八个多小时,你在低迷的情绪里没想停止敲打键盘,你的写作也是飞跃的迷离,呵,你知道这说法有点俗气,迷离的事物一直都俗,迷离的事物常常伤害着你,你五体投地。
你想,咖啡馆里的人真多,为什么中国人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待着呢,你觉得这儿只有写作的人才可以来。这想法有些偏执,不过没关系,我同意你,我也觉得不写字的人(或者说不思索的人)的确是空的,空的动物不能在咖啡馆里撒野;我是在咖啡馆里泡大的,深懂你的感受。
这儿的服务员态度很好,这儿的水很甜,这儿的沙发是黑色的,这儿有很多椅子,红的、绿的、黑的、灰的,这儿的桌子是核桃颜色的木质,你喜欢木头,你恨不得自己也是木头做的。
你的面孔充满诸多奇怪元素,你不知道当你投入到一个人的怀抱里是不是想证明些什么。你想证明什么?你想证明自己就是高更笔下的塔希堤吗?你真是吗?她真能被取代?你又想,其实那人才是你的小男孩,而你,你是他的老女人。
当然,你知道那人为什么爱你,他爱你的写作,你知道他是爱你写作的,他想爱一个写作中的女人,他当然也知道你为何爱他。你们没有声音。
在咖啡馆里长大的女孩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