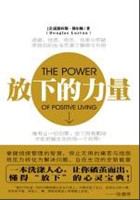刘子夕想:不会吧?如果一个男人的条件还算不错,为什么要找袁小玉呢?现在的男人稍微有点可恃的条件都觉得是自己的筹码,那是万万不肯吃亏的,一定要把女人放在天平的那头称一称,看看对方的筹码能不能比得上自己的。平心而论,袁小玉又不是什么大美人,在一个普通的公司里打工,充其量也就是个低级小白领,工资不高,也不会有多少积蓄,这男人愿意娶她是图什么?听起来怎么就让人觉得一定有陷阱在里面。
刘子夕不死心,又不好赤裸裸地明着问,只好说:“那他脾气怎么样?身高怎么样?”她相信这个男人一定是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存在着什么缺陷,袁小玉一定是还没来得及发现,她作为她的阶级姐妹应该提醒她一下。
袁小玉的回答还是让刘子夕意外了,她说:“脾气还好吧!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什么怪异,要是现在就看出来了,那还结什么婚。身高嘛,大概比我矮半头。”她说得如此心平气和,以至于让刘子夕觉得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矮半头?袁小玉就没高到哪儿去,他居然还要比袁小玉矮上半头,那不就是一残疾吗?她还以为这男人是某个内在的隐秘的地方有什么缺陷呢,搞了半天这缺陷就在明处摆着,还是硬伤,而且是第一眼就能看到。这袁小玉真够狠的,就能对自己狠得下来啊。真是把问题彻底想明白了,抓住那点最主要的核心,其他的枝干一律可以省略,就当没看见。人家有这样的魄力要是还嫁不出去,那还有谁能嫁出去?
袁小玉是十月办的婚礼,不过一领到结婚证就搬过去和那男人住了。她来来去去了好多趟,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自己那点东西陆陆续续都搬走了,最后她住的那间屋子便彻底空了出来,她和她的东西像水一样从那间屋子里慢慢蒸发走了,用手挡都挡不住。
袁小玉举办婚礼的那天,刘子夕和梁惠敏都去参加了。两个人在一起住了一年了还是觉得挺陌生的,像这样一起出门真还是头一次,像两种不同的材质,就是绑在一起也通不了电。两个人像两张不粘胶一样疏离着、冷漠着,一起到了酒店门口,远远地就看见新娘和新郎正站在十月的秋风里。新娘穿着露肩的白色婚纱,尽管是租来的,那穿在自己身上也要穿成是新的一样。这些繁琐仪式哪个可以不执行呢?都是做给人看的,可是人活一辈子哪个不是做给人看的?给自己看的又有多少?
新娘裸出的肩膀陡峭地却是屹然地露在那里,谁还有几次办婚礼的机会不成?好歹就这一次,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扛着。她们终于见到了那个隐形的新郎,他站在穿着高跟鞋的袁小玉面前简直不是矮了半头,而是一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新郎,像个站在新娘身边的穿着西服的小花童。因为高出了一头,这是傻子都能看出来的硬伤,反正是遮不住了,倒使人有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过瘾心理,藏不住的裂缝就干脆撕得再大些,索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所以尽管两只脚是藏在婚纱下面的,袁小玉却毫不肯给新郎面子,仍旧穿了高跟鞋屹然站在那里,只管让自己看起来婷婷袅袅,享尽了新娘的绝代风华。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一定要让自己在今天达到巅峰,决不能辱没了自己。袁小玉在这种决绝悲壮的心理支配下特意选了一款大红色的口红涂上,被雪白的婚纱衬着,大有烈焰红唇的效果,看起来她似乎整个人都要被那两片红唇烧着了。
见到刘子夕和梁惠敏,袁小玉伸出戴着白纱手套的手,作出拥抱的姿态。两个人都过去和袁小玉拥抱了,虽然有点话剧式的做作,但抱在一起的一瞬间,还是有点苍凉的暖意涌向全身的各个地方。她们都明白,这一抱是带着些别离的意味,似乎象征着她们从此就别过了,以后她们将会消失在人群里,像水珠一样从人群里蒸发,她们将再无法真正找到彼此。旁边的新郎只是搓着手,呆呆地笑着,一副高兴过了头不知道该把手往哪里放的架势。这男人不仅小而且瘦,就像是比常人小了几个型号,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都能装进袁小玉身体里面去。
酒席上刘子夕有些微微的怅惘,忍不住想起了张末的婚礼,又想起了杜明明,不知道她和博士又是举行的什么样的婚礼,不知道博士的病治好了没有,毕竟博士的其他条件还是不错的,要不自己怎会一直惦记着。想着想着,忽然觉得人生真是虚幻啊!有什么意思,这些女人为了图这么点东西就把自己给嫁了,嫁给矬子,嫁给性无能,什么人都敢嫁。而男人呢?什么人都敢娶,钟昊佐娶张末,一娶就换了工作,真像是女人嫁好了就有钱花一样。刘子夕这样想着就多喝了几杯,也没有和谁碰杯的意思,就是自己想多喝几杯。
从酒席上下来走出去被风一吹,刘子夕立刻觉得头晕起来,便扶住头不肯再往前走。站在她身边的梁惠敏见了就扶住了她的一条胳膊,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下了车又搀扶着刘子夕磕磕绊绊地上了楼。
刘子夕先是倒在床上天昏地暗地睡了一觉,等一觉醒来看到窗外已经是昏黄了。现在是暮色四合时分了,竟睡了整整一下午,这才开始回想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既然喝多了酒,那是怎么回来的?模糊中想起了梁惠敏,好像是那个女人扶着自己回来的。在一起住了一年了,两个人基本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么近的身体接触还真是第一次。仿佛是不应该的,就好比一个人已经在户外冻惯了,忽然被让进了温暖的屋子里,靠着火盆,穿着棉袄,乍寒还暖,身体多少是有些消受不起的。可是最初的那点不适应过去了,也就还是贪恋起了屋子里的温暖和炉火,人都是肉身长成的嘛,知道冷就知道暖,有谁是心甘情愿让自己受冻的?除非是她的全身神经都麻痹了,和植物差不多了。
刘子夕想爬起来,一动才觉得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便奇怪自己中午怎么会喝那么多酒,又不是应酬,又没人强迫她喝,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地喝上了。正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她吓了一跳,因为袁小玉已经搬走了,这屋里唯一可能敲她门的人不在了,那会是谁敲她的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梁惠敏。她从床上爬起来,蓬头垢面地去开门,站在门外的果然是梁惠敏,除了她的人,还有她手里的一碗汤。刘子夕还没开口,门外的梁惠敏就先开口了,先发制人的意思,却是为了消除两个人之间的尴尬。梁惠敏说:“我煮了点排骨莲藕汤,顺便给你盛一碗,喝了酒的胃要喝点热汤才能舒服的。”
刘子夕接受了这碗汤,她没理由不接受,不接受就是她不识好歹了。那汤看起来炖了很长时间,已经是雪白的颜色,里面沉着一块排骨和几片白玉似的藕片,还漂着几粒鲜红的枸杞。只看着就已经让人觉得很舒心了,喝了一口汤,觉得真是很鲜,顿时从心里对梁惠敏刮目相看。她们三人平时偶尔做饭也是各自做各自的,单身本来就懒于自己弄饭,倒是常在外面吃,不过也很少在一起吃饭,更没有机会知道对方的厨艺。没想到梁惠敏那副世俗的模样下竟深藏着这样不凡的厨艺。一碗汤喝下去果然觉得酒气被压下去了,胃里舒服了许多。真是吃人手软,喝了人家一碗汤,就觉得对人家什么意见也没有了,只觉得一片感激之心在腹中荡漾,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总该尽到人情,她便趁着还碗的机会拿了一盒储备下来的德芙送给了梁惠敏,还没有忘记夸她的汤好喝。梁惠敏收下她的德芙,大概也是有些受宠若惊,连忙问:“要不要再喝一碗?还有的。”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最难相处,因为不是最复杂就是最简单。收买一个女人有时候一碗汤就够了,有时候十个金戒指也不行。
两个人便趁着换物的空当聊了几句家常话,就像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多少年都没有见过彼此的面,却因为自己家的倭瓜爬到对方的院子里了,两家便爬上墙头,趁摘瓜的时候说起了话。
刘子夕讪讪地问:“好久没有见你弟弟了,他怎么不来了?”
梁惠敏低头说:“他毕业了,正在准备考研。”
看她不愿意多谈的样子,刘子夕立刻住了嘴,知道这是个不要轻易涉及的话题,忙改口说:“你看人家袁小玉多有魄力,说是要在下次搬家之前把自己嫁出去,果然就嫁出去了。”
梁惠敏听了这话便也回升了温度,迎合着说:“就是就是,就剩下咱俩了,咱俩不及人家有魄力。”
两个人抓住袁小玉品头论足了半天,反正她已经不在这屋里了,人去楼空,总得为剩下的这些单身女人做点贡献,哪怕仅仅作为她们的口头谈资。两个女人都用了比平时更大的声音说话,好像生怕对方听不见的样子,憋足了劲一般,就连笑都是很夸张的,大声地打着哈哈。袁小玉被两个女人的嘴轮番揉捏了半天,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榨出来的了,两个女人才分头散去。
又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中秋一过很快就是冬天了。虽说两个人住着也相安无事,可是袁小玉搬走后还是起到了一些眼睛看不见的效应,比如这三室一厅的房子竟像三脚柜缺了一条腿。三个人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起来,就像一只珊瑚虫搬走了,整座珊瑚竟露出了水面,而且这空出一间的屋子就像嘴里的豁牙,白白空着,看着就难受。还是要再找个女孩住进来,好分担一点她们的房租。合租启事贴出去没几天,一个女孩找来了,手里拎着两只巨大的皮箱。
这个女孩叫汪静路,今年七月研究生刚毕业,到这座城市里找工作来了,她原来租的那房子房东忽然要用,就把她赶出来了,她只好急急地再找。刘子夕有些奇怪,她既然大学不是在这座城市里上的,老家也不是这里的,怎么跑到这北方的二线城市找工作?而且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找工作和房子。
汪静路性格倒也爽快,住进来不到一天就把自己的底细全交代清楚了。原来,她的男朋友在北京工作,她在北京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想到随便参加了考试就考上了这个二线城市的公务员。好在这城市离北京也就三个小时,和男朋友见见面还算容易,就打算先在这城市里定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汪静路说:“宁可在小城市当公务员,也不去一线城市当牛做马地打工,那样的生活,心里既不安定,生活上也没有多少尊严感。”
尊严很重要,她一再说,以解释她为什么来到这座二线城市,她可不是被北京赶出来的,她不是没有那个能力,是她心甘情愿地从那个城市里出来的。
梁惠敏问:“你不怕你和你男朋友不在一起夜长梦多?”
汪静路一笑:“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怎么也到不了你手里,急什么。”
刘子夕想,这女孩子倒是厉害,对她多少有些畏惧,来往便也不多,下了班就只钻进自己的屋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刘子夕发现这女孩子有的晚上是不回来的,经常夜不归宿。梁惠敏充其量回来得晚些,却是一定要回来的,汪静路则是干脆不回来。她男朋友不是在北京吗?那她又是去哪儿过的夜?莫非因为男朋友不在身边就已经在这里找了个情人。
其实刘子夕猜得不错,汪静路确实有个情人,有时候晚上就在情人那里过夜。她去的时候经常是坐晚上十点的公交车,那时的公交车很空,几乎没有什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