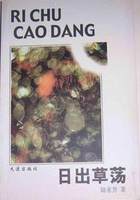与越来越少的精河水不一样,精河河岸上的房子倒是越来越多了。米娜奶奶嫁到精河镇的时候,附近可没这么多人。那时候,精河岸边的这块高地上,只有不多的二三十户人家,每户之间隔开刚好烧开一壶砖茶的时间,邻里之间既不会感到隔墙有耳,也不会远到走动起来觉着不便,适中的距离反倒使彼此之间终年怀有亲近和信赖的情愫,新生儿的啼哭声会让镇子里的每个人都喜悦,死去的人会受到镇子上每个人的尊敬与哀悼。可是,眼下情况全变了,高地上见缝插针盖满了房子,但房子里住着的人米娜奶奶从来记不住他们的脸,他们来了又走了,每一次都是新面孔,每一次都带着新口音。
米娜奶奶从不与这些急着来到又急着离开的外乡人来往。这些人都是冲着精河水来的。他们都是些因为无子而陷入痛苦的夫妇,长期孕育的失败让他们既绝望又不甘绝望,因此每个人都面颊塌陷、憔悴不堪。除了有关精河水催孕并使奇迹成为现实的消息,能使他们的眼睛流溢出一缕油亮油亮的光泽,其它时间,他们的眼睛都是灰黯的,连无精打采都谈不上,简直就是瞎子的眼睛。这些外地人的生活笼罩着阴影,所以从不会给精河镇带来快乐,时间长了,土生土长的精河人会半带同情半带挖苦地嘲笑这些外乡人:“那些男人都给吓怕了,他们以为干那事就是把水舀进水桶那么简单,气都不敢出,他们哪知道咱们的女人为这事会快活得要让咱们死死按住她们的嘴才不至于把咱家的房顶掀翻……”
精河的水是能够催孕的——传言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拨又一拨前来精河镇求子的外乡人。在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之前,这些外乡人就已经精河水当药似地喝进肚子里了。后来,突然又来了一个姓黄的南方老板。黄老板让人把精河水放在瓶瓶罐罐里带到精河人谁都没去过的大城市,翻来覆去进行检查。消失了将近半年之后,有一天,黄老板再次从天而降。他拿着一撂谁也看不懂写着什么的白纸,关着门窗,秘密地在铁镇长家里合计了两天两夜。再后来,他们找到了昆齐爷爷。他们把昆齐爷爷请到铁镇长家里,用刚宰的一只小羊羔款待了昆齐爷爷……
那件让米娜奶奶难以启齿的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5.
具体的时间谁都说不清了。只记得是个初春的日子,黄老板、铁镇长,还有昆齐爷爷,三个人围坐在铁镇长家的一张方桌前,蛮不在乎地开起了男人之间的玩笑。黄老板连声夸赞昆齐爷爷至少能够活到一百岁,并用一种油腻的眼神打听昆齐爷爷的隐私。当问到昆齐爷爷还能不能和女人做那种事,昆齐爷爷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继而捋捋胡子,嘴角撇出一个得意的微笑,最后,认认真真地说:“我行。”
黄老板和铁镇长一听哈哈大笑,于是,接下来三人的谈话就转入了一件能够改变每个人命运,同时也能改变精河镇命运的大事。首先按捺不住的是黄老板,他举着那沓谁也不知道写着什么的化验报告,告诉昆齐爷爷:那些关于精河水能够促孕的传言,经过科学验证,全都是真的,精河水丰富的矿物质确实能够激活男人的精子女人的子宫。昆齐爷爷听着有些糊涂:“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精河镇的男人从来没为这件事操过心。”黄老板眨眨眼睛,说:“昆齐爷爷,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啊。”
事情接下来就越说越清楚,也越说越荒唐了。因为精河水的特殊功效,黄老板决定在落后偏远的精河镇投资建厂,专门生产能够催孕的精河牌矿泉水。但是为了让矿泉水的品牌一炮打响,必须要让人们亲眼见识精河水的厉害,要让人们看到事情从不可能变成可能!黄老板与铁镇长思来想去,认为这件事从各个方面来看,昆齐爷爷都是最佳人选。一来他年纪够大,二来他身体够好,倘若快九十岁的昆齐爷爷能让一个女人怀孕,一旦成功,等于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这样一来,白白流掉的精河水每一滴都能变成和金子一样值钱了。
铁镇长接过黄老板的话,继续说:“昆齐爷爷,黄老板的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他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可咱们精河镇的人,还赶的是毛驴车,昆齐爷爷,你一辈子没去过省城吧,咱们得为儿孙们想想了,咱们得让儿孙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放心,这事情不只黄老板一个人得利,精河水是每一个精河人的,等工厂建成了,精河人每个人都是工厂的股东,股东就是小老板的意思,只要精河流出一滴水,这一滴水的钱每个人都有份。当然,昆齐爷爷,你的功劳最大,你是最大的股东,别人得一倍的利,你得十倍的利,有了那些钱,你的儿孙们几辈子都吃不完呐。”
昆齐爷爷听得脑门子发烫,胸口汗津津的,脑袋里活像飞旋着一群苍蝇,嗡嗡乱叫,一时捋不清思路。昆齐爷爷想,跟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怎么七绕八拐突然把他卷了进去,不仅如此,他竟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非他莫属。后来,稍稍明白过来之后,昆齐爷爷心中十分振奋,他没想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够干件大事。
依照昆齐爷爷年轻时的性格,这事儿准保在当天就能够一拍即合,然而,等到黄老板和铁镇长说到要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做这件事时,他突然冷静下来。当然,这种事情只能和另外一个女人做,因为米娜奶奶的子宫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被激活的。但怎么和米娜奶奶说这件事呢?他怎么开得了口呢?
但是昆齐爷爷犹豫了两天,还是对米娜奶奶说了。
昆齐爷爷说:“铁镇长向我保证了,只要能干成一次,咱们就成了精河镇的大恩人,他会报答我这个大恩人的。米娜,我的心肝宝贝,到时候,你随便提什么条件都行,唉,如果能行,咱们的孩子们也不用再为钱犯难了。”
“你难道不害臊?”米娜奶奶觉得昆齐爷爷疯了。
“米娜,米娜,你别生气,铁镇长让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我还是告诉你了。”昆齐爷爷有一张精河男人传统的脸,大鼻子,高颧骨,皮肤黑红,嘴唇红中透紫,下巴上一圈长短相宜的银白色胡须显得他兼具气度与活力。看见米娜奶奶睁大的眼睛,昆齐爷爷反而劲头更足了。
米娜奶奶为这件事和昆齐爷爷生闷气的时候,铁镇长一再催促昆齐爷爷赶快拿定主意,他私下里对昆齐爷爷说:“昆齐爷爷,投资建厂可是精河镇的一件大事,黄老板到哪里都能发大财,咱们要趁热打铁,黄老板要是等得不耐烦,又找到了别的财路,这件大好事就会像精河水一样白白地流掉了。”
昆齐爷爷还是有些犹豫:“你去问问别的人愿不愿意。”
“黄老板临走时再三叮嘱我,只要昆齐爷爷,换了别人,他一毛钱也不出!”铁镇长为这件事情着了急,嘴角起了一溜又红又亮的水泡。
05
从一开始,米娜奶奶就知道拦不住昆齐爷爷,她心里清楚得很,昆齐爷爷要是自个儿不愿意,整件事情就到不了她这里。昆齐爷爷真伤人心呐,虽然是半路夫妻,但两个人一直是真心对待的。昆齐爷爷是让铁镇长灌了迷药吗?一出口,就把事情全扔在了她的肩上,好像全看她的了,不仅昆齐爷爷盼着她,铁镇长盼着她,精河镇的人昐着她,连未出世的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的儿孙们都盼着她。这可叫她承受不了。
米娜奶奶没有继续逼问昆齐爷爷。事到临头,一个人的心思会像剖开腔子的羊一样,心肝肺一个不少,什么样儿全都露了出来。生闷气的那段时间,昆齐爷爷最初还有些羞臊,常常躬着背坐在床边,两只关节粗大的手安份地搁在两腿上,眼睛不时心虚地瞥一眼米娜奶奶。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两个人面对面吃饭,昆齐爷爷只剩下一脸地不高兴,不仅一声不吭,连眼睛都不抬一下。
知道自己拦不住昆齐爷爷之后,米娜奶奶感到自己骨头里的冰又厚了一层。已经四月初了,她反倒把那双扔在一边好几年的毡筒靴拿出来穿上,又给膝盖上缠了厚厚的白布。毡筒靴又厚又重,米娜奶奶从早到晚不离脚,一直穿到太阳往天空中滴火星子的季节。
昆齐爷爷私下里与铁镇长拟定了一个协议,协议起草得十分简陋:事情是昆齐爷爷自愿的,谁也没有强迫谁,如果成功,精河镇一定发给昆齐爷爷的一笔很大的奖励。协议上还额外附带了昆齐爷爷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事情办成之前,整个计划必须秘密进行,不能让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知道。协议上摁了鲜红的手印,一张留给铁镇长,另一张昆齐爷爷藏在冬天的一件棉衣口袋里。昆齐爷爷去世后,米娜奶奶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这张协议。只是到了那时,事情既没像昆齐爷爷所希望的取得成功,也不像协议中所约定的秘密进行,计划刚刚开始进行,整件事情就好像春天的大风吹遍了精河镇,又卷带着飞沙走石,尽可能远地吹到了精河镇以外的地方。
“德明说得对,脸都给丢尽了,铁镇长一句话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太阳开始往下扔火星子了,空气烫得伸不出手,挨上去就冒烟。米娜奶奶躺在毛毡上,火星子掉在她的胳膊上,衣裙上,小腿肚上,一滴滴都服服帖帖化成了温暖的水流。米娜奶奶的身体跟大冬天泡在热水盆里一样舒服,她在方巾下面睁着眼睛,发根与脖颈里渗满了汗水,突然就下定决心。
“至少得说点儿什么,一句话不说怎么能行?”身体的舒适让米娜奶奶猛得生出了早年守寡时的韧劲儿。说实话,这一生她很少感到心中充满勇气,绝大多数时间,她只是逆来顺受生活给予她的一切,只要还能活下去,她就能忍受一切。或者,话该倒过来说,因为她能忍受一切,她才活到了今天。就是这股倔强的耐力,让她一个人把孩子们养大成人。只是,他们个个活得都让她感到愁苦,大儿子赌博输掉了老婆,两个女儿不是挨丈夫的打,就是孩子需要不停地花钱看病。而这一次,她的忍耐又让她默许了昆齐爷爷的荒唐事。她似乎什么都能忍,什么愁苦都能默默地吞咽。但德明的话确实激起了米娜奶奶对自己含辛茹苦、对昆齐爷爷做的这件荒唐事的怨气。
怨恼慢腾腾地上升,就好像身体里一点点融化的冰。米娜奶奶不再想忍气吞声了,两次守寡,每个男人都留给她没完没了的烦恼。
心里有了怨气,站在房顶上的米娜奶奶躺不下去了。她下了木梯,朝着坐在窗前土台上昆齐爷爷的影子瞄了一眼,喃喃地说道:“得让铁镇长说点儿什么,让他知道丢脸的事搁在人的心上该有多不好受!”
06
“天这么热,精河的水却越来越少了。”晚饭后,空气又湿又闷,燠热在地面上升腾,仿佛蒸煮着人间。米娜奶奶脚下有些拖沓,下午,膝盖莫名其妙疼了起来。走进镇长家的院子时,见到铁镇长正蹲在窗下卷莫合烟,她随口嘟哝了一句。
“米娜奶奶,你好啊,你的腿怎么了?”铁镇长瞅了一眼米娜奶奶,又伸出舌尖仔细舔湿烟纸的边缘,卷好一根烟。
“膝盖上的老毛病,唉,人老啦。”
“坐,坐下。”铁镇长给米娜奶奶递过来一只胡杨木矮凳。
“米娜奶奶,羊毛的价格上来了,你得抓紧赶快剪完。”米娜奶奶一进院门,铁镇长的心就往下掉了一截。他有意叉开了话头。
“还得几天呐,一个个都想偷懒,耍赖的都还不算。”米娜奶奶有几十头羊交给在大青山上放牧的牧人管理。
“你把德明放到山上帮你看着。”
“那可不行,用不了几天,羊准会全都给他输光。”
铁镇长穿着一件洗薄了的老头衫,蹲在窗下一边眯着眼抽烟一边和米娜奶奶说话,隔着缕缕烟雾,他在想米娜奶奶找他什么事。
“镇长,我想问问昆齐爷爷的事。”
“昆齐爷爷,什么事?”
“昆齐爷爷活得好好的,突然就走了。”
“米娜奶奶,你可要想开一些,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铁镇长,你倒说说看,往后的日子怎么个好法?”
夕阳在铁镇长家的院门外露了半个橘红色的脸,一绺斜长的光芒穿过门扉,直抵到铁镇长的两只赤褐色光脚丫前。铁镇长两根指头夹着烟,眼睛望着脚前的光芒,默不作声。
铁镇长瞥了一眼米娜奶奶。米娜奶奶无声地坐着,半垂着眼睛,像一片苍老的浮云,落在他家的院中央。从侧面看,米娜奶奶更加瘦削了,下巴尖细,花白的头发絻在脑后,那件灰白色的连衣裙洗得像纱一样薄,两只手木然放在膝前,似乎握着一张纸。问他话的时候,声音淡得像没加盐的白菜汤,神情漠然,像是对什么事情都一无所动,也像是从没有生过怨恨。然而,瞥过一眼之后,铁镇长莫名地觉得他仿佛在跟一个影子说话。
“镇长,昆齐爷爷留下一张字条,这字条上的事你跟我说说。”米娜奶奶打开手里的协议。纸张折放在昆齐爷爷棉衣口袋里,时间长了,边边角角都打了卷了,但纸上的字迹和纸中央的红手印都清楚得像昨天才写和摁上去的。
不用看,铁镇长知道那是什么。那一刻,他的脑子从未有过地快速飞转起来,就好像正在发动的四轮拖拉机,噔噔噔冒着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