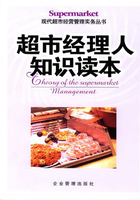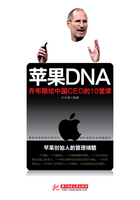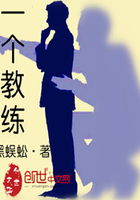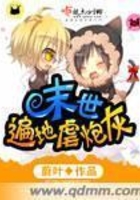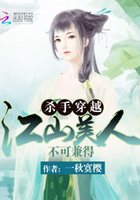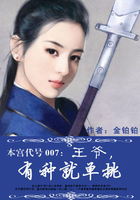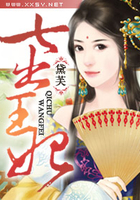现在,自我批判已经成了华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对此,华为官网是这样描述的:“自我批判的目的是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而不是自我否定。只有坚持自我批判,才能倾听、扬弃和持续超越,才能更容易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合作,实现客户、公司、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为了防止研发过程中的浪费行为,华为曾开展过一场别开生面的“反幼稚”活动。所谓“幼稚”,就是指研发人员缺乏市场化、工程化意识,在开发过程中只注重实验室性能,而忽视了技术和实验品的市场价值,没有考虑到技术和产品的推广问题。
在“颁奖大会”上,数百名研发部门的员工被点名上台“领奖”。获奖的人面红耳赤,而没有获奖的人则在下面不停地鼓噪、哄笑。原来,获奖的人并不是因为工作优异受到表彰,而是因为工作失误接受变相的批评。他们领到的奖品既不是奖金也不是证书,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产生的废品,以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的凭证。
华为不仅开展自我批判,而且也不会因为面子问题排斥外来的批评和建议。天津市通信部门在访问华为时提了一些意见,华为随后把中研部、中试部全体队员组织起来听现场录音,还安排员工写心得。之后,华为内部的《管理优化报》将心得编辑成册,分发到每一名员工手中,要求所有华为人认真学习。
有不少外国企业家在评价中国的企业时表示,中国不乏世界级的富豪,世界级的企业却很少。为什么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应该在于小农经济思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代经济体系脱胎于农业经济,人们受农业文化影响较大,不擅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也缺乏走向世界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极个别的企业家因为自身的远大追求,才带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埋头耕耘,比如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和华为的任正非等。
华为正是打破了农业文化的束缚,以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前行,最终成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标杆。
垫子文化:“吃苦”的幸福
华为在其文化体系中是如此描述其核心价值观的:公司核心价值观是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核心信念,是华为走到今天的内在动力,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共同承诺。它确保我们步调一致地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实现“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的愿景。
其中,艰苦奋斗是其核心价值观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艰苦奋斗用人们更为熟知的词汇来描述的话,就是通常所说的“垫子文化”。
“垫子文化”为外人所知,是因为一个负面事件,并非华为刻意为之。
2006年,华为一位年仅25岁的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不幸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媒体对胡新宇的情况进行了披露:
胡新宇早晨7点起床上班,晚上22点回家。住院前,胡新宇已经有病在身,但因为正在参加一个接入网硬件集成开发部的封闭研发项目,不仅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而且还要经常熬夜加班,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司打地铺。之后不久,胡新宇的病情开始恶化,并住进了医院,再没有好转。
由于网上盛传胡新宇的死和华为的“垫子文化”有关,导致这一文化成了人们叱责的罪魁祸首。
这一事件给华为带来了较为恶劣的影响,任正非为此还特意写了《天道酬勤》一文。文章介绍了“垫子文化”的由来,认为“垫子文化”是华为的精神支柱、力量之源,但并不意味着加班加点。华为虽然提倡“垫子文化”,但办公室的床垫主要是用来午休的。任正非强调:“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
在很多华为老员工的回忆性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垫子文化”的蛛丝马迹。早年,加班加点在华为的确是经常性的事情。其实,对于创业期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加班应该是一种常态。那些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企业,很难经受住创业期的考验。
创业初期,华为资金紧张,无论是办公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极不理想,很多时候都是凭借“两弹一星”这样的榜样力量来支撑的。1989年,华为搬入深圳南油深意大厦。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华为员工在办公区域的一个角落用砖头隔了几间宿舍。
那时,华为新员工刚进入公司时,都可以到总务处免费领取一床毛巾被、一张床垫。很多科研人员就住在实验室,没有假期,不分白天黑夜,都自觉地拼命工作,差不多是以办公室为家了。
华为的“垫子文化”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姑且不论“垫子文化”是否合理,仅就华为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而言,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很多单位,都有这样的文化,也都倾向于提倡这样的文化。
任正非表示,“垫子文化”记载了老一代华为人的奋斗和拼搏,是华为人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华为人虽然回避“垫子文化”的说法,但这种文化显然已经传承下来。在华为最新的文化体系中,艰苦奋斗作为“垫子文化”的另一种说法,成为华为六条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华为官网,我们能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没有任何稀缺的资源可以依赖,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与信赖。奋斗体现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任何微小活动中,以及在劳动的准备过程中为充实提高自己而做的努力。我们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使奋斗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这就是华为“垫子文化”的最新解读。
涅槃重生:烧不死的鸟是凤凰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企业的发展,华为的企业文化体系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并不是很大。仔细比较现在和以前的文化体系,我们会发现变化的主要是表述的方式,比如 “垫子文化”用“艰苦奋斗”代替了;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则被“团队合作”取代了。更为有名的“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同样没有消失,依然在华为人身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凤凰涅槃
在华为,不知道毛生江的人很少,并不是毛生江能力多强,业绩多么显赫,而是因为“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这句话就是从他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毛生江在华为的经历,不乏传奇色彩。
1992年,参加开发部08A型机项目组,后任项目组经理;
1993年5月,任开发部副经理、副总工程师;
1993年11月,任生产总部总经理;
1995年11月,调任市场部代总裁;
1996年5月,任终端事业部总经理;
1997年1月,任“华为通信”副总裁;
1998年7月,调任山东代表处代表、山东华为总经理;
2000年1月18日,任公司执行副总裁。
其中的关键点是1996年的沉浮,毛生江的市场部代总裁职务被免去,成为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当年在市场部,毛生江是孙亚芳之外的二号人物,调整幅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是一份比较奇怪的履历。在中国,除了因为年龄或意外事故会出现降职的情况,很少有人平白无故地被降职,而且还能留在原单位,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走上更高的岗位的。
让人钦佩的是,毛生江并没有因为职务变迁而沉沦,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激情。尤其是调任山东代表处代表后,毛生江不仅面临着薪酬和职位的下降,还要放下家庭,孤身出去闯荡。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都会在这样的压力前选择放弃。但毛生江选择了坚持,在面对朋友时他坦承:“说不在乎是不真实的。我想,不会有人心甘情愿去为自己制造磨难……我在乎的是华为的兴旺和发展;在乎的是一代华为人付出的青春、热血和汗水;在乎的是我能够继续为华为做些什么;在乎的是战友们的期望和嘱托。面子、位置,这些虚的东西,我真的不在乎。”
毛生江初到山东时,工作环境并不理想,市场压力很大。毛生江从刚开始的浮躁中走出来,沉下心来对办事处实施改革,同时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短短一年时间,山东办事处就取得了丰硕的回报,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回款率接近90%。由于业绩太过突出,不到两年时间,毛生江就接到了公司新的任命,于2000年年初荣归总部,成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任正非从毛生江身上发现了一种精神,并将其总结为“烧不死的鸟是凤凰”:“我认为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以永存的……在市场部集体大辞职中毛生江是受挫折最大的一个人,经历的时间也最长,但是他在这四年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有了明显的成长。”
从这时起,“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便成了华为公开的口号,曾经贴遍了华为的办公场所。
2市场部集体辞职
或许是民营企业的缘故,华为不存在国有企业通常具有的弊病。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华为坚持人才的流动性,在业绩考核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考评结果调整岗位。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员工集体辞职。
员工集体辞职在华为颇有传统,2007年华为曾组织了7000人大辞职,但因为适逢劳动法颁布,受到了舆论的指责。与之相比,1996年的市场部集体辞职更有代表性。
当时,按照活动要求,市场部员工集体辞职,下岗后重新竞聘。这次辞职非常彻底,而不是走过场,就连主管市场部的公司副总裁孙亚芳,以及市场部二号人物毛生江,都在活动中下岗了。
市场部人员在提交辞职报告的同时,还要填写一份述职报告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公司按照员工的业绩和拟定的工作计划,对其个人表现、发展潜力和发展需要作出评价,并据此决定批准辞职报告或者述职报告。如果批准的是辞职报告,意味着这名员工就要离开原有岗位,很可能会降职处理,或者离开公司;如果批准的是述职报告,则意味着员工通过了考核,可以在原岗位重新上岗,或者得到提拔重用。
一位员工在作报告时说:“如果公司批准我的述职报告,我会加倍努力,在1996年的市场大决战中作出我的贡献。如果公司批准我的辞职报告,我绝不气馁。我会调整心态,加强学习,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工作、新的挑战。”
另外一位员工说:“华为公司的目标是与国际接轨,如果我跟不上公司发展的步伐,我愿意让新人,让更有水平的人接替我的工作。”
毛生江后来总结说:“人生常常有不止一条起跑线,不会有永远的成功,也不会有永远的失败,但自己多年坚持一个准则--既然选择,就要履行责任,不管职责如何变迁,不管岗位如何变化,‘责任’两字的真正含义没变。”
很显然,华为员工既尊重了公司的安排,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像毛生江一样被降职使用的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人因此抱怨或非议。
华为正是凭借这种能上能下的文化基因,保证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和员工队伍的活力。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商,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创业激情和前进的动力。以这样的发展势头,华为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商应该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