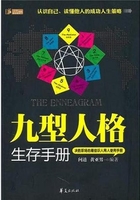黎元洪怀着一腔忧愤从宛平回到府中,第二天早饭后才给袁世凯去了一个电话,算是回复。末了竟重重地说了一句:“硕权无辜,请大总统还是收回成命吧。”
袁世凯重重地放下电话,脸色即刻阴沉下来。他感到事情真的麻烦了,他既不能收回成命,尹昌衡也不能这样死去。更令他难以招架的是那些中外记者,不断出招与他过不去。报上天天变着花样登载尹昌衡的消息,整个北京城的人都在说他袁世凯陷害忠良了。更有甚者,英国公使朱尔典居然也为尹昌衡鸣起不平来。
昨晚在六国饭店的晚宴上,朱尔典端着酒杯走上前来说道:“大总统,本人与尹昌衡将军虽然有过很多不愉快,但我十分欣赏尹将军。他性格豪放,为人刚直,军事上的才能少有人比,这样的将军难得呀!大总统……”
袁世凯没好气地打断:“这是本国的内政,公使先生还是少说为好。”
黎元洪的话仿佛又将他推到了绝壁边缘,一时竟没了主意。袁世凯是个从不轻意回头的角色,既然走到这一步了,脚下即便是火海他也要往下跳的。他在卧榻上躺下来,闭着眼睛寻思进退之策,两个使女前来为他轻轻地捏着。
袁克文郁郁走来,见父亲似睡非睡的样子,不便开口,站立一旁候着。袁世凯却发话了:“克文,有什么话就说。”
袁克文小心地道:“父亲,克文为硕权的事……”
“我知道你还是为他来的。”袁世凯打断袁克文的话,“他想以死来逼我。哼哼,他要是真的想死,就让他死好了。”
袁克文嚷道:“父亲,硕权不能死啊!”
“为什么不能死?”
“外面的舆论对父亲太不利了。”
袁世凯看了看袁克文:“不是我要他死,是他自己想死,怪得了我吗?”
袁克文急切地:“父亲,一定要想办法劝阻硕权才是啊!”
袁世凯反问道:“怎么劝阻?黎副总统亲自出面都无济于事,谁还有这个能耐?你?你有这个能耐吗?”
“我想,有一个人可能行。”
“谁呀?”
“玉楼姑娘。”
袁世凯沉默了一阵子,点了点头。
袁克文迫不及待地驱车前往朱雀胡同。进了四川会馆,竟见里面乱作一团,正房里传出女人的号哭声。罗嫂从里面慌慌张张走出,袁克文拦住一问,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自尹昌衡被判刑绝食后,本就重病着的戴爷气得几番昏死过去,要不是抢救及时,早就没命了。这天早晨,良玉楼到房中看望戴爷,饱含眼泪说她今日无论如何也要去宛平探监。戴云鹤不便阻拦,但又放心不下,就派了两个小厮用会馆的马车送她前往。未及中午,两个小厮跛脚瘸腿狼狈而回,说马车在半路被一伙强人劫走,玉楼姑娘不知去向。戴云鹤顿时脸青面黑,一口痰堵了喉咙,竟然气绝。
会馆的人都忙碌着张罗戴爷的后事,顾不得袁二公子在院子中呆呆地站着。袁克文正茫然不知所措,忽见彭光烈从外急匆匆走了来。乍见袁克文,彭光烈问道:“袁二公子怎么来了?”
袁克文道:“我是来寻玉楼姑娘的。大总统答应了,请玉楼姑娘出面去劝劝硕权兄。我想,或许只有玉楼姑娘能够办得到的了。没想这里又发生了这些事。”
彭光烈又问:“真的只有玉楼姑娘能够办到么?”
袁克文道:“黎副总统都到宛平去劝过了,不抵事。其他还有谁能说动他?唉,没想玉楼姑娘又……”
这时,罗嫂在堂屋门口嚷道:“这下好了,彭师长来了!”
彭光烈对袁克文说道:“这里的事正等着我哩,恕不奉陪了。”说着就要离去,却被袁克文一把拉住。
袁克文道:“直先兄,玉楼姑娘是怎么回事,你要给我拿个主意呀!”
彭光烈想了想,道:“除了冯敬棠,还有谁会劫走玉楼姑娘?”说完,急急地走进堂屋去了。
袁克文闷闷不乐回到府第,亲妈沈氏问起请玉楼姑娘出面的事,他便将四川会馆发生的变故说了。沈氏笑道:“这有啥难的,让陆建章派人去将玉楼姑娘抢回来不就得了。”于是,沈氏便与袁克文一起去见大总统,袁世凯果然答应了,当即打电话令陆建章火速办理。
冯敬棠自从迫于马忠和张得奎的威胁不得不将良玉楼送回四川会馆后,胸中堵着一口恶气久久未能消散。然而没隔几日,尹昌衡被袁世凯的军事法庭判刑九年的消息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冯敬棠便来了精神,感到是出出这口恶气的时候了。那天在万花楼宴请山西客商韩二爷,席间不免就聊起尹昌衡与良玉楼的话题来。这韩二爷在山西开着两座大煤矿,还做着烟土生意,是个富甲一方的豪绅。韩二爷对良玉楼心仪已久,如今尹昌衡蒙了难,便对良玉楼动起心思来。
冯四爷将这看在眼里,择机说道:“如果韩二爷真的有心于玉楼姑娘,冯某倒可以帮帮忙的。”
韩二爷闻言大喜,说他正有心将良玉楼讨回山西去做三姨太。这老财出手特大方,称只要能得到良玉楼,愿给大洋四万。接下来,冯敬棠便与韩二爷商定了交人的方法和大致时间。
当晚,冯四爷就到醉香阁与惠娘密议,要她到四川会馆探听虚实。没料嫣云偷听了他们的谈话,急欲给玉楼报个信,却又抽身不得,不禁暗暗着急。
翌日一早,惠娘带了一份礼信赶到四川会馆去见良玉楼,哭哭啼啼地将前次法源寺劫持一事全都推到冯四爷身上。又说与玉楼母女一场,尹都督出事后,日夜都为玉楼担惊受怕,所以前来探望。
良玉楼心软,竟也信了,含泪道:“不管尹将军怎么样,我都是他的人,死活都是他的人了。”接下来,无意间透露出她明日要到宛平监狱探视尹昌衡的打算。惠娘听了暗喜,离开会馆就直奔盈春堂向冯四爷报了。第二天一早,良玉楼乘上马车往宛平方向驶去。没想出城不多远,丛林中闯出一伙强人来,将玉楼连人带车劫走了。
冯敬棠和惠娘得了四万大洋,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正得意时,盈春堂和醉香阁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冯敬棠先自一惊,很快冷静下来,笑容可掬地将陆建章迎进堂内,说道:“哎哟,陆统领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陆建章道:“冯四爷这么聪明的人,陆某人的来意你不会不晓得吧?”
冯敬棠即道:“陆统领,自从上回私藏烟土事发被抓进大牢,我就再也不敢涉足那门生意了。陆统领要是不信,可以尽管搜查,要是从我家里搜出一两烟土,我冯敬棠哪怕倾家荡产、坐牢砍头也甘愿。”
陆建章喝道:“今日我不管你烟土的事,你派人劫持了玉楼姑娘,她人在哪里,你把她交出来。否则……”
冯敬棠闻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道:“陆统领,只怕你是冤枉好人了!我为啥要去劫持玉楼姑娘呀?玉楼姑娘不是早被尹都督赎去做姨太太了吗,怎么会被人劫持了?这是哪里的强盗这样歹毒,干下伤天害理之事却赖到我冯敬棠头上来了……”
见冯四爷又哭又闹矢口否认,陆建章便叫人将他绑了,一顿马鞭狠揍,而冯敬棠哭天呼地,就是不认账。陆建章反倒纳闷起来,难道这事儿真不是他干的?
醉香阁那边,吴七带人搜遍整个院落不见良玉楼的踪影,而鸨妈惠娘更是伶牙俐齿一问三不知。吴七正拿她没法子,忽见屋角处有个姑娘在向他使眼色,是他侍卫尹昌衡时认得的嫣云姑娘。嫣云将吴七悄悄带到僻静处,就将冯四爷和惠娘劫持玉楼姐卖给山西老财韩二爷的事说了。吴七当即撇下惠娘,赶往盈春堂向陆建章报告。
韩二爷顺利得到良玉楼,高兴得不得了,当即用他带进京来的豪华马车将良玉楼载了,随从保镖左右护卫,走官道直回山西。路途颠簸,行进速度甚慢,薄暮时分方才走进涿州境界。韩二爷吩咐不能让玉楼姑娘太累了,就在前面寻个上好的客栈住下。就在这时,忽然后面腾起漫天尘雾,就见一队骑兵快速驰来,将韩二爷车队团团围住。
韩二爷惊慌道:“我是山西韩二爷,你们要做啥?”
带队的吴七并不答话,跳下马来,撩起车帘一看,果见良玉楼捆着双手坐在车内,便高兴地嚷道:“玉楼姑娘,我们救你来了!”
韩二爷势单力薄,哪敢跟这些横枪跃马的警卫兵们较劲,只得眼睁睁看着良玉楼被吴七一行人救了回去。
陆建章救出良玉楼,当夜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冯敬棠那里将四万赃银讨了来。冯敬棠偷鸡不着蚀把米,却闹不清他与韩二爷的交易是如何走漏了风声的。正纳闷着,惠娘领着虹儿急急走了来。原来嫣云向吴七透信时,没想被虹儿看在眼里。冯四爷暴跳如雷,顿起杀心,命八哥将嫣云从醉香阁捆了来。可怜如花似玉的嫣云,只为与良玉楼的一份姊妹情义,竟被吊在盈春堂后院大树上活活打死了。
监室里死一样的沉寂,形容枯槁的尹昌衡静静地等待着死的到来。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忆了,偶尔感觉到的声响证实着他尚且存在的生命。监室门又吱呀一声开了,隐隐响起轻微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慢慢地向床前靠拢。他于冥冥中感觉到有人在床沿坐了下来,抓住他的手抽泣着。这抽泣声渐渐清晰,令他的灵魂一阵震颤。如此温馨的手手相触的感觉,多么熟悉的哭泣,竟在幽冥之中出现了?
“昌衡,昌衡……”床边的人哭着唤道。
尹昌衡无力地撑开眼来,他看到了一个模糊却熟悉的身影。
“昌衡……”良玉楼伏在尹昌衡身上痛哭起来。
尹昌衡慢慢抬起手来,抹着玉楼脸上的泪水:“你怎么来了?”
良玉楼盯着须发蓬乱的尹昌衡说不出话来。
尹昌衡喘息着道:“原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这下好了,我可以放心地死了……”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良玉楼哭嚷着。
“玉楼,别伤心。”尹昌衡轻轻抚摸着良玉楼的脸,“你没见我那诗里的话?我是决计不话了。我知道,袁大总统才不愿我死呢,可是我偏要死给他看看。玉楼,有些事你是不会明白的,但今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死……”
良玉楼在床前跪了下来,哭道:“昌衡,你不能死,我不让你死……”说着,端起水杯要喂尹昌衡,被他轻轻挡开了。
“玉楼,是袁世凯让你来劝我别死的吧?”尹昌衡问。
“袁世凯不让我来,我来得了吗?”良玉楼啜泣着说道,“昌衡,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生死磨难才见到你的啊……”
良玉楼泣述着她是怎样从天津连夜赶回北京,戴云鹤夫妇将她当女儿收留下来;骆爷、戴爷和彭师长是怎样冒着危险千方百计为他鸣冤叫屈,要营救他出狱的;冯敬堂和惠娘又是怎样先后两次将她劫持,几乎置她于死地的……
尹昌衡一动不动地静听着,眼角渗出泪来。
“戴爷昨天死了。”良玉楼说,“临来宛平时,袁二公子对我说的。”
“啊,戴爷死了,怎么就死了……”尹昌衡喃喃着说。
良玉楼又道:“袁二公子说,他知道你受冤屈了。要我一定劝劝你,要爱护好自己的身子,千万不要想到死。”
尹昌衡指头动了动,触摸着玉楼的脸:“我的身子已无所谓了,生死也无所谓了。”
良玉楼又痛哭起来:“昌衡,你不能这样。为了我,你也不能死呀……”
尹昌衡叹息着道:“玉楼,有些事,你是不会明白的,我别无选择。人生如白驹过隙,迟死早死都是死。我这时候死去,在袁世凯的监狱中死去,我反而觉得值。”说罢他垂下手去,不再说话,似乎在静候着死神的到来。
良玉楼绝望了。她深知尹昌衡死意已决,便揩了揩眼泪,在他耳边轻轻说道:“昌衡,既然如此,我就陪着你。我原说过,生生死死都跟着你了。你死我也死,谁叫我们是夫妻呢。”说罢,她在他身边躺了下来,静静地,偶尔轻轻抽泣几声。尹昌衡身子一颤,却没更多的反应。
良玉楼竟然陪着尹昌衡不吃不喝,杨进忠惊恐万状。
监室里沉寂下来,偶尔一只苍蝇嗡嗡飞过。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监室的门开了,狱警端着饭菜进来。
“太太,该吃午饭了。”狱警小声说。
良玉楼仍静静地躺着。狱警又小声地唤了两次,良玉楼依然如故。狱警无奈,将饭菜放在桌上退了出去。
杨进忠在铁栅门外面候着,问:“怎么样了?”
狱警回道:“太太躺着,没吃饭的意思。”
“没关系,也许是太伤心了,吃不下。”杨进忠说着离去了。没料晚上还是如此,送去的饭菜依然未动,良玉楼搂着尹昌衡静静地躺着,像在沉睡中。
杨进忠开始着急了,忙打电话向陆建章报告。
“好啊好啊,玉楼姑娘要是能吃下饭,那才糟了!”陆建章却高兴起来,没想到玉楼姑娘会来这一手,说不定尹昌衡很快就会放弃绝食的。杨进忠也觉有理,就不再理会监室中的情况。这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情况照旧,又一个夜很快来临。二更时分,杨进忠踮着脚来到尹昌衡监室外,趴在窗口探听里面的动静。突然,一丝儿很轻很轻的话语声隐隐约约传了出来。杨进忠兴奋地笑了,遛回房间放心地睡去。
惨白的月光透进监室,屋子里弥漫着幽冥地界的朦胧感觉。躺着饿了两天,良玉楼只觉浑身麻木,躯壳也显得轻飘起来。身边的昌衡仍丝毫不动地睡着,呼吸越来越弱,他没两天活的了。良玉楼突然想说话了,她猛然间觉得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心爱的夫君述说,不管他听没听,也不管他应不应,她要对他说出来。
她说了她儿时的故事。她从小聪明伶俐,爸爸把她视若掌上明珠。爸爸曾经说过,等她长大了要把她送到城里的洋学堂去读书,没想庚子年闹洋匪,庄子烧了,爸爸和全村的人都死了。她说她仰慕尹都督,但她从没奢望过成为尹都督的太太。她说他在天津被捕后,她天天都在想,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她也决不会活下去了。她说那天她到宛平来探监,半路上被冯敬堂的人劫持,被四万大洋卖给了山西老财韩二爷。路上她就想定了,一有机会她就寻死,做鬼也要跟着昌衡去。她还说,现在可好了,可以与心爱的人死在一起了,多幸福。她还说,她最觉遗憾的是她已是尹家的媳妇了,却没能为公婆尽上一点孝道。但她又说,要是公婆晓得儿媳是陪着昌衡走上黄泉路的,他们一定会原谅她,会说她是个好媳妇的。末了,她从贴胸处掏出那枚红心石来,放在尹昌衡手中握着。她说自从天津一别,这枚红心石就像昌衡的心一样伴着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她给他唱曲儿,将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吟唱。她唱了李清照的《点绛唇》: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栏杆,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她唱了王翰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她唱了他写给她的《赠良玉楼》:
枇杷门巷玉人家,粉黛纷纭斗烛花。
阅尽群芳皆白眼,乍惊孤艳拂红牙。
鸳鸯独宿香衾冷,翡翠双拖舞袖斜。
我欲自为仙子婿,一生长与饭胡麻。
良玉楼唱了一曲又一曲,歌声清丽而悠扬,在尹昌衡的耳边萦回。远处传来几声鸡啼,院子里响起值夜狱警训斥犯人的骂声。良玉楼不唱了,也不说了,强撑着起身下床,面对窗棂呆呆地站了很久。她回头望了尹昌衡最后一眼,掏出一条丝带来,在窗棂上拴牢。
就在这时,身后猛地响起尹昌衡微弱的声音:“玉楼,你过来。”
良玉楼吃惊地转过身去,顿见尹昌衡艰难地挣扎着要坐起来,她哭叫一声“昌衡”,扑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