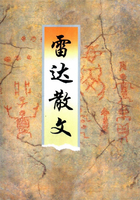戴云鹤回到会馆,当晚就被气得病倒了。他想不到竟然在醉香阁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却又对惠娘及冯敬棠毫无办法。他后悔莫及,真不该到那种地方去。他太天真了,骆成骧也太天真了,还想去给惠娘和冯敬棠提个醒,让他们不要为难玉楼姑娘哩!这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反将自己的老脸几乎丢尽。
夫人熬了参汤让戴爷喝了。邹稷光前来探视,问道:“姑父白天都好好的,怎么晚上就病倒了?”
戴爷闭眼不答。夫人道:“今天出去着了凉,回来人就不舒服。”
邹稷光道:“姑父上了点年纪,出门去一定要多带件衣服。北京这地方,天气多变,稍不小心,人就容易着凉的。”
戴云鹤咳了声,并不说话,侧向床里睡去。邹稷光自觉无趣,说了几句关切的话就退了出来。就见车夫张老三从车房走出,唤住他问:“老三,戴爷今天是怎么了?”
张老三道:“今天戴爷去八大胡同了,可能是为玉楼姑娘的事到醉香阁走了一趟。他进去也就一袋烟工夫,出来时就见他脸色都变了,一路上啥都没说,只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邹稷光便知是怎么回事,料想戴爷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他出卖了良玉楼,于是放心地回到房间,钻进被窝里睡去。这一夜他做了个春梦,梦见他与玉楼姑娘好了,良玉楼半推半就,正当要成就一段美事时,他却突然醒了。这时天已大亮,邹稷光失意地爬下床来,到厨房随便吃了点东西,无所事事,便径直往天桥去会暴眼龙大。
这天风蝶儿开早场唱《凤仪亭》,暴眼龙大和两三个弟兄早早地就在书场中坐着了。邹稷光寻来时,风蝶儿正唱到吕布、貂蝉调情被董卓发现的节骨眼儿,见龙大色迷迷地将风蝶儿盯着,便没敢惊扰,在他身后坐了。临完时,龙大才发现邹稷光。
“啥时来了,也不吭一声?”
“来一阵了,见龙哥看风蝶儿入了迷,没敢坏了你的雅兴。”
便有一弟兄道:“邹哥,都晓得你发了笔财,中午请弟兄们喝一杯如何?”
邹稷光笑道:“小意思。”
散场后,龙大邀上风蝶儿,与邹稷光和弟兄们就在附近小酒楼里坐了。风蝶儿虽为男艺人,但举手投足、眉眼言语都具十足的女人味,加之脸蛋生得俊秀,便引得众多男人亲近。自从暴眼龙大盯上风蝶儿后,那些男人也就敬而远之了。龙大成了风蝶儿的保护神,风蝶儿也乐得有这个地头蛇做靠山,对龙大也就格外顺着。
邹稷光自言他请客,招呼风蝶儿给龙大敬了三杯酒,自己也向龙大和风蝶儿双双敬了。龙大便问道:“良玉楼被冯四爷劫回了醉香阁,这些天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邹稷光道:“昨天戴爷到八大胡同走了一趟,可能就是为玉楼姑娘的事。
回到会馆后见他神色不好,估计没什么结果。”他没说戴爷病倒的事。
龙大笑了笑:“今非昔比了,他还能将良玉楼劫回去?”
便有弟兄笑道:“如今良玉楼回了醉香阁,也不是什么都督太太了,龙哥正好去会会这个京都名妓,过把瘾嘛!”
龙大挠着下巴,得意地笑着,没说话。邹稷光心里怪不是滋味,他想起了早上的那个梦,便愈加沮丧起来。他抬眼看了看龙大,见他仍在挠着下巴想心事,便道:“龙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要是真的想会会玉楼姑娘,你去醉香阁走一走不就得了。”
龙大心里痒痒的,笑道:“我是该去会会玉楼姑娘了。如今她又堕入风尘,不比都督太太了,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的。我倒要去试试这女人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能叫尹昌衡这个大人物也把她爱得死去活来的。”
喝到午后两点,风蝶儿下午还有场《珍珠衫》,提前去了。邹稷光便陪着暴眼龙大和弟兄们继续喝下去,直喝得天昏地暗,七歪八倒,他还叫拿酒。龙大打住了,说:“要喝你们喝,我要走了。”
邹稷光道:“龙哥怎走得?你一走,弟兄们就没兴致了。”
暴眼龙大诡谲地笑着:“今晚我就想去会会玉楼姑娘。你把我灌醉了,我怎么去得了八大胡同?”
邹稷光忙笑道:“啊哟,龙哥真是个急性子。既是这样,我们都散了吧。”
于是邹稷光掏钱结账,而后自回四川会馆。这一夜邹稷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揣测着暴眼龙大是否真有本事得到良玉楼。良玉楼是个烈女子,他已为她吃了一顿皮肉之苦,三天起不了床。他就不信,龙大今晚就真能得手!
第二天,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邹稷光再到天桥去会暴眼龙大。来到龙大家,却见大门紧紧闭着。他敲了两下,门开了。邹稷光问:“怎么把门闭着?龙哥呢?”
开门的弟兄说:“龙哥伤着了,躺在床上哩!”
邹稷光急忙走进龙大的屋子,就见好几个弟兄围在床前,龙大趴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邹稷光吃了一惊,问:“昨天还好好的,怎么就成这样了?”
便有弟兄说道:“龙哥昨晚到醉香阁会良玉楼,被人打伤了。”
又有弟兄嚷着:“是哪个混蛋王八吃了豹子胆,敢跟龙哥作对?弟兄们,有种的跟我走,咱们这就去砸了醉香阁那家臭窑子!”赖皮们便嚷嚷了起来,有的便要操家伙。
“都不准动!”龙大吼道,弟兄们不吭声了。
邹稷光在床边坐下,问:“龙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暴眼龙大:“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背上就挨了一块石头,被打蒙了。”
邹稷光问:“是哪个敢打龙哥?他不想活了!”沉吟片刻又道,“这事一定与鸨儿惠娘有关,你怎么不跟她讨个说法?”
龙大道:“那婆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私下琢磨,这事儿可不寻常啊,如今的良玉楼,不是随便就碰得的女人了。”
邹稷光听龙大如此说,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话说昨天下午回到家里,暴眼龙大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人也就清醒了许多。天近黄昏,他换了一身亮色的衣服,叫了辆马车,体体面面地来到八大胡同。进了醉香阁,就有三四个姑娘围了上来,龙大一笑,说:“我先要见见鸨母,再跟你们玩。”
惠娘走了来,笑道:“哟,这位爷怎么称呼啊?”
龙大一看便知是鸨儿,道:“我是天桥的龙大,不知鸨妈听说过没有?”
惠娘咋会不晓得天桥的暴眼龙大呢?她审视着龙大那对鼓鼓的眼睛,奉承道:“哎哟,北京城有不晓得八大胡同醉香阁的,可没有不晓得天桥的龙大龙爷的啊!”
龙大听了惠娘的吹捧,便得意地笑了,说:“鸨妈,醉香阁名气大着哩!
如今不止是北京城,恐怕天下人都没有不晓得八大胡同醉香阁的了!”
惠娘一愣,说:“龙爷这话就说得玄乎了,我小小醉香阁哪来这么大的名气?”
龙大低声道:“就因为出了个良玉楼,醉香阁真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惠娘笑笑:“哎,别只顾说话了,龙爷难得来,快进去坐坐。我这里的姑娘可称心了,龙爷你尽管玩高兴。”
到内院客堂坐定,惠娘笑问龙大:“龙爷,你可是贵客了。我猜你一定是瞧上我们这儿的哪位姑娘了,是吗?”
龙大当即答道:“我要会会玉楼姑娘。”
惠娘脸色沉了下来。她从冯敬棠口中得知,向四爷提供良玉楼行踪的人就是天桥的暴眼龙大,这家伙为此敲了冯四爷和她五百大洋,没想今天他就奔着良玉楼来了。惠娘装作不知情,叹息道:“哎哟龙爷,你难道不晓得玉楼姑娘早就被尹都督赎走,做姨太太了么?”
龙大不高兴了,暴眼鼓得像胡桃,说:“鸨妈在蒙我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
惠娘又笑道:“哪敢呀!我也对龙爷实说了吧。玉楼姑娘是回来了,但她这人呀,给尹昌衡做了几天少奶奶就正经起来了,要让她重操旧业当姑娘,那可比登天还难哪!”
龙大拉大了嗓门说道:“没这么怪的事!是鸨妈不让我会她吧,瞧不起我?”说着掏出二十块大洋放在桌上。
惠娘把大洋推回到龙大面前:“不是我不让,真的是玉楼姑娘不会客,我拿她没办法呀!”
暴眼龙大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嚷道:“今天我偏要会她,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
惠娘晓得拗不过龙大,只好说:“好吧,龙爷实在要会玉楼姑娘,我也不硬拦着你。要是你能劝得玉楼姑娘回心转意,我还会重重谢你的。只是,龙爷可要耐着点性子啊,千万不要伤了玉楼姑娘。”
冯四爷和惠娘把良玉楼劫了回来,一则此前被尹昌衡、陆建章和吴炳湘这些人骗了,咽不下这口气;二则确也看准了良玉楼这个京都名妓因尹昌衡这么一折腾,不消说名气定会大增,如若重返风尘,岂不红透北京城?良玉楼可是一棵摇钱树啊!岂料回到醉香阁后,玉楼三天不吃不喝,躺在玉人轩里默默流泪,任冯四爷和惠娘威逼利诱,决然不走回头路。便有前清的一位贝勒爷带着大把的银票慕名而来,坚称要会玉楼姑娘,惠娘就让他去试试。良玉楼闭门相拒。贝勒爷急了,撞开了房门,便要强行与玉楼行欢。谁知良玉楼早准备了一把剪刀在枕下,没等贝勒爷近前,就将剪刀抓在手中,对着自己的咽喉。贝勒爷慌了,只得作罢。
惠娘见玉楼这般性烈,只得悠着点来,企望能慢慢让她回心转意。
嫣云悄悄来到玉人轩看望,二人伤心地哭作一团。哭罢,良玉楼发狠道:
“我是决不会再走这条道了。他们要是把我逼狠了,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嫣云急了,说:“玉楼姐,你决不能想到死。尹都督只要还活着,你肯定就有希望的。”
良玉楼又泪眼模糊起来。尹昌衡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盼头,尽管这盼头十分渺茫,她也决不放弃。昨晚,她正苦苦思念着尹昌衡,惠娘便领着暴眼龙大走了进来。
惠娘脸上堆着笑,说:“玉楼姑娘,这位是天桥的龙爷,在北京城可是出了名的龙头老大。今天龙爷是慕名而来,特意来看望你的。”就有小厮送来茶点水果。惠娘随即离去,并将通往后院的门道锁了,派了两个小厮把守着。
龙大一见良玉楼,两只本就暴突的眼球仿佛就要跳出眼窝来。良玉楼也认出暴眼龙大来,料想这夜难逃劫难,便狠下心来要与龙大拼个你死我活。她到床头坐下,伸手抓住枕下那把剪刀。
龙大眼尖,察觉到良玉楼这个细微的动作,便做出轻松愉快的样子离得远远地坐下,长叹一声说道:“玉楼姑娘,你也许不知,我对尹都督是十分敬佩的。尹都督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尹都督与玉楼姑娘是英雄配美女,天造的一对夫妻啊!”
说到这里,龙大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愤愤地骂起袁世凯来:
“袁大总统他是有眼无珠,他凭啥把尹都督关进大牢?尹都督是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啊……”暴眼龙大说着说着就向良玉楼走近,没料玉楼陡然站起,手中的剪刀直指龙大。
“你出去!马上出去!”良玉楼喝道。
暴眼龙大突然朝良玉楼跪下,带着哭腔说道:“玉楼姑娘,求你别这样了!我今天来会姑娘,决无歹意,只是想陪玉楼姑娘说说话而已。那次在天桥,我龙大是有眼无珠,得罪玉楼姑娘和尹都督了,至今我都后悔莫及。如今尹都督蒙难,我龙大要是能为都督做点事,为玉楼姑娘分点忧,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啊……”
没料龙大会来这一手,良玉楼紧握剪刀的手也就微微垂了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龙大猛地跃起,夺过剪刀,将玉楼紧紧搂在怀里。
“我的大美人,龙爷想你好久了!今天乖乖地伺候伺候龙爷,龙爷一定会重重赏你的!”龙大任由良玉楼挣扎叫嚷,稍一用力将她抱起,重重扔在床上。
良玉楼奋力挣扎,怎奈这厮甚是凶蛮,脱身不得。她绝望了,愤怒地尖叫起来:“龙大,我死了变鬼也饶不了你……”就在这时候,忽听龙大哎哟一声惨叫,便歪倒在床上不动了。
良玉楼惊骇不已,穿上衣服冲了出去。通向内院的门道锁着,她声嘶力竭嚷叫起来。门开了,惠娘气呼呼走进玉人轩,但见龙大昏倒在床,便吓着了,生怕酿出人命来,就将龙大狠狠地摇着。
暴眼龙大呻吟一声翻身坐起。
惠娘问道:“龙爷,你这是怎么了?”
龙大仍在迷糊中,晃了晃脑袋说:“老子也不晓得是怎么了!”突然,他看见床边的一块石头,便依稀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来。他将石头拿在手中,盯着良玉楼,又转眼盯着惠娘,问道:“是谁干的?”
惠娘忙说:“我离去时将通往前面的门道都上锁了,这后院里只有龙爷和玉楼姑娘,除了她,还有谁能砸你石头?”
暴眼龙大便直盯着良玉楼,想了又想,便觉不对。刚才他将良玉楼死死地压在下面,她怎能出手砸伤他呢?这里肯定还有第三者。龙大呻吟着在屋里转了一圈,又走出门去,将夜色中的后院细细地审视了一番,未见任何异常。这厮顿觉毛骨悚然起来,也不再追究下去,一瘸一拐地走出醉香阁,叫了辆马车自回家去。
龙大回到家里,背上越发痛了起来,脱掉衣服一看,背心处乌黑一大片。
他没法平躺着睡觉,在床上趴了一夜。
翌日,他的弟兄一早就来到家中,想听他说说与良玉楼寻欢的故事,没想他们的龙头老大竟是如此的狼狈不堪,便都傻了眼。
“邹兄,你说这究竟是谁干的?”暴眼龙大说完昨夜的遭遇,愤愤地问邹稷光。
邹稷光直晃脑袋,说:“在那种情况下,良玉楼是不可能用石头砸你的,醉香阁的人也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妈的,这事也太蹊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