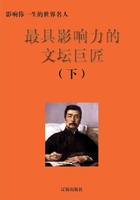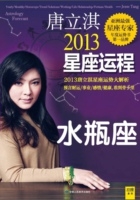他强调,源客家之所以变成有自觉意识的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和畲族的战争。这种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后期扩张时,客家人在两广地区又和不同的“本地人”产生冲突的结果。(Cohen 1996[1962])拒绝接受把异族通婚作为一个客家文化发展主要因素使许多研究者陷入矛盾境地。畲族妇女同很多中国南方妇女和东南亚山地妇女一样,担任大量的农间劳作,她们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有效高产的农业知识。所以,如果没有异族通婚,源客家人是很难获得和学习这些主要生活技能的。
畲族男人经常投入政治和战争,同时妇女负担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畲族妇女和男人一样,对土地有平等的拥有权。和畲族妇女的异族通婚将使土地的使用权自动地(在畲族人的眼中)给予汉族丈夫和他们的子女(汉和畲通婚生育的子女在户籍上从属于汉族父亲)。
不断的地区战争已经证明源客家人迁入畲族地域的事实。客家的先锋力量大量包括男人,数目远远超过妇女。和畲族的战争又使更多的男人进入该地区,这是由于政府需要派遣军队来控制暴力战争的扩散。1517~1518年的一项军事活动“不仅恢复了几十年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同时也加速了畲族的汉化”。而类似的活动在此后一直继续(Leong 1997: 35)。由战士转变而来的移民者和当地的源客家男人担任着边界守卫的职责,他们很难找到妻子。
对于这种不平衡,和畲族妇女的婚姻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但是也可能是导致畲族仇恨和暴力的直接原因。源客家男人和畲族妇女异族通婚的假设给我们所了解的客家历史补充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缺失要素。通过和畲族妇女的婚姻,移民者获得了妻子、土地和姻亲,而这种姻亲关系使永久的和平得以实现。
畲族人从这个交易中能得到什么呢?对于畲族男人来说,一个负面影响结果是适合的婚姻对象的急剧减少。而从肯定的方面来看,他们获得和平,更多汉族商品物资,文化教育机会,也有可能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联合感,他们开始和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心结合。畲族妇女的得失比较复杂,消极地说,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她们失去了配偶间共有的理解。这一点对于重视浪漫的年轻文化,可能是一个重要失去。与在她们本社会群体中结婚相比,和汉族男人结婚的畲族妇女也可能会失去更多的自治权。虽然她们并没有失去自己和儿子土地所有权,但是最终,在中国法律下,她们的女儿失去了这种权力。如果她们的移民丈夫还担任边界守卫的职责,或者是矿工、猎人和樵夫,那她们的农业劳动生活并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就如她们的母亲所做的一样,她们种田、养育家庭,却不能从她们的丈夫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那么,这样的婚姻到底给畲族妇女带来什么好处?好处并不明显。从汉族观点来看,这样的婚姻给女人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高。很难假设妇女本身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也不同意把讨论的基础建立在大汉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如果要证明妇女有婚姻自主权,我们必须寻找到更强有力的证据。我猜测这些移民者能够得到妻子的部分原因在于,来自中央帝国的服务人员补充了自愿的民间移民者。比如,一个边境战士在国家等级中的地位很低,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和他的同事是在“公”的范围中。他们代表了庞大的(部分是想像的)大汉族关系网。
客家刻板印象的诠释虽然不是完全真实或者具有历史精确性,现在存在的刻板印象仍然能帮助我们明白某些有用的信息。它们使我们注意到一些被夸大或者误解了的各方面事实,很少有完全的捏造。
在明朝晚期大量离开客乡的条件下,客家的经验和个性是如何固定为刻板印象的?Nicole Constable在她的一本关于客家身份的书中,有一篇发人深思的介绍。她列举了一些过分综合但相当重要的形象,“不辞辛劳的客家妇女,政治上的爱国主义(集团内)的合作,以及农业或者劳动阶级的职业”,节俭和共同的历史(1996: 6,33)。她还总结了Sharon Carstens对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性格描写:“经济上的保守谨慎,平等观,独特的性别角色”(1996: 19)。Howard Martin介绍了台湾客家传统主义者强调客家忠诚和团结的论点。
客家刻板印象的另一个方面尤其惊人:客家主张自己的汉族文化“纯正性”,而非客家人则认为他们并不属于汉族文化。Constable提醒我们,“在某些地区”,客家人并不被视为纯粹的中国人(1996: 15),较早期西汉学家曾经坚持这个观点。而恰恰相反的是,客家人和他们的南方邻居相比,视自己为更纯正的中国人,而认为“广东人和闽南人是原住土著人的后代”(Blake 1981: 5)。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四川特别重要的刻板印象:贫穷、低下的地位;非常高或者非常低的汉血统(“纯正性”);客家男人的美德、政治忠诚;以及客家女人的耐劳苦干。如果我们把客家族群置于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这些刻板印象就更具有特别意义。
我在一本书中对此做了详细的探究(Gates: 1992, 1996);这里我只想概括地说,让我们把客家置于一个生产的双重形式,而在此双重形式中,商品生产和国家服务辩证地结合起来。
二元性普遍适用于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和人的分析。这些二分法,主要集中在两个系统(它们都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以及它们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其中之一,所有前工业的农业帝国都司空见惯的,可以被称之为“贡赋式的生产方式”。社会生存资源由农民和工匠生产制造,他们通过自己家庭的劳动和所有物自给自足。剩余物质以税的形式上缴给统治阶级,满足统治阶级生存的更高生活水平,并且提供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持功能。贡赋式的生产方式的不平等性在自然等级的意识形态中被看作正当,这种等级不仅根据主要的阶级分等(如生产者和管理者),还包括在姻亲群体内部的辈分、年龄和性别。
中国贡赋的统治阶级允许生产者家庭的市场交换,甚至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物品。在宋朝期间,中国发展了密集的私有市场网络。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物质在私人手中积累。在中国,社会剩余物资不仅产生了学者——官僚阶级,也创造了更高强度的劳动生产,以及充分发展的高等文明。中国统治阶级管理市场并因此保持统治力量,相当重要的部分是依靠血亲关系的形态和管理本身。由于受到贡赋政治经济、法律和市场预先设置的价值观念的限制,我把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生产者市场网络系统称之为“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存在长期从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贡赋式的生产方式。对此方式做极大贡献的生产阶级,发展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民间形式,和官方价值体系在重要细节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在明朝,客家人族群从在福建西南的孵育地向外扩散时,能适应这个理论模式吗?他们本身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给了我们答案的线索。贫穷和卑下的地位暗示了在生产阶级中的低地位;北方汉族人的起源和文化的“纯正性”暗示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依附;知识和军事威力,群体团结和政治忠诚要求他们在帝国中作为汉人的各种权利;妇女辛勤的劳作(与客家男人和非客家的汉族妇女相比)强调了一个完全的性别等级。客家人的自我肖像是,多产的、地位低下但可敬光荣、对权威服从、持久的、“最中国的中国人”。
客家人的本地邻居普遍持有的刻板印象与客家相反,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阐明客家人的刻板印象。从本地邻居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新佃户,客家人具有北方中国农民的标准印象:太老实而缺乏企业家头脑,因此只能固守贫穷;由于商业智慧的缺乏,在他们和其他人的交易中被迫使用暴力;对贡赋价值体系太过坚持而丧失了改善的机会;在品味上的粗糙体现在接受天足新娘;并且,相当可能的是,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这个相反印象揭示了许多我们所知的关于两广本地人的事实。这个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粮食仓库,在其最好的种植基地上,经历了商品化的膨胀和收缩(Marks 1998)。
这些人的当地文化(连同那些福建沿海和长江下游的人)是中国小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虽然受贡赋结构和价值较为宽松限制,小资本主义兴旺繁荣,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地人觉得客家人并不能在他们建造的商品世界中游刃;客家人保护自己的方式,是通过强调贡赋美德,比如政治忠诚,正直诚实和勤劳工作。因为,从意识形态上,在“天下”的世界里,贡赋稳定性的地位高于小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灵活性,客家人可以骄傲地声称他们自己汉族血统的纯正性,并且认为本地人被私有和当地利益所腐败。
在中国两个彼此交织的生产方式中构建客家经验可以帮助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客家人从以前直到现在,一直称呼他们自己为“客家——做客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解释和选择,客家人在他们生活了一千年的移民地区一直保留着“客人”的身份。代代相传,他们选择了用一个词来称呼自己,那就是,“客家”,来强调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原来起源于管理,但现在成为一个族群的标志。批判或者忽视他们对畲族的早期借用,以及有可能在稍晚时对本地人的借用,他们更着重于和伟大中国贡赋系统世界的联系。这个世界使得当地关系次要于一个抽象的文化身份。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曾祖母们的贡献看起来太狭小而不重要。但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理解了中国妇女的劳动贡献,才能明白中国历史。
说明:本文选自作者参加2001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作者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