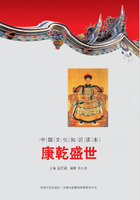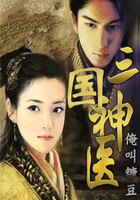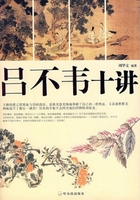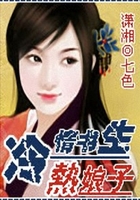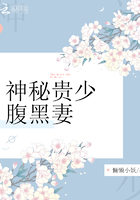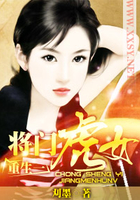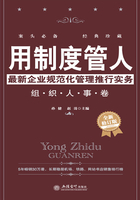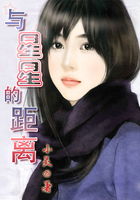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孝文帝既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也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无论男女一律改穿汉族衣服。后来又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公元496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变鲜卑贵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能执行。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5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门望族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矛盾,而且还使二者血统实现了融合;同时也支持了北魏封建政权的统治,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受冯太后影响,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变了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故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得非常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得以兴盛。
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先进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10、祖冲之与圆周率
南朝从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夺取帝位,建立宋政权开始,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祖冲之是南朝人,出生在宋,去世的时候已经是齐了。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官员。祖冲之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做了详细记录。
南朝宋的孝武帝听说他的情况后,就派他去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原本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于是他欣然前往。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这部历法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但是,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于是,宋孝武帝就帮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但也被祖冲之一个个驳倒了。但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去世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在研究科学。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给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还又编写了一本《缀术》。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求得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祖冲之在长期的艰苦研究后,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按照刘徽的割圆方法,设了一个直径为一丈的圆,在圆内切割计算。当他一直切割到圆的内接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最后求得直径为一丈的圆,它的圆周长度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之间,这些长度单位我们现在已不再通用,但换句话说:如果圆的直径为1,那么圆周小了3.1415927。
要做出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一琐极为细致而艰巨的脑力劳动。因为在祖冲之那个时代,算盘还未出现,人们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叫算筹,它是一根根几寸长的方形或扁形的小棍子,由竹、木、铁、玉等各种材料制成。通过对算筹的不同摆法,来表示各种数目,叫做筹算法。如果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摆放的面积就越大。用算筹计算不像用笔,笔算可以留在纸上,而筹算每计算完一次就得重新摆放以进行新的计算;所以只能用笔记下计算结果,而无法得到较为直观的图形与算式。因此只要一有差错,比如算筹被碰偏了或者计算中出现了错误,就只能从头开始。要求得祖冲之圆周率的数值,就需要对九位有效数字的小数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等十多个步骤的计算,而每个步骤都要反复进行十几次。今天,即使用算盘和纸笔来完成这些计算,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时期,当一位中年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手中不停地算呀、记呀,还要经常地重新摆放数以万计的算筹,这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状态,如果一个人没有极人的毅力,是绝。对完不成这项工作的。
“祖率”这一光辉成就,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祖冲之,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同时也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的推崇。1960年,苏联科学家们在研究了月球背面的照片以后,用世界上一些最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那上面的山谷,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
祖冲之在圆周率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适应了当时生产实践的需要。比如他亲自研究度量衡,并用最新的圆周率成果修正了古代的量器容积的计算。
古代有一种量器叫做“釜”,一般的是一尺深,外形呈圆柱状,那这种量器的容积有多大呢?要想求出这个数值,就要用到圆周率。祖冲之利用他的研究,求出了精确的数值。他还重新计算了汉朝刘歆所造的“律嘉量”(另一种量器,与上面提到的都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用的“升”等量器,但它们都是圆柱体。),由于刘歆所用的计算方法和圆周率数值都不够准确,所以他所得到的容积值与实际数值有出入。祖冲之找到他的错误所在,利用“祖率”校正了数值,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还造过“千里船”,并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chōnɡ)米碾谷子,叫做“水碓(duì)磨”。
祖冲之死后,他的儿子祖(gèng)、孙儿祖皓都继承了祖冲之的事业,刻苦研究数学和历法。据说祖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全神贯注,连天上打响雷也听不到。他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有一次,他在路上走,前面来了个大官徐勉。祖根本没有发觉,一头就撞在徐勉身上。等到徐勉招呼他,祖才像从梦中惊醒一样,慌忙答礼。徐勉知道他研究出了神,也没有责怪他。后来祖刻苦钻研,终于找到了计算圆球体积的正确计算方法。他求得这一公式比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至少早1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