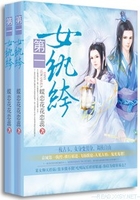腊月二十九的夜晚,孙庄鬼鬼祟祟地造访了三角线的每个旮旯,铁路新村的每处墙角,像孩提时搜索可疑的蛛丝马迹一样。他偷听了好些人家的动静。姑姑家的灯早早地睡了。杭州妈妈竟开始准备年夜饭,点燃两只煤炉,一只炖鸡,一只炸丸子,她唱一段骂一段,并发誓要吃穷姚家馋死丈夫。范多多家在炒花生黄豆,从二楼飞出来的花生壳,迷了孙庄的眼,多多该吃胖了吧?下大雪的那几天,多多去技校看孙庄,为的是告诉他,她准备顶职,范站长要退休啦。一进学生宿舍,她就扒去大棉袄,好像就为了展示被红毛衣绷得鼓鼓的胸脯。她的春天在毕业之际悄然而至。多多再也不是那瘦棱棱的秧鸡。蛰伏在她皮肉之下的许多活物,果然经不住蛊惑纷纷钻了出来,一只蚕蚁陡然间出落成一条晶莹剔透的大白蚕。
在这个夜晚,最热闹的孙家。油锅滚得哗哗的,炒锅翻得嚓嚓的,蒸锅则是嗤嗤地喷热气。炸的有咸条糖三角萝卜丸,还有用红薯掺合糯米粉做的点心。蒸的花样更多,奶奶能蒸出一个动物园来。奶奶指挥着炸炒蒸,全家都上了阵,小猴子也来了。就缺孙庄。孙庄听到枣儿操着锅铲直叫唤:孙庄怎么还不回家干活呀,害得我手上又起泡了。我要看书呢。奶奶骂道:死妮子,快翻,糊啦!孙庄是谁呀?问你妈去,她多咱生了那个鳖羔子呀!窗下的孙庄一惊,揉着眼溜走了。走进无边黑暗中。
他回到西站。站场上遍布着形形色色的灯盏,灯光很乱,面前的轨道如银蛇狂舞,月台上却空无一人。雨棚下,胡乱停放着行李车和几辆售货车。他从售货车里竟翻出一个破了皮的包子。他把包子扔向夜空的那一霎,突然响起的广播吓了他一跳。五分钟后,开往上海方向的票车进站了。下车的旅客寥寥无几,上车的只有他一人。车厢里也是同样的冷清,整节车厢成了他的专列。一发车,列车便迫不及待地广播范莹莹。喇叭里说,那个被旅客携带的摔炮炸死的女列车员,才二十二岁。它没有指出时间,那个悲剧好像刚刚发生似的。这是一趟慢车,它走走停停的,好像就是为了不断复述范莹莹的事。孙庄跟着范莹莹到了金华站,又换乘回头的票车折返。
返程是上海开南昌的快车。作为整列车上唯一的旅客,孙庄被女列车员请去了餐车,和列车员列检员乘警一道吃年夜饭。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车长高山青。高山青笑眯眯的,不断往他碗里夹菜。拘谨的孙庄心里直犯嘀咕,好不容易才认出她来。
高山青说:好几年没见,长小胡子了。看你垂头丧气的样子,肯定是把特务跟丢了。你从小就犟,还记得替我吸奶的事吗?
孙庄的脸刷地红了,却抱怨道:这趟车都成了空车皮,广播也不停。播音给谁听呀。
高山青伸手摸摸孙庄的小胡子,再拍拍他的后脑勺,说:大过年的也不赶紧回家,你奶奶该急坏了。你心里不高兴,肯定不光是技校毕业没当上司机。
孙庄愣愣地望着她。
高山青接着说:我知道你的事。你何刚正叔叔前两年调路局,现在又去了宁赣铁路指挥部。他从分配名单上看到了你。你还是党员呀,真不简单。看来,你比你爸爸有出息。你爸爸太老实了。你家过去那点事,他不写在履历表上,谁知道呀?白纸黑字的,害得自己勤勤恳恳干了半辈子也出不了头,还连累了下一代。
孙庄更是惊讶了,问:何叔叔在指挥部干吗?
在政治部。他去技校了解过毕业生情况。你给学校写了个声明,是吗?所以,你无家可归了。
孙庄再也不吱声了。于是,高山青自豪地告诉那些嘻嘻哈哈的列车员姑娘,儿女是母亲身上的肉,任何人都割不断血缘的牵连,她每次跑车经过合欢,要么能在月台上看见双胞胎张龙张凤,要么在将要进站的那一刻,可看见铁路新村的两道手电光柱,那是儿女临窗在向她致意呢。张凤还时常偷偷去南昌看她,暑假里上错了车,给拉去了广州。
果然,在十点钟过后,列车通过合欢东站时,高山青赶紧撩开窗帘,将脸贴在车窗上,仔细地在闪闪烁烁的灯火中,搜索忽明忽暗的光的语言。孙庄也在寻找。他看见了铁路边的红石楼房,看见了家里的灯光和楼上的手电光。两只划着圈的手电筒,从夜色中切割出两个深深的圆。
列车停稳后,孙庄毫无下车的意思。高山青便拎起他的网兜,叫了个乘警架着他,硬是把他撵下了车。高山青威胁道:孙庄,初四你就要去指挥部报到。你何叔叔管着你呢。要是让他知道你不回家过年,他饶不了你。
大年三十的半夜里,铁路新村所有的灯盏都在守岁。孙庄踏着满地爆竹屑,又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趟着爆竹屑、甘蔗屑和花生壳,他溜进门洞,贴着自家大门听了一阵,终是不敢敲门。
他听见奶奶的自责:俺咋忘了这茬呀,这几天咋能骂俺孩子呢,升天的灶王爷该对玉皇大帝说俺庄儿的坏话啦。秀不是买了两斤高粱饴吗?俺真是老糊涂。咋不记得供奉灶王爷,让他老人家甜甜嘴呢?粘住他的牙就好啦。
接着,就听见锅碗的响声。想来,家里已经包好了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饺子,这是奶奶往锅里放豆腐,接灶呢。大年三十晚上,升天的灶王爷要带着吉凶祸福,和别的神灵一道来到人间,那些神灵过完年后就回去,灶王爷却要长久留在厨房里。接灶,为的是接福。
孙庄出了门洞,蜷在奶奶睡的外屋窗下,继续偷听。他听见鹰儿厦儿为一把拾来的爆竹在争吵。枣儿喊道:奶奶,他们口袋里藏着爆竹。奶奶从厨房里出来,便要掏他俩的口袋。鹰儿骂枣儿:你这个女甫志高!厦儿则委屈地说:是我拣来的,为什么不让炸!奶奶哄道:俺厦儿最乖,玩火尿炕呢。大孩子还尿炕,叫同学知道了脸没地搁。明儿想要压岁钱,就赶紧把爆竹扔马桶里。他俩只好扔了,却不甘心,便揭发枣儿在床底下藏了好几本书,每本书都用报纸包着,写上“毛泽东选集”,其实都是小说。
正在给孩子准备新衣服的秀,赶紧给枣儿使眼色,叫奶奶瞅见了。不等枣儿辩解,奶奶就开口了:作吧,召来臭虫咬的是你们的细皮嫩肉!俺老啦,不中用啦,连臭虫都不稀罕俺啦!
话里有话呢,秀便打岔:年年要熬夜,等不到下半夜就呵欠连天。今年可不许睡着。下军棋吧,枣儿给做裁判。
厦儿要奶奶一起抽乌龟,谁是乌龟谁钻桌子。鹰儿找出扑克牌,去掉大小王,藏起一张牌。奶奶说:要俺来也行,俺输了谁替俺钻桌底呀?
枣儿却想到缺席的另两位成员。秀说:咋就这么巧呢,俺记得这几年他爸没在家过过年三十。
分着牌的枣儿,多分出两份。她要妈妈代爸爸,奶奶代孙庄。奶奶左手那把牌是孙庄的,右手才是自己的。奶奶笑着对秀说:你看看,你养的闺女多孝顺呀,当乌龟俺都得双份。告你们说啊,要是俺左手这把牌输了,钻桌底给孙庄留着。他能不家来吗,他不还是姓孙吗?
秀抬头瞅着窗外,竟抹泪了。奶奶白了她一眼。奶奶说:翅膀硬了,就得远走高飞。安路离开家那会儿,还没他大呢,到处是枪林弹雨的。孙庄要上班了,该高兴。俺寻思,他是想拿到第一月的薪水再家来,给俺买把新剪子,这眼镜盒也该换啦。
枣儿说:我要孙庄送一件的确良的花衬衣。鹰儿厦儿也哇哇叫,他们要的是回力鞋、篮球和乒乓球拍。
奶奶说:叫俺说,孙庄该给妈买块上海手表。人是三八装卸队的队长呢,没块表,像么当官的!
接着,枣儿加上爸爸的刮胡子刀、姑姑的衬衣、小猴子的书包,还有该为余美丽肚子里的合欢准备的礼物,给孙庄算了一笔账,把一个学徒工几个月的工资给算没了。
窗下的孙庄哭了。那压抑的哭声像猫嚎似的。鹰儿首先听到了。他支棱着耳朵,也不抽牌了。奶奶问他咋啦。鹰儿说外面可能有小偷。奶奶说,那是灶王爷带着天上的福禄寿三星回来啦。
第一盘,输家是奶奶的右手。是奶奶自个儿。三个孩子硬要奶奶钻桌子。不过,他们把桌子高高地抬起来,奶奶只要走过去就行。奶奶不依。奶奶还是给大家唱童谣——
过新年,真热闹,
闺女要花儿要炮,
老头戴个新礼帽,
老嬷嬷要个哈哈笑。
隔着红石墙,孙庄感受着这个非同一般的大年夜。墙上的煤饼印子蹭了他一身。他留在墙上的,则是一把把眼泪和鼻涕。直到他离开窗下,奶奶左手的那把牌已输了三回,就是说,他将在某年某月某日家来时,至少得钻三回桌底。
厦儿去大门后面撒尿,竟发现大门没插上。于是,他大叫起来:奶奶,姐姐又忘记插门!
枣儿说:我插了。今天我都插了三次啦。是谁的手这么贱啊,想放小偷进来过年呀?
秀不做声。奶奶却瞪着枣儿斥道:找块脏抹布擦擦嘴去!你这张嘴还不比俩小的。
孙庄哧溜跑了。跑到楼房拐角处,再也憋忍不住,放声哭起来。
奶奶对闻声推开窗户的鹰儿说:冬天过去啦。是猫叫春呢。叫春的猫像孩子哭似的,有时还能笑得格格的。怪瘆得慌的。
后来,孙家连续收到了从景德镇工地邮寄来的包裹。大年夜念着的礼物几乎都有,送给奶奶的却是一双小套鞋。小脚哪去买鞋呀。可那双小套鞋穿上正好,上自来水再也不会湿鞋了。奶奶揉着眼,喃喃道:叫春的猫是你啊!咋不给俺寄剪子呢?
剪子是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