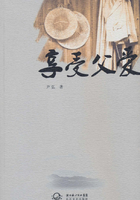过了六十,趁着眼好使,奶奶就时断时续地为自己准备百年了。她要按照老家的风俗打扮自己。其实,她离开娘家时是个大闺女,对娘家风俗所知不多。嫁到枣庄铁路上,虽说大多都是山东人,可枣庄人、济南烟台青岛荷泽人,哪儿的都有,一地一口音,习惯也各有各的讲究。而到了南方,见到的,听到的,更是五花八门,记都记不住。经过屡次改扩建,合欢站发展成为江南最大的编组站,这会儿又要建南站了,铁路人口更是天南海北。于金水为了编一个叫三句半的节目,曾叫两个漂亮的大姑娘找秀作过统计,在铁路新村里,连待解放的台湾省籍人士都有。既然如此,五湖四海的风俗习惯融会贯通,也就不奇怪了,许多讲究虽各有说法,却也分不清来路。
所以,奶奶关于老家红白事的记忆并不可靠。那不过是她凭着琐碎的旧日生活片段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是她博采众长、大胆创造的结果。不管怎样,奶奶把百年后的自己设计得艳丽而飘逸。大红披风紫红袄,藕绿裙子墨绿裤,还有黑鞋白袜。她对布料的要求很严,要纯棉布,颜色还得合意。因为年纪大了,颠着小脚上街有所不便,秀又天天忙着家属连和三八装卸队的事,她只能支使枣儿去买,为此浪费了不少布票和钞票。她把自己看不上的那些布,做成了好些小衣服,裹进了重孙辈的襁褓里,指望着能庇佑他们健康成长。
颜大嘴死后,奶奶不肯接活儿了,一心一意忙活自己的寿衣。缝着披风和裙子,她不时暗自发笑,自说自话:成么样啦?做闺女也没这么披红戴绿的,看骚的!她对镜比着照着,再强调一句:看你骚的!车头爹车厢娘,你是么呀?
虽然,自嘲的表情始终在她脸上荡漾,她对做这活儿却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就像一个小女孩,很专注地折折叠叠裁裁剪剪,赋予浪漫的想象以生动的造型。有了鲜艳色彩的映衬,生命便如落红付诸春水般平易。她戴着老花镜坐在冬天的太阳地里,对着亮晃晃的晴空穿针引线,满头银丝瑟瑟如弦,一双巧手颤颤如弓,她喃喃唱道——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自己去。
她的头发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变成全白的。或者说,是为了一件事猛然大变的。因为颜大嘴的死,秀的言行变得怪怪的,梅香坚决不再嫁了,周葱花要把破鞋扔进太平洋的心愿破产了,奶奶对张家的宿怨更是解不开了。就连杭州也不让奶奶省心。那天,杭州竟是现场的目击者,亲眼看到颜大嘴是怎么倒下的。随后,他三天两头地跟安芯闹,为的不是孩子,而是他要去支援新线。他去新线能做么呀,新线能要他?这不是故意找茬闹别扭吗?
最让奶奶担心的,当然是秀。带着这么重的心事去卸车,多危险呀。路上有不长眼的溜放车,工地上又是汽车吊车又是火车,让吊起来的钢轨枕木磕着碰着,也没个好。可是,奶奶怎么也劝不住。秀曾恍恍惚惚地对奶奶说:指不定俺真是他的亲闺女呢,他出事那一霎,俺在医院里,可右眼皮子直跳,枣儿说那叫心灵感应。其实的,俺早就觉着俺俩长得怪像。奶奶说:可别胡说八道!俺秀多俊呀,他是个丑八怪。秀啊,人走啦,早死早托生。你就别天天念着啦,你有四个孩子呢。俺那会儿,为了孩子,头七没出就拾煤核去啦,连那死鬼的忌日也没记住。你这样去卸车,叫俺天天跟着闹心啊。你看看俺愁的!你不心疼俺的头发呀?
奶奶梳头喜欢用篦子。篦子细密,能把头发篦得纹丝不乱,把头皮清除干净。末了,再蘸点水篦一遍,头发就有了光泽,熨帖而鲜亮。后脑勺上扎个发髻,人也显得精神了。掉在肩头后背的头发,都是叫秀摘去的。这阵子,秀老是忘了替奶奶摘头发,每天倒是叫余美丽碰上了。
奶奶终于忍不住了:美丽啊,有么话对俺说呗。你天天一大早就上门来,指定心里有事。你瘦了好些,得爱惜自个儿啊。
其实,余美丽不仅瘦了,而且脸色寡黄,还长出了一些褐斑。不过,此刻她却是满脸通红。她捏着一根白发对着阳光照了照,说:奶奶,你头发长得好,虽说都白了,还是又浓又密,掉的少。你能活一百岁呢。
那就成老妖怪啦,肉都耷拉着,找着鼻子找不到眼,可别吓坏了俺的重孙子。俺不要一百岁,等着抱上重孙就行。就怕活不到那会儿,这阵子眼不得劲,耳朵也快聋啦。
耳聋长寿呢。
奶奶的语气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为么呢?看不到听不见,心不烦。你别是为俺一百岁来的吧?
余美丽帮着奶奶把椅子搬到墙根下。俩人一块坐定后,她说:奶奶,那天在山上,我给那些坟都散了喜糖。安路他爸爸、连根和他父母,还有莹莹,都吃上了我们的喜糖。
奶奶心里一热,一把攥住了余美丽的手。她的声音在发抖:好,你是新娘子,该。俺让老颜揣上喜糖带去,你也没忘散糖呀。多好的媳妇!他们在地下都得保佑你!他们嘴甜着,指定天天说你的好话。老颜娶你是福气。可他咋就没福气进洞房呢?你说说,一个大男人,一辈子没见过女人,他活得多憋屈呀!
余美丽喃喃道:他见过。
见过?他对你说的?他老家真有媳妇孩子?奶奶问。
余美丽却是坦然:我不敢跟他提过去,想到过去他就哗哗流泪。我是说,他见过我,见过女人。
奶奶瞠目结舌。好一会儿,才问:你给他啦?多咱的事呀?
给了。有些日子啦,周葱花给我们做媒后,他一直不阴不阳的。我就问他,嫌我是破鞋吗,痛恨钉在墙上的道钉吗,我不好看吗,不喜欢我的发型和花露水味吗,讨厌我下巴上的痣吗,那是美人痣呢。他说不是。说我是鲜花,他是牛粪。他怕自己身上的疤吓掉人的魂。我说,我见过你这样的男人,那个男人死了,我的魂还在呢。那些道钉就是我的魂。我的身子也是我的魂。
说着说着,余美丽竟像在批斗会上的表现一样,声音腻腻的,眼神迷迷的,微笑醉醉的。奶奶拍了她一下:快别说啦,没羞没臊!
余美丽瞅瞅四周。孩子早上学去了,大人也都上班、买菜去了,四下静悄悄的。于是,意犹未尽的她,胆子更大了:有天夜里,他上门来告诉我,说小蒋也认为我是好人。我问,好在哪里。他说,心眼好,实在。我说好不好的,要你自己去看去体会。你不是巡道工吗,盯着线路检查得多仔细呀,一颗道钉松了也不放过。这些年,我全身的道钉都松了,你不给检查一遍?你就不怕我成了事苗,酿成重大事故,影响安全运输吗?
奶奶扑哧笑了:你这是么人呀?你成狐狸精啦!俺怕你想不开,还叫秀和葱花常去看看你。你心里倒是豁亮。美丽啊,生死有命呢,是得放宽心。你们拿了结婚证,你就是老颜的媳妇啦,该上单位说去,他咋的也得算烈士,不能只给个工伤了事。么历史问题呀,不就是让老蒋抓了壮丁吗?可人救了火车!是英雄呢,比杭州更英雄!
可是,余美丽却说:老颜不在了,那名分对他没有意义了。别人不会再怀疑他是那边的特务,他在地下也就合上了眼。我也不在乎。吵呀闹呀,还不是找气受?就算争得烈属的待遇,带大孩子还是要靠自己。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奶奶又是一阵惊喜:说么呢,你有孩子啦,怀上啦?
怀上了。这些天,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还担心,马上就见肚子,叫家属连看见,还不得用唾沫淹死我呀?说我未婚先孕,那是事实,我不怕。就怕她们说我怀的是野孩子,对着孩子指指戳戳。我不是胡诌过流浪汉的事吗?
奶奶乐得在她脸上掐了一把,说:美丽,俺信!俺还纳闷,老颜是头犟驴,一跟你谈对象,咋就变成马驹子呢?那天头晌在你家,他不就是小马驹吗,一步不落跟在你身后撒欢儿,俺不是说,新娘子变成枣红色的母马了吗?别人要是敢胡说八道,俺替你撕她的嘴!
余美丽说,她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无论男女,都叫颜合欢。生下孩子后,她就去做临时工,找不到工作,就去拣煤渣去卖菜。为了孩子,她不怕吃苦遭罪。奶奶说,去三八装卸队吧,马上不搞义务劳动了,能发工资呢。
叨念着孩子的名字,奶奶忽然想起为老颜立碑的事。她说:美丽,俺寻思,你和他还没入洞房,往后日子还长呢,就没让安路刻上你的名字。别怨俺啊。
余美丽眼睛潮湿了:奶奶,你是为我着想呢。明年清明节吊青,我要把名字加上,把他儿子的名字也刻上去。让老颜看看,他有儿子啦!他的儿子叫颜合欢!
奶奶也很激动,冲着东站方向喃喃道:大嘴啊,你真是个大特务呀,人小蒋盯你没盯错呀!你看看你,放了半辈子烟雾弹,末了,入个洞房也是悄悄地进庄。像电影里的鬼子。俺还当你是童子鸡呢,你都有儿子啦!那会儿,小蒋逼着你放长线钓大鱼,他被鱼拽到河里去啦,鱼被你钓上岸啦。还是条美人鱼呢。
奶奶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立马就要给颜合欢做婴儿衣。颜合欢还在娘肚子里呢。颜合欢还没成形呢。颜合欢穿着胞衣,穿着母亲的身体和父亲的灵魂。
装卸队要是下午收工早,吃过晚饭,便有人陆续来孙家串门。奶奶把十五瓦的电灯放矮了,坐在床头,迫不及待地缝着白天裁好的小衣服。她手里的针线活,就像一条标语,把余美丽怀孕的消息发布出去了。那是颜大嘴的遗腹子呢。这个消息,就像黄梅天的北风,湿漉漉的空气水淋淋的墙,顿时便干爽了。周葱花脸上的愁云惨雾荡然无存。她重新获得了做媒的勇气。她不住嘴地夸奖余美丽,一激动,又踌躇满志了。她说,为了保证铁路大动脉的安全正点,我们家属连要把全合欢铁路的光棍称号统统扔到太平洋里去。
奶奶沉下脸来:又瞎咧咧啦,说谁呢?
周葱花意会了,格格地笑着说:我指的是年轻的光棍。
奶奶摘下眼镜:多大算年轻?你的孩子,俺的孙子孙女够年轻吧,你也一块扔太平洋?
奶奶,我指梅香于金水呀,隔壁的嘉兴呀,楼上的张卫国,范家的明明、亮亮呀。唉,那个明明到现在离不了,我干着急,不敢插手,人家是军用品呢。
奶奶伸手逮住周葱花的翘屁股掐了一把,周葱花很夸张地尖叫一声:奶奶,你又掐我呀。我的屁股都让范站长掐紫了。看着他蛮正经,阴坏呢。
奶奶说:人喜欢你这热乎劲,俺也喜欢。叫俺说,那些光棍你放在心上,眼下赶紧地帮帮余美丽。你不是大媒吗?照说,做媒不能保人生孩子,可人怀上啦,你白拣了个功劳!多长脸的事啊。你还不得好好地显摆显摆?这事得告诉工务段,老颜不光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人母子往后咋办,该给个说道。
周葱花当即表态,明天就向上面反映去,家属连认为颜师傅应该算烈士,烈士的家属应该顶职。万一不能顶职,就去三八装卸队。这样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
第二天,风风火火的周葱花,竟领人给余美丽送奶粉奶糕去了。余美丽说,孩子要等到明年五月落地呢。周葱花哈哈直乐:往你嘴里喂,不也是到了孩子肚子里?
余美丽心里有数,奶奶是借周葱花的嘴,早早地大肆张扬自己的肚子,真正的用意,是不让人有丝毫猜疑,堵住自来水边那些蜚短流长的嘴。
一个月后,西伯利亚的寒潮带来一场大雪。在南方,这场雪是罕见的。
雪断断续续,连着下了好几天。起初,它很温柔很诗意的,零零星星的雪花悠悠然,飘洒在不经意的视野里,没有先兆也没有宣言,如一树树花骨朵儿无语绽放在没有风的日子里。未待落地便已融化,刚刚诞生迅即死亡。所以,那会儿,奶奶根本不相信下雪的事实。
雪是在雄浑的歌声里越下越大的。那歌声似乎对天气怀有某种敌意,或达成了某种契约。歌声显然刺激着、要么是感染了阴郁的天空,柔情的腼腆的雪渐渐变得剽悍和蛮横,不再情愿就那么轻易落在地上,而是顽强地搅起了风。依仗着风,脆弱的生命变得持久了。雪花愤怒地翩飞着,疯狂地旋舞着。天地万物在纷繁迷乱的洁白中一片混沌,天地没有了界线,万物没有了轮廓。只有那歌声依然劲挺,依然兀立在连汽笛也变得萎靡的调车场上——
巡道工人英雄汉,
不怕牺牲不畏难;
踏破铁鞋为革命,
洒尽热血保安全。
风雪弥漫。歌声弥漫。扩建已经完工的东站,显得更加宽阔了。密布的钢轨,密布的车阵,密布的扳道房。因为雪,这里和南面的山岗、田园、村舍融为一体。一位歌手就藏在密密的车阵里,面对某一只麦克风望情地高唱着铁路工人非常熟悉的歌,供作业用的高音喇叭将他的歌声糊里糊涂地撒向整个合欢城。开始,人们只拿它当儿戏。后来歌声渐渐频繁,天气也在这铺天盖地的歌声中变冷了,人们才开始烦躁起来。铁路中学和小学的校长接到通知,通知要求各学校加强教育禁止学生去车站玩耍。通知未能禁锢歌声,这说明拿调车场当舞台的不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毫无办法。唱歌其实比调车场上的工人利用喇叭聊天骂娘高雅得多,比捡煤渣的扒车的利用喇叭招呼伙伴光明磊落。车站只好听之任之。
大雪纷飞,歌声纷飞。在铁路新村,莫名其妙的行人踉踉跄跄奔走在风雪里,不时顾望东站,都是一脸的惊惶。杭州望着窗外,冷笑着对安芯说:是于金水呢。他在为颜师傅鸣冤叫屈。你听听,曲是老的,新编的词。《调车工人英雄汉》变成了《巡道工人英雄汉》。
于金水重新填词的这首歌,唱的真是颜大嘴。于金水本来准备组织宣传队赶排一个男女声四重唱,参加春节期间的路局汇演。可是,这首歌在合欢地区就给枪毙了。理由很简单,颜大嘴不是烈士,因而不宜大力宣传。其英雄壮举固然可嘉,可工务段认为他有历史问题,压着不肯上报。工务段其实是怕这件事牵连出道口管理的责任。工务段还振振有辞地说了些闲话。说,水牛皮坚韧,火车轧上去会出轨,可那是一趟准备进站的车,已经减速了,它本来完全可以不把水牛当回事,打着唿哨扬长而去,而颜大嘴冲进道心,使情况变得复杂了,再说,他死于牛角而非车轮。如此颂扬颜大嘴,特别是再弄首歌唱开来,很可能有人会为猪呀狗呀鸡呀搭上性命。当然,要害处还在于历史问题。于金水愤愤不平且不甘,竟到调车场上来传唱他的新歌了。他要教会调车员、扳道员、车号员和列检员,以及所有在东站上班的员工,包括拐五三上的押运员。
安芯打开窗户,让钻在窗缝里的歌声涌进屋来。她说:真没想到,为了颜叔,他成了大男人。一个敢做敢为的男人。找工务段找地区找路局,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竟敢来撺掇你一块呼吁。
杭州问:我比领导还可怕吗?比那条水牯还凶恶吗?
接着,杭州又说:他写英雄唱英雄,我看他自己比英雄还英雄。这年头,谁敢这样为别人打抱不平呀!有个领导把我们联名写的材料都砸在他脸上了。
颜大嘴出事的时候,杭州是现场的目击者。那天在下班路上,他和安芯又拌嘴了,气得安芯撂下了他。他过了道口,独自站在桥吊旁边看调车作业,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发生在他的眼皮之下。一连几夜,他耿耿难眠。所以,当于金水得知他是目击者来了解当时的情景时,他竟痛哭流涕。他说人家才是真英雄我是狗熊。他说人家一辈子任劳任怨绕地球走了三圈呀我连半圈都没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