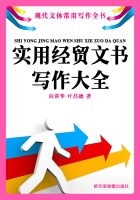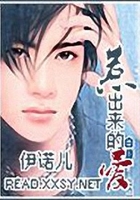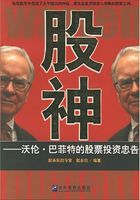我只勾引过头一个。我扔裤衩给他,是因为我晕倒在脚盆里了。他进来抱着我,说我的头发真好看。我说,脸呢?他说,也好看。我说,身上呢?他哭起来。说他虽是流浪汉,却是好人,家乡遭灾了,这才扒车跑出来,想找个活儿混口饭吃,饿了好几天。我说,你就把我啃了吧。还要往下说吗?
问:难道你有问我们的权力吗?难道还要我们交代政策吗?
那就好,我彻底坦白。他疯了,亲我咬我拧我,也要我同样以牙还牙。像《铁道游击队》里岗村的那条大狼狗。我身上印了花,成了白底暗花的的确良。后来他就要那个。不,是我要,我老实坦白。他要带我到里屋床上去,我来不及了,我全身软瘫如泥,我们就在厨房地上,弄得全身尽是煤灰菜叶饭粒。我从来没领受过那种凶猛的劲儿,我恨不能让他吸尽骨髓,把每根骨头中间通一通。那次,我在下面。我只知道这样。他在浙赣线鹰厦线上跑来跑去,也没找到工作,路过合欢就来看我。后来有一次,他说今天不是三八节吗,妇女要翻身,我就翻身了。他不断想出新的花样来,点横竖撇捺,他能把这简单的笔画弄成一本厚厚的字典。
余美丽说得有三分羞惭七分迷醉。台上的她已经不是破鞋了,而是个传教士或性教育的启蒙者乃至表扬家属连的某位上级领导。有好些女人竟无法自制,或者尖叫着“再具体点”,或者像遭非礼似的惊呼,梅香干脆莫名其妙地晕了过去,叫坐在她身后的秀抱住了。当然,正襟危坐而穷追不舍的是大多数。
问:一共多少次?
我没记,比夫妻做的总数要多,大概有一篮子吧。
又是一阵哄笑。对于“一篮子”的概念,大家已经掌握。她们只是惊讶时间与数量或曰重量的强烈对比。也许正因为对比强烈,从这一刻起,关于剪“阴阳头”的威胁悄然流失了。
问:十年的半篮子和这一篮子怎么解释?是你故意亏待你丈夫,还是你丈夫有病?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来到世上就是性命,有生有死,哪能亏了人家呢?他是养路工,从来干活不要命,你们没见光屁股的他呀,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尽是五彩斑斓的伤口和疤痕,有新鲜的嫩肉,有涌动的血珠,也有腥臭的脓水和肥嘟嘟的蛆虫,烧伤烫伤砸伤撞伤戳伤摔伤轧伤,看得见的皮肉惨象之下,肯定还有无可救药的内伤。所以,每回我越主动他越紧张,后来他连衣服也不敢脱了,撒尿似的一掏。砸洋镐也要脱掉上衣图个利索对不对?
当过农村小学老师的余美丽,用乡音浓厚而动听的声音娓娓道来,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以致娘子军全连官兵都听得入了迷。她们放过了余美丽的头发。那次批斗会开得非常成功,成为后来的范本。文斗,而不曾武斗;触及灵魂,且一饱耳福;增长见识,并寓教于乐;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又是精彩的文化生活。
那是盛夏,合欢花已经凋谢。在闷热的夏夜,家家户户总是露宿在房前屋后,一溜一溜的竹床门板漂浮在星光月辉里堵了路封了门,好像发大水似的,光得不能再光的大人孩子就成了爬上漂浮物逃生的灾民,大人呱嗒呱嗒摇着大蒲扇,划动着焦灼的时间,将一家老小渡到凉爽的清晨去。而批斗会后那些个奇热的晚上却是反常,露宿的床少了许多,摇扇的声音听不到了,睡在外面的几乎都是孩子。后来有一阵子,铁路医院妇科医师忙得见了孕妇产妇就急,她们骂道是不是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一夜间把你们全糟蹋了?
会后,周葱花问秀:梅香怎么晕过去了呢?
秀说:俺也知不道。别是饿的吧?
饿的?她下班后没吃晚饭吗?走,我们一道去看看。这回她该明白我们的苦心了吧,是为她好呢。秀啊,你说得对,她是饿晕了!
周葱花嘿嘿一笑,贴着秀的耳朵补充道:这个会开得,连我也饿了。那流浪汉真厉害,还有那么多花样。夜里,让孙大车学学?
接着,周葱花告诉秀,合欢乡下男人喜欢用吃肉比喻所有的美好,那事就比吃肉还好嬉。这时,她目光迷离,竟学着某个男人的腔调,说了一句土话:要是吃肉有××好嬉,猪崽子都会被吃光了。
秀满脸通红,轻声说:连长带头学吧,你男人可是响当当的八级钳工!叫俺说,别再开余美丽的会了,把人都教坏啦。老古话说,捉奸捉双。没捉着,逼着人承认,人不就胡诌吗?就算她是破鞋,也要脸要皮呀!说得连俺听的人都想钻地缝,俺觉着吧,她是存心的。
周葱花说:对,存心的。从前她的嘴是锈死的道岔扳不动,这回脸皮厚得像钢轨能过火车。她耍小聪明,在学范站长呢。
秀说:俺没文化,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别批评俺。俺怪同情她的,嫁的男人多窝囊呀。那个流浪汉的事,俺不信。她男人,俺信。俺干爹身上跟他一样吓人,俺闺女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呢。难怪的,俺干爹打了一辈子光棍,他是怕媳妇嫌啊。
周葱花一听,兴奋起来:秀啊,让余美丽给你当干娘怎么样?让颜师傅娶了她,一个得到了老婆,一个摘掉了帽子。颜师傅和她死去的丈夫是同事,这些年他不时上门帮着买煤做煤,他们有感情基础。说不定,余美丽不再嫁,就等着他呢。也许,那个流浪汉其实就是他。
秀连忙摇头。余美丽的名声太臭了。
而周葱花却意味深长地表示,从今往后,我们家属连要把做媒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要让所有的寡妇光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能消灭偷鸡摸狗的现象,也有利于安全运输。她的语言是生搬硬套的,但她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把铁路新村垃圾堆里的所有破鞋扔到太平洋里去。
她和秀敲开了梅香的门。此刻是晚上十点钟,梅香刚刚出浴。
屋中央的大脚盆里盛着半盆女人的肤香和撩人的水声。地上放着泡软了的香皂。小板凳上有苹果剖面似的臀印。一面镜子正好映着对面墙上的相框,相框里的陈连根一直在偷看她洗澡。门后的墙旮旯里钉着由道钉组成的方阵,因为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布鞋而成了别出心裁的鞋柜。
秀盯着那些布鞋,认出那都是奶奶给她一家老小做的,包括给连根的。周葱花也紧盯那儿。不过,她是联想到余美丽家厨房墙上的道钉。它就像插秧一样,按照行距株距,把婚姻经历装置成了生活艺术。
周葱花指着那儿问:什么意思?
擦着湿头发的梅香慌了:挂鞋的,没挂篮子。
我连鞋和篮子都分不清吗?我问那些道钉有什么讲究。什么时候跟人学的。
梅香可怜兮兮地望着秀,说:没有学她。哦哦,我不是她那种人,我老早就钉上了,每年钉一颗。连根去世那么多年了。
周葱花恍然大悟,说:还念着他呀。你还有一辈子呢,你想把整面墙都钉上道钉呀,不嫌难看呀?别紧张,我们来,就是问问会后你有什么感想。
秀近前挽住梅香的胳臂:葱花连长关心你呢。
梅香扔了毛巾,也用手绢把头发扎起来,凄然一笑:感想就是赶快嫁人,不嫁人小猴子得饿死。现在煤渣都被机务段管起来,不让拣啦。我怎么养活小猴子?
周葱花和秀都一愣,对视片刻后,周葱花说:哦,你误会了,叫你开会,是因为你不算正式工就该归家属连管,跟你去公寓上班无关。
什么无关!刚才公寓来人通知,叫我明天不要去上班。行,我听你们的,嫁人,嫁谁都行,只要饿不死我们母子。梅香说。
周葱花当着梅香的面发火了:张段长这个浑蛋!为了把自己撇干净,不管别人死活啦!他还会搞阴谋诡计呢,趁着我们叫梅香开会,立马撵她。这不是让我们家属连背恶名吗?难怪贴出大字报,他都没事。他比狐狸还狡猾!他是一条老狐狸!
见安芯抱养了孩子,于金水就不再为挑选演员去缠她了。他也不敢去。杭州成天阴沉着脸,随时能电闪雷鸣。
过了暑假,枣儿读高中了。也不用上课,铁路中学的师生成天忙着挖防空洞,竟把学校所在的那座山包掏成了马蜂窝。
枣儿嫩嫩的一双手,长出了老茧,磨破了多少层皮。她心疼得家来就哭。于金水还缺扮女儿的演员,见着抹泪的孙枣,就选定了她。女儿的角色要求就是善哭。孙枣在台上得出场三次,每次都是为了痛哭,分别是为老板逼死爷爷、恶霸强占妈妈、工头打伤爸爸呼天抢地。在于金水的辅导下,她哭得非常出色,每次排练回来都是眼皮红肿嗓音撕裂,以至后来惹得观众们泪雨滂沱义愤填膺,不断怒吼“牢记阶级仇”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