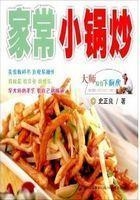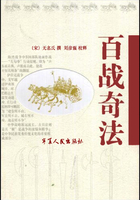奶奶对庄儿的牵挂,变成了没完没了的絮叨。她的絮叨,多半是对秀的怨。怨秀不该撺掇庄儿给那“蹄子”写信,不该向人伸手。秀总是微笑着忍住,也不吱声,也不生气,任由奶奶说去。
奶奶低着头,把眼睛从老花镜片下拉上来,不满地紧盯着秀:忙么呢,你咋就不能坐下歇歇,听俺说说你?像条蛆似的,尽在俺眼前晃,晃得俺眼花心烦。
那阵子,谁都心烦。世道不知怎么了,坐火车也不要买票了。南来北往的,都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学生。合欢是中转站,这会儿客流量大得惊人,站前广场上、候车室里,甚至两座月台上,成天人头攒动。红卫兵大串联呢。所有的列车都没了点。该到站的一再晚点,该发车的发不了车。发不了车是因为学生们拼命往车上涌,站上的广播喇叭撕破了喉咙也不管用。铁路公安都调到客站去维持秩序,小蒋也就管不了老蒋那边的人和事了。就连居委会的干部,也得轮班去车站帮忙。秀望着那个乱劲,对翘屁股的周主任说,那些孩子能听俺的吗,俺觉着堵住合欢铁中的学生最要紧,别让俺的孩子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帮忙。周主任点头称是。于是,居委会干部日夜把守在机务段边的出站口上,那是铁路员工的便捷通道。她们劝住了十几拨想去北京见毛主席的铁路子弟。不过,却没能拦下金华。金华说,我到售货组找我妈妈买包子不行吗。秀说,就怕你去串联呢,车厢里人挤人人摞人,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睡着人,厕所里塞满了人,走一站,停半天,哪天能到北京啊,几天不吃不喝还能熬,不拉不尿行吗,还不得活活憋死呀。不是说,前阵子有个闺女蹲在过道解手,叫人踩死了吗?金华发着毒誓硬说是去买包子,秀也就无奈了,只叮嘱道:可别上车啊当心叫人踩成肉馅子。谁知,金华竟扒在车门外走了。因为车厢里太挤,到站的票车大多打不开门,车窗便成了出入口。一旦车窗紧闭,便有不怕死的,贴在车门上或爬上车顶,就像逃难的灾民似的。金华一走就是多半个月。毛主席没见着,倒是把也想见毛主席的一个山东女大学生带了回来。
秀坐立不安,就是为那闺女。她是那“蹄子”的小闺女,也就是安路安芯的堂妹,叫孙安芸。昨夜,金华从车窗跳到月台上时,正好让值夜班的秀逮住了。秀朝他后脑勺呼了一巴掌,说你这臭小子买包子买到哪去啦你妈双眼哭成一对大肉包啦。金华说,我给你家带礼物回来啦。说着,就从车窗里抱下一个穿军装戴军帽的大闺女。他俩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认识的,聊到南方聊到鹰厦线,孙安芸就打听合欢打听孙安路,金华说孙家是我家亲戚呢。秀顾忌着奶奶的态度,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先送安芸去行车公寓,让梅香把她安顿下来。
已是半上午,老这么晾着人家也不是事。金华正急得不停地在门口探头。秀终于鼓起勇气,坐到奶奶身边,替她摘去掉在背后的几根白发:他奶奶,这白头发也铮亮呢。像细铅丝一样,多稀罕人呀。你看看。
老啦。快不中用啦。有么事,说吧。昨儿半夜里你回来,隔壁金华也回来了,俺耳朵不得劲,可他妈又是哭又是骂的,俺还听得到。你说,她骂儿子凭么扯上你?
她骂居委会呢,没替她看住孩子。你猜猜,金华这孩子从北京带回谁了?
奶奶这才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北京?北京俺就认识毛主席和吕正操。
秀继续让奶奶猜:是从山东去北京的,女的?
俺从前认识的大闺女小媳妇都该成老嬷嬷啦,谁能让他个毛孩子带到南方来,来做么呢,给他做娘还是做奶奶?
她们的闺女呀。你再猜。
奶奶说:人就是怪啊。孩子们一个个人小鬼大,大人呢,比孩子还会发嗲。俺秀么时候学会了杭州妈妈说的倩煞煞呀。
秀搂住奶奶的胳臂,贴着她耳朵说:安芸来啦,安芯有张相片抱着的那个闺女。
奶奶一愣。紧接着,忿忿地推开秀:死妮子,她咋来啦?为么来呀?俺活得好好的呢。就算俺死了,俺也不稀罕那蹄子来给俺送葬!
秀说:那是个孩子呢,十八九了,大学刚毕业。夜里到得晚,俺把她安顿在公寓。人想她大娘呢。那闺女长得跟安芯似的,又白又俊,小嘴可甜哪,怪招人疼的。
奶奶态度很坚决,不肯让人家进门,并说:俺就奇了怪了,好没来由的,她自个儿咋就上门来了呢,别是安路和你撺掇的吧?你们小两口子想做么呀,老背着俺跟那蹄子粘糊?
秀说:人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和金华拉呱上了,一拉,正巧,也就跟着来合欢啦。
巧么呢?毛主席么时候来合欢啦?他老人家来,俺安路知不道吗?一准叫安路去拉专列啦。
秀哭笑不得,一转念,便顺着奶奶说:那好,俺这就去公寓,告诉安芸说,她大娘恨着她娘,恨得牙痒痒,赶紧回去吧,多俊的脸蛋呀,别叫大娘啃下一块肉来。
那叫大娘吗,那成了老狼!奶奶悻悻的,白了秀一眼。
秀小心翼翼地说:安芸说,她起小就纳闷呢,为么老听见娘念叨南方的大娘一家,俩家咋就没来往呢?铁路家属不是有免票吗,为么大娘不带着媳妇孙子孙女回老家看看呢?人家就是想不明白,才会跟着金华从北京过来的。把人撂在公寓里,还不叫老家笑话死啦?再说,上辈子的怨,哪能传给晚辈呢?
奶奶沉着脸:谁说俺和那蹄子结怨啦?俺腻歪她!你没见那会儿她多贱!她的事俺都不兴对你说。
说着,奶奶摘下老花镜,放入别着好些缝衣针的眼睛盒,再找出尺呀剪子呀线团呀,用块布一裹,要去连根父母家。她对秀却说:告诉安芸吧,她大娘去技校看大孙子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你咋侍候她俺不管,俺眼不见心不烦。
人要是等着不走呢?
1
秀劝不住,更拉不住,很是无奈地送她出了门洞。连根母亲忽然来请奶奶做衣服,真是出奇。因为那两口子很会过日子,平时不是军装就是铁路制服,没见过穿别色的衣服,军装都带补丁,新制服也要在箱子里搁几年才穿上身,连根母亲身上则是改小的军装或制服。一旦听人说长道短,他俩便唱和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这会儿,好没来由的,连根母亲居然买了一堆布料子,不仅要给梅香母子做,还要给自己和老伴做,而且要把奶奶请到她家去做。
谁知道,奶奶竟在半道上叫安芸堵回来了。是等不及的金华,叫上孙枣去公寓把安芸领来的。枣儿拥着安芸,一口一个姑姑,叫得可亲啦。奶奶跟在后面直嘟哝:是你姑奶奶呢。
秀迎着两个闺女说:老孙家的闺女在哪都不走样啊,知不道的,当是两姐妹呢,加上安芯,是三姐妹。
奶奶在床沿上落座后,瞅瞅她俩,奚落道:丑到一块去啦,都是塌鼻梁,大蒜鼻头。芸啊,快把帽子摘了吧,皱拉吧唧的,像棵酸腌菜似的,俺看着就犯酸。
秀笑了,对着安芸说:你大娘馋山东大蒜馋的,看你的脸是白面的煎饼,耳朵是柿饼,小嘴是醉枣,掉色的军帽成了酸腌菜。
安芸说:大娘,怪不好意思的。我在北京碰上这个金华,临时决定来的,只买了些北京的茯苓馅饼。回去,我再给你寄老家的特产。
奶奶说:别听你嫂子瞎咧咧。俺合欢是个好地方,么都有。甘蔗柚子橘子,北方没有的这儿都有。你这孩子真是,车上多乱呀,也敢来。没听说人掉下月台给轧了,在车上给挤成泥了?俺成天担心庄儿,也像金华这个鳖羔子乱蹿呢。亏得俺庄儿懂事了,老老实实在学校呆着,怕俺担心,隔天来封信。
安芸扑闪着大眼睛,听出弦外之音:没有金华这个小弟弟我不敢来。在北京站,他扛着我上的车。他说回山东不愁,从火车司机到列车员乘警,都是他家亲戚。大娘,你身体挺好的吧?
好。么病没有。一顿能吃一大碗白米干饭。俺爹在老家活到九十八,临死前还能下地做活。俺寻思俺像他,能活一百岁。你爹呢?
挺好的。年轻时在铁路干装卸,后来干不动了,回乡种地去,当上了大队长。
俺记得你上头有两个哥哥,都该有几个孩子了吧?
都是俩。我大哥在济南工厂里上班。二哥在枣庄煤矿上。我哥我姐呢?安芸指的是安路和安芯。
奶奶说:都当班呢。安芯下班就来,安路跑车没个准,照这个乱劲,指不定得十天半月。你上大学啦,学的么?
我在济南读师范,刚毕业,这不等着分配吗?我姑父要我到济南铁路上去教书,回头就该分配了。安芸说的姑父,就是当年的游击队连长。
奶奶问:你经常见他?他是大干部啦。他们一家可好?
安芸把他一大家子的情况都说了。奶奶问这问那,偏偏不提安芸的母亲。安芸说:大娘,我要求进铁路,就是为了今后能调到南方来。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将来台湾解放了,再跟孙庄一起去宝岛台湾搞建设。我喜欢这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就是受孙庄的影响。他写信说,这里每天都过军列,铁路边架着高射机枪,美蒋的U2型飞机经常飞过来,他好几次差点抓到美蒋特务。这样的生活多有味道呀。不过,他的信闹得我娘几天几夜睡不好,牵挂着你们哪,烧香磕头的,拜了门神灶神拜土地,那些神哪能管到十万八千里去?可她说,再远不也俺老孙家的人吗?
奶奶愣愣地瞅着她,不知说么好,表情却是复杂。
秀赶紧抢过话头:调过来好啊,铁中正缺老师呢,教高中的老师初中还没毕业,有的还是线路工调上来的。你这大学生能成一块宝。再说,那还不把安芯乐坏啦?
安芸兴奋起来:我姐的事听金华说了。我真敬佩她,那才是真正的革命爱情,革命爱情才会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力量。说心里话,真正促使我下决心来的,是这件事。我要当面祝福我姐和姐夫。
奶奶忍不住了:芸啊,等天黑安芯下班回来,去她那儿看看布帘子后头垒成一面墙的革命爱情,再说调不调来的事。俺老孙家有一个傻大姐就够受的啦。
安芸在合欢呆了三天。奶奶说起话来不冷不热,招待却是不含糊,顿顿有鱼有肉有鸡有鸭,一个月肉票全用掉了,为买好菜和让安芸捎回去的土特产,还向范站长家借了十块钱。奶奶悄悄地对秀说,别心疼钱,打肿脸充胖子也得争这口气,都是庄儿那鳖羔子给俺惹的事,俺不缺那蹄子的五块钱花!
给准备的土特产,是十多个柚子和一捆甘蔗。和堂妹在一个枕头上睡了两夜的安芯踹了它们一脚,抱怨道:嫂子,这不是为难人吗?人都挤不上车,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人带得动吗?
奶奶说:找你小叔子金华呀,他不是说铁路全是他家亲戚吗?再说,人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能让人空手走呢?你还是人家带大的,别叫人说不懂道理!
安芯撅着嘴说:东西别带了,我让安芸给婶婶捎了二十块钱。
奶奶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是你的。俺是俺的。秀,把甘蔗剁巴剁巴,装在旅行袋里,再找个大网兜盛柚子。
金华还真挺负责,居然联系了福州到北京的行李车。金华高中毕业了,正等着冬季征兵呢。是安芯领着孙枣孙鹰跟金华一道去送站的。爬上行李车后,安芸说:姐啊,大娘和我娘这一辈子到底有么疙瘩呀,三天她也不提我娘。
安芯说:等你真调过来,日子久了,你就知道啦。
又一趟票车进站了,是上海开往厦门的特快。安芸望着那趟车上的指示牌,认真地说:我一定争取调过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奶奶在家里一直留意着发车的动静。现在,铁路新村再也不能凭着列车到发的动静生火了,指望听动静做饭得活活饿死。奶奶问:秀啊,福州车晚点多久啦,咋还发不了车呢?
秀说:好在上了行李车,挤不着安芸。等呗。
奶奶又问:知道俺为么让捎上甘蔗和柚子吗?
甘蔗为么节节甜啊,长得直,长得实在。甜在根上。根甜,整棵甘蔗都甜。柚子为么瓣瓣酸啊,树就没长好,长得曲里拐弯的,树干弯,树枝也弯,枝上还带刺,叶子带臭味。
这是奶奶认准的理。她说过多少遍了。
连根父母也住在下坡道那儿,和梅香娘俩是前后栋,不过,那是新建的三层楼。那栋楼里还住着翘屁股的周主任。奶奶是春节过后去给老陈家做衣服的,陈家给工钱,还管三餐饭。
奶奶说:做手工不比踩机器,不出活儿,俺就搁你家睡吧,夜里还能做一会儿,两头不耽误活。
连根母亲说:好啊,我正寻思咋开口呢,做活不要紧,我们唠唠嗑。奶奶你不知道,这个家里放下碗筷就是眼对眼唉声叹气。一年到头没个串门的。我家老陈出来进去的,老板着个脸,对谁都爱理不理的,人说他架子大,把人得罪光啦。他哪是架子呀,就是这脾气。我为什么做这么多衣服呀?你看看,你一来,这一上午多热闹,楼上楼下都来了。
奶奶笑道:多稀罕人啊,做衣服图的是热闹!敞着门吧,俺成公园里的猴啦。
连根母亲对串门来的邻居特别热情,倒茶递烟的,还不断往她们的孩子兜里塞糖果。孩子闹着要上大街逛公园,她便钻到床底下,拖出两只可能是过去铁道兵部队用来盛雷管的木箱子,翻出连根留下的篮球和一大堆小人书。那些小人书虽发黄了,却是完好无损。连根母亲说,小猴子就喜欢口琴,不爱看书,要不早糟践了。她还说,看我家连根多爱惜书呀,到现在还像新书。言下之意,是叮嘱邻居看好孩子。她自己也紧盯着翻书的几个孩子,不时警告几句。
奶奶见她那紧张劲,便说:你心疼书,快收起来吧,别叫孩子撕了。好好留着,等小猴子大了懂事了,就知道那是个念想呢。
说着,那几个孩子竟为一本打仗的小人书争抢起来。连根母亲上前夺下书来,孩子们一起哭闹起来。她用大把大把的糖果,才哄住他们。可是,她家的小人书却被好些孩子惦记着了。
黄辣椒也来陈家看奶奶了。她扒着门,伸进半个脑袋,很夸张地叫道:哎呀,是奶奶呀。我去三楼串门路过,心想陈主任家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原来奶奶在这里。
主人请,奶奶唤,黄辣椒就是不肯进门,却又不走,倚着门框,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闲天。奶奶说:你也不嫌累得慌呀?人叫进就进来呗。想叫人先打药水还是咋的?
黄辣椒脸一红,借故得赶紧去接车,腰一扭,折转身子下楼了。奶奶对着门口讥嘲道:咋不上三楼了呢?车哪有点呀,慌么?可得留神,千万别碰上流弹!
前些日子,不论货车车皮还是客车车厢,都用墨汁或石灰水涂满了“炮打”、“火烧”之类的标语,南来北往的火车好像就为了运送那些触目惊心的标语。接着,造反派和保守派闹武斗,合欢站有个列检员正当着夜班,被流弹击中一命呜呼。孙安路也有一次历险经历。那是在彰武车站,数百上千人声称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包围住火车头,有些人扒在车头前面的排障器上,有些人索性躺在轨道上。他们的目的是要制造铁路长时间中断的事件,以期引起各地造反派的注意,从而赢得声援。他们向孙安路宣传了一番最高指示和革命道理,便动蛮了,推推搡搡的,要把司机司炉撵下车关起来。刚接到发车命令的孙安路火了,使个眼色,与副司机司炉一起动手,把爬上机车的两个大汉推了下去,接着,便放汽。滚烫的汽雾朝着两边喷射,吓得那伙人四散奔逃。孙安路拉响汽笛,列车缓缓启动,卧在轨道上的人连滚带爬,车头前面的人则像下锅的饺子,纷纷往路基下跳。镇静下来,他们便朝着不断加速的火车开枪,连机枪都用上了,子弹嗖嗖地击打在火车头上。孙安路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