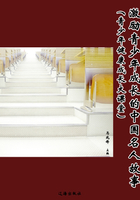秀是个伶俐女子。秀逗着女儿:小枣子,姑姑好吗?对,好!好在哪儿呢?漂亮。聪明。会唱歌,会画画。还疼枣哪。赶明儿,让姑姑给家里带个解放军叔叔回来行吗?
奶奶白了她一眼:漂亮能管饭?就你能!
奶奶即使生着气,见了秀,气也能消去一半。秀是奶奶在从浦口到南京的轮渡上拾来的。济南解放那年,奶奶仍在给人做保姆,主人家有个儿子是地下党,和奶奶小姑子的丈夫、铁道游击队的那个连长曾是战友。济南解放后,他成了政委,专门负责动员、组织年轻的铁路员工参加南下工作团。政委见一个寡妇靠做保姆、替人缝补浆洗居然能让儿子读到初中,很是感动,执意要带走十七岁的孙安路。他把孙安路留在自己身边做通讯员。算起来,孙安路当兵不过半年时间,大军打下南京,南下工作团一部分官兵便转到铁路工作。政委本来安排孙安路去学报务,可孙安路偷偷在政委写的条子上改了一个字,去学机务了。一当上司炉,他就写信要母亲来南京。奶奶乘坐的列车上了轮渡,扒着车窗,她看见下面有个脏兮兮、泪汪汪的闺女痴痴地望着自己。奶奶抹抹脸,又用双手小心地理理常被篦子篦得熨熨帖帖的头发,最后,正正后脑勺上的发髻。奶奶不禁疑惑了,问:闺女,看么呢?秀说:大娘,你带上俺吧!奶奶几乎是毫不犹豫,马上探身把手伸给了她。秀通过车窗爬上车。秀比孙安路小两岁,自懂事起再没见过父亲,只知道父亲在枣庄挖煤,年年托人往家里捎几回钱。可是,日本人走后,他不但没有回来,连音信也没有了,传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两个月前,母亲突然病故时,有个和她父亲一道被抓走的亲戚逃回村里,说秀父亲指不定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就在南京,要么成了解放战士,进军大西南去了。孤苦伶仃的秀为找父亲,沿着津浦铁路走了两个月。奶奶却认定,这闺女上辈子曾是她女儿,这辈子投错了胎,觉着错了,就来认门了。要不,咋说有缘修得同船渡呢;要不,咋见了就欢喜呢?
有乖巧的秀护着安芯,奶奶就不说女儿的事了。奶奶想念的,还是山东大葱:安路,你就不能托人捎来?
能行。可一程一程的,麻烦呢。得托济南的列车员带到上海,再托跑上海的,带回来。等以后有了直达车,让你天天大葱蘸酱!又不是么好东西,费这事,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奶奶不满儿子的方式,就是扭过头去,嘟嘟哝哝地唠叨:咋就不是好东西啦?你忘本啦。没有大葱,你能长得这么壮实吗,当司炉那会儿就把你累趴下啦。你起小不生病,就是爱吃大葱。有一年,多少孩子闹病呀,打摆子,老张的老二就是打摆子死的。那阵子担心死俺了,可你好好的。一顿能吃几棵葱,放的屁都是大葱味,咋还能闹病呢。你妹妹起小就病病歪歪,怨谁呢?不沾葱姜,做碗面放点葱花姜末,她都扔筷子摔碗的……
孙安路有些不耐烦了:好好,给你捎,给你捎个一麻袋来!让部队下次放电影的时候,食堂里尽是臭屁!
奶奶却笑了:俺就是想让那些山东小老乡记着这大葱。部队不是要走吗,指不定离山东更远啦。等台湾解放,还不都去了台湾?隔着大海,捎也捎不过去啦。
铁道兵医院那栋两层的红石楼房,上面有两条刚刚用石灰水刷下的长长的标语。一条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另一条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奶奶几乎每天都要牵着孙子、抱着孙女去食堂门口遛遛,她常在那儿指着对面医院的标语,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孩子。离开了那儿,她就一个大字不识了。
见儿子答应了她的要求,奶奶竟递去纸和笔。说:你忘性大。记着,顺带给俺捎上篦子,顶针,纳鞋底的锥子,捻轴,鞋楦,针,大小号都要,还有擀面杖,擀面条的,擀饺子皮的,都要,要枣木的。再带几个笤帚疙瘩,老张家的小气,只给俺一个,俺不稀罕,俺拿它扫脏鞋,俺自个儿买扫炕的扫面的!
当天晚上,孙安路就是把这张纸条掖进帆布工具袋走的。工具袋里还有三节的电筒、检点锤、腰形饭盒和司机手册。包乘组得提前两小时接班,接受调度命令,并在司机手册上抄下值班员交代的注意事项。然后,在车库上机车,司机进行制动机正常试验,副司机钻进地沟检查油润、补油,司炉则检查炉床和煤水柜的存量。趁着等机车出库命令的空闲,孙安路把纸条托给了同样来自枣庄的范站长。白白胖胖的范站长说:好家伙,干脆俺调二三十个车皮,你让老张派个车头,俺几个齐心协力把个山东省都拉来吧!
孙安路跑了这趟车回来才知道,他出门后,母亲突然记起他该歇班的,慌忙追出门去,幸亏遇见安芯,叫女儿堵了回来。于是,她便咒了一夜的张大车。秀悄悄对丈夫说:往后有个张大车好呢,张大车就是食堂门口的潲水桶,咽不下的气都倒给他,倒了心里也就痛快了。你说呢?
可是,那两天奶奶纳着鞋底,老是抱怨锥子不好使,拗断了好些针。她想给几个山东战士送布鞋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甚至让他们吃上山东大葱的心愿也没兑现。因为,大葱捎到的前几天,部队开拔了。放映员倒是没走,他调到525部队,留守西站票房对面山上的材料场。大葱便宜了放映员。他以馋大葱的名义,每天瞅空来一趟,一来二去的,就和安芯熟了。
临管处叫鹰厦铁路临时运营管理处。那里一共有五栋铁道兵留下的红石楼房,在盛产红石的合欢一带,它们可以算是红石建筑的代表作。砌墙的每块石头如同经过精心挑选,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平整,细密、均匀的錾痕,斜斜的,仿佛每根线条都测了角度。赭红的墙面看上去,整齐中富有变化,精雕细刻一般。当地石匠管修整石坯的工艺叫“洗石”,仅此一项就足以让几代石匠汗颜。
五栋楼房作“门”字形排列,中间是篮球场,两边各有两栋做家属宿舍,东头横着的成了单身宿舍。东头靠南那栋,就是过去的铁道兵医院。每栋家属宿舍建筑格局一样,两层,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里有八套房,挤着住了十来户。他们操着南腔北调。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孙安路一家三代,便分得一整套,里外两间带厨房。是做过医院的那栋,在中间的门洞。也就是说,他家厨房是挂号室,里外两间分别是换药室和注射室。
搬家的那天,孙安路难得地唱起歌来,唱的是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女儿拽着他的制服跟在后面,也唱。女儿两岁多了,还吃奶,见着秀,就拿歌声往她怀里拱。拱开了怀,却哇地哭了。
秀的奶头上涂着紫药水。奶奶早就催她该给孩子断奶了,秀觉着自己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每天又不上班,闲着也是闲着,就拿喂奶当工作了。听说可以搬出工棚,马上有了真正的家,奶奶就催得急了。秀当然知道,她是盼着再添个孙子。可枣儿恋奶的程度,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一个爱笑的小妮子成了一只狼羔子,不让她叼着奶头,她能嚎得岔过气去。奶奶给秀出主意,让秀抹红药水、紫药水,不行,贴上胶布,再不行,抹辣椒面,抹大蒜汁,让孩子怕了,断奶就成功了。
秀是架不住女儿哭闹的。孩子一哭,秀的一只手马上就伸进怀里,偷偷地擦奶头。孙安路递给她一条湿毛巾,说:行啦行啦,再喂一顿吧,不喂也浪费了。
奶奶气咻咻地说:没见过这样做爹娘的!说给你俩听啊,从前有个娘惯孩子惯的,儿子念书了,还不给断奶。有一回,孩子放学回家,他娘怕孩子饿坏了,抱着孩子就喂奶,让几个一般大的孩子看见,都笑话他,吃奶的孩子又羞又臊又恼,咔哧一口,把他娘的奶头给咬掉啦!看看。
孩子不吃,她还胀奶胀得疼呢。
忍忍就过去了。不断,奶多咱缩回去?
秀在用湿毛巾擦奶头之前,就手给丈夫擦了擦脖子,抱怨道:你这脖子咋就洗不干净呢,哪天俺把白衬衣染了!
孙安路搓着脖子,对奶奶说:好好,明儿开始断。抽棵烟,对你说个事。
其实,儿子一掏出烟,奶奶就知道有事了。平常,奶奶并不吸烟,可别人递给她,她也能吧嗒几口。她接过烟:把洋火给俺!
孙安路只顾抽烟。奶奶嘟哝道:还不比你爹那死鬼呢,三棍子打不出个屁,说事啊。
孙安路小心翼翼的:张段长人挺好的。打鬼子那会儿,他帮助游击队做了不少事,后来,参加抗美援朝立了功。听说他可勇敢啦,驾着火车跟美国佬的飞机捉迷藏,机枪子弹射进了他胳肢窝里,再偏个一寸就成烈士啦。
奶奶讥嘲道:咋不说那子弹是他媳妇,钻他被窝里去了?
孙安路后来就语无伦次了。他的意思大致是说,张段长对自己很爱护很关心,鼓励自己正确对待历史、对待组织,继续积极要求上进,高举三面红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多拉快跑。孙安路还闪烁其辞地透露,张段长表示他是孙家历史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