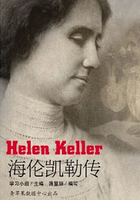但是,终明之世,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编制上一直是临时的,成员严格上讲也都有自己的本职,人阁只是一种兼差。而且,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在体制上并不隶属内阁,内阁领导它们,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依据,所以内阁和六部经常会出现摩擦。这个制度跟宰相体制最关键的区别是,天下的奏章不是先通过他们,而是由通政司首先送达皇帝那里,再由皇帝批交他们处理,处理完之后,再返回皇帝定夺,用朱笔按阁臣拟的意见批下去。这里,伺候皇帝笔墨的司礼监的太监(宦官),在皇帝比较懒惰的时候,往往会做些文章。所以,内阁的作用往往受皇帝个人性格与气质的影响,取决于皇帝对司礼监太监的依赖程度,更取决于皇帝对内阁成员个人的信任程度。当皇帝比较开明,或者说比较懦弱,同时对阁臣又比较信任,对司礼监尚能控制的时候,对公务处理往往大撒手,所有奏章到他这里只是过过手,例行公事,既没有多少“留中不发”的事情,也不会对票拟有更多的挑剔。在这种情况下阁臣就有点像宰相了,权势几乎跟宰相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像几朝元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世宗时的严嵩,神宗前期的张居正等都可以说是没有宰相之称的宰相,拥有类似宰相的权势,可以部分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反过来,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那么内阁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上面要受皇帝的气,或者将重要的奏章留中不发,或者对票拟百般挑剔;中间要受司礼监的气,怕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坏话。司礼监在实际掌握了批朱权之后,事实上变成了“立皇帝”(皇帝身边站着的皇帝),一举一动举足轻重,内阁往往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下面还要受六部等执行机关的气,只要内阁所受的“恩宠”稍衰,权力颇大的六部就有可能乘机刁难,不听招呼。
所以,内阁是宰相,也不是宰相,本质上依然是由于皇帝制度外的信任而私授权力的秘书班子。
2.司礼监的权势消长与明代的宦官专权
所谓司礼监,原本是宫廷宦官的一个机构,负责宫廷的礼仪宴飨等事宜,在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负责跟礼部和光禄、鸿胪寺等部门的协调。在司礼监的下面,设有秉笔太监,伺候皇帝的笔墨和茶水,原本只是皇帝的书童。正是这个秉笔太监,最后成为宦官专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明朝负责内宫事宜的机构叫内侍省,是管理宦官的衙门。由于下设机构主要是监、司和局,监的地位最高,每个监的主管称为太监,所以自明朝以后,宦官在习惯上被称为太监。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历代宦官专权原本是深恶痛绝的,曾经在宫中立下铜牌,上书宦官不许干政的禁条,而且为了防微杜渐,他还不许太监读书识字,并在实际的宫廷事务中,将太监严格限制在伺候人的范围之内,严格限制太监的数量。但是,朱元璋皇帝做得久了,对太监的依赖逐渐增多,太监的人数逐渐增加,机构也就愈发完善。建文帝继位后,一反其祖所为,对太监严加限制。但是永乐篡位以后,由于在战争中相当多的太监站在了他的一边,为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报,所以,自他起,太监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原来的种种限制逐渐化于无形,连那个铜牌也被偷偷扔掉了。
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历朝历代之最,开创了宦官制度上的奇迹。这种专权,跟历代的宦官专权有所不同,由于皇帝个人的信任和亲昵,导致宦官权力溢出,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制度性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明代废相以后,皇帝独揽全部行政权力,但又无法完全应付。在这种格局下,下面来的奏章是通过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里,再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者交给阁臣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用朱笔形式上誊写一遍,算是他亲自处理了。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一头一尾的关键环节。都要经过皇帝本人,皇帝一天不办公,整个政务就要停滞。如果皇帝本人懒惰,又不信任别人,那么身边伺候笔墨的宦官秉笔太监就有机可乘了。
明神宗朱翊钧是在老师张居正卵翼下,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事事都由张师傅摆布,朝政很有起色。张居正死后,反张的人们对张的诋毁和对皇帝的吹捧,唤起了神宗的“事业心”,他一面对死去的张居正追加贬斥,一面准备自己大展身手。可是,当他真的“乾纲独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事情也处理不好。他薄嫩的面子,使他不肯认输,同时也不甘心像前任一样,听任宦官做立皇帝,结果是采取了缩头乌龟的策略,干脆称病躲到后宫里不出来,导致全国政务二十几年停滞,所有朝廷重大事务没人理会,刑部大狱里装满了待决的犯人,朝廷各个部门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补,六部堂官仅剩四五人,原来五十余名的给事中,只余四人,原来百员的御史,只剩五员,连内阁也只剩下一个人。大员遭逢丁忧(父母死亡),不敢不去职,奏报数十,也没有人理会,只好自己走人。
跟有宰相的皇帝不同,即使仅仅誊写一遍,皇帝的工作量也相当的大,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日常的公务很多,遇有突发事件,公文更是堆积如山,加上朱家的后代往往比较懒,所以,免不了要让在旁伺候笔墨的太监代劳,让他们替自己誊写御批。开始的时候,太监代笔,皇帝还在边上看着,久而久之,就听任太监自己干了。开始是票拟偶尔出现错漏字,批朱的时候可以改动,后来则随意添改,发下来都是皇帝的旨意,谁敢怀疑。刘瑾做秉笔太监时,居然经常把奏折拿回家去,找几个狐朋狗党一起商量后再批答。(《明史》卷304《刘瑾传》)就这样,司礼监(主要是秉笔太监)就获得了批朱权,与内阁的票拟权遥遥相对,但是,批朱权显然要压过一头,因为批朱后的奏折,就是法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其中,秉笔太监的作用举足轻重。明朝的大权宦,如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秉笔太监出身。时间长了,由于秉笔太监的地位突出,司礼监的实际负责人就改为秉笔太监,而且机构也逐渐扩大,权力越来越大。这个机构逐渐发展为收发奏章、传宣谕旨、掌管东厂,以及干预司法、后妃选择、监控地方和军队、留都守卫、管理皇室收支(包括包揽地方工商税收),几乎无所不管。
明朝皇帝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普遍地不愿意见大臣。宣德以后,甚至连内阁成员都很难“一睹天颜”,于是,司礼监太监又得了一项特权,就是传达皇帝旨意,有的时候是笔谕,有的时候是口谕,而越到后来口谕越多。往往是太监们口衔天宪,随意添改。开始还是秉笔太监亲自到内阁或者六部传旨,后来干脆派个小太监到内阁知会一声就完了。
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次彗星出现,大臣们纷纷借机上奏说是因为君主阻隔,大臣们见不到皇帝缘故。宪宗不得已安排见了一次内阁成员,但相见时皇帝一言不发,待大臣三呼万岁后即离去。周围太监们说,时常不闻召见,好容易见了只听到呼万岁。后来,人们称内阁为“万岁阁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
由于长年累月见不到大臣,皇帝的猜忌心只能越来越重,于是开始依赖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有时还设西厂),对朝臣加以控制。东厂和锦衣卫事实上已经合流,统归司礼监掌握。它们一方面刺探朝臣的所谓不轨言行,一方面可以自行对朝臣逮捕关押。凭借这个特殊镇压渠道,司礼监的权力往往可以达到令天下战栗的地步。
同样由于猜忌,皇帝往往派太监去监视地方和军队,最后发展为矿监、税监、盐监和珠监(对采珠地方派出的太监),这些人干脆直接搜刮工商,为自己敛财。更加危险的是,派出的太监居然可以在仪式排位上压过官员一头,这事实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体化上升,可以公开地主宰朝政。
在这种情形下,中枢决策中心的内阁与司礼监这双轨机构,权力的不平衡是决定性的。即使在内阁尚能比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阁臣也需主动与司礼监搞好关系,比如张居正就与秉笔太监冯保,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皇帝比较昏庸,特别依赖太监的时候,内阁则完全被司礼监所压倒。前面提到的刘瑾,不但将奏章随便拿回家批答,而且写完了之后拿回来让阁臣焦芳为他润色,而首辅李东阳对此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已经变成了司礼监的附庸和工具。内阁与司礼监,此消彼长的势头是一边倒的。据说嘉靖年间,有个太监说过,“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808页。)。这番话很生动地说明了太监与内阁势力的消长。到了熹宗年间,朝臣全都沦为司礼监的奴才,稍有自尊者不是被迫害死,就是弃官归田,赋闲回家。满朝文武,争相当魏忠贤的干儿干孙,连王公贵族,见了内监都要回避。依附魏忠贤的大臣,文则有所谓的“五虎”,武则有“五彪”,再下则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党羽,“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同上书,809页。)。当然,赵翼说得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明代的宦官专权,虽说非常可怕,但魏忠贤即使号称九千岁,遍地都是他的生祠,但以一个残缺之躯想要做皇帝,可能还是有点超乎他和他的党羽的想象。明代宦官虽然权重势大,但经过理学多年浸润和皇权的神秘化熏陶,朝中人无论士大夫还是宦官,要想篡位都有巨大的心理障碍。宦官的权势,说到底,都是皇帝给他们的,他们只是附在皇权大树上的藤,很难有意识去对抗皇权。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野布满魏忠贤党羽的情况下,一个以藩王入继大统的崇祯帝,才几个月,就能把魏忠贤扳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