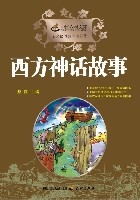只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狂热,跟五四运动一样,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动。握有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里,反映的还是相对开化的江浙农村,如果到了内地,情况还要令人泄气。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分子,大力度鼓荡文明,但连作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标志的男人头和女人脚,都很难改观,即使强悍的革命军,也只能在城里给进城的乡下人剪辫子,断然不敢冒险下乡去动剪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民变,再来一次清朝入关时的嘉定和江阴式护发(辫)抗争,也未可知也。至于给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缠足,更是收效甚微。开明女人文明脚的示范,仅仅是人们的笑柄。当时的民谣,没有歌颂革命的,反对“文明”的却有不少: “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是讽刺剪辫子的,时人把剪了辫子的人都讥为和尚。“你说邪不邪,娘们儿穿着爷们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是讽刺放足的。正像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那样,农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龙庭,但却在意自己头上的辫子。抵抗文明,比维护皇权更起劲儿。
跟农村的人们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对于革命或者不革命,进而对于共和或者帝制反而更在意。当家的袁世凯日趋保守,祭天祭孔,强调尊孔读经,连官衔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后看,着眼的是帝制的恢复,不过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连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复大清的旗号,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戏。搭完了台,戏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价,传统掉了价。
因此,当五四运动再一次鼓荡西化的时候,虽然林琴南之辈特别希望伟丈夫荆生,也就是段祺瑞的爱将和谋主徐树铮出头,将覆孔孟,铲伦常之辈一鼓荡平,但徐树铮毕竟没有介入,反传统依旧没有深入农村,但社会对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却微弱了许多,听任白话文占领学校,听任西方的学科体系,扫荡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曾经的体育课
现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体育课基本上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课,跟升学没有关系。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呢,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而已,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的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裤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掖吧掖吧,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儿鼓,还是蛮精神的。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儿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扛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只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儿行进。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不应该缺乏才是,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可惜,这套鬼子操练法,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孙子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乎,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满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儿,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但是,清朝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的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儿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惶惶,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扛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谎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体育课变成兵操,原本是为了给官办的新教育摆样子,而摆样子是一切官办事业的共性,只是,清朝末年学堂里的摆样子,却无意中帮了官府的对头,看来,古今一理,凡是摆样子的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欢摆样子的人,一辈接一辈,这个道理,死都不会觉悟的,觉悟了也没用,还是要摆样子。
奴才的创造性
一次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胡扯,谈及创新性国家这个话题,我随口说道,没听说过奴才有创造性的。有人不服,认为我看不起奴才,有种族歧视(严格说应该是族群)之嫌。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如果碰巧是个能工巧匠,碰巧有条件,也许能有创造性,但是一般我们说的奴才,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一般我们所说的奴才,都是指家里的下人、仆人。这样的人,就是有创意,也无非表现在如何揩油上,买菜买贱报贵什么的。这一点,晚清和民国在华的外国人,印象特别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特别用的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有一阵皇帝感觉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来说,即使在上者权威再大,禁人这个,禁人那个,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独禁止不了下面人的低声下气,自我贬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只好听任满人一口一个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实,满人这样的自称,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汉人自称“臣”,满人如果也称臣,那不就没区别了吗?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意思里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能打能骂,贱称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个狗子、驴蛋什么的,说明彼此关系不寻常。汉人的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汉臣们,其实特羡慕满人这种自称,可惜几个胆大的,冒险试了一试,热脸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头土脸。别的人就不敢再试了。因此,汉臣只好称臣如故。这个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也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下了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不希望他们提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那么,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好像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大印,汉人主文稿,也就是说,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方面大员,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臣子最高的评价,还是“会办事”。在老佛爷眼里,即使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不过是会办事而已。正因为如此,为我们某些大人物特别看好的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就像《红楼梦》里探春等人三驾马车当家,下人请示办事,不懂事的李纨,下人说什么都照样批准,而聪明的探春则一律让查以往的旧例。这种聪明,就是奴才的聪明,照既定方针办,不出错。只有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儿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200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应,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写了好些让人快乐的文字,但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儿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原本就跪着,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儿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呆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的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因为别人想不到)。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儿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 “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 “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是最发怵的,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