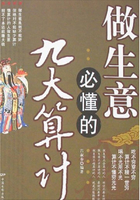大夫人道:“你是龙九?”
“是。”
“为阿浔而来?”
“是。”
“要见我也容易,先跪下!”语声仍是冷冽无情。
寒烨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要求未免太过分。
他心中的九爷,不跪天不跪地,戎马生涯时,亦不曾跪过天子。
丞相夫人,一度风光无限是真,可若真论起来,她着实受不起九爷一拜。
与寒烨一样,萧珑、东方睿、宅院中的下人、龙九的手下,目光全部凝注在他身上。
萧珑凝视着那道如枪似剑的身影。
母亲堂而皇之的命令,一如他先前所言,荒谬。
他可以在生死关头只护她平安,却不见得能屈膝下跪。
因为母亲只是她的长辈、至亲,不是他的。
因为他是连同门手足都可漠视、囚禁的男子。
他对她的那些在意、迁就,不足以成为他在众目睽睽下低头的理由。
她知道自己该在他给出反应之前劝说母亲收回成命,或者立刻跳起来拉走他。
但她没有。
她只是明白,此时此刻,她做什么都没用。她不能左右母亲,亦不能左右龙九。
她以为,龙九会出言周旋;她以为,龙九会嗤之以鼻,拂袖离去。
可他没有。
手势优雅地撩起锦袍,屈膝,缓缓跪倒,微微低头。
他缓声道:“龙九拜见夫人。”
语声沉冷,毫无恭敬。一如他即便下跪,还是让人觉得孤傲。
大夫人的惊讶不亚于任何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之后,龙九缓缓起身。
起身之际,大掌拂过萧珑脊背。
“你这……”萧珑身形一软,倒在他臂弯。
她想说的是:你这混账!
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出人意料有机可乘?
阿福立刻唤来一名丫鬟,笑眯眯地道:“将大小姐送到九爷帐中?”
龙九颔首。
那名丫鬟是先前服侍容老庄主的人,身形高大,很有些力气,接过萧珑,抱起来就走。
“放肆!”大夫人手掌拍在桌案上,险些按捺不住火气冲到院中。
龙九却唤来寒烨,指了指一旁的药碗。
寒烨会意,去询问之后,找到几包草药,细细查看药材。
随即,龙九转身端起药碗,走进厅堂。
一脚跨进门内之时,三枚银针挟带疾风而来,分刺他眉心、咽喉、心口。他抬了抬手,迫人的煞气在同时消散。
大夫人凝眸再看,三枚银针已经在他指间。她脸色愈发苍白,眉间尽是怒意。
龙九似未发觉,安然落座。
“是我纠缠阿浔,追寻至此,夫人若要责怪,也该怪我。”
这是他第一句话。
大夫人挑眉,语调却已平静下来,“如此说来,我竟不能责罚膝下不孝女?”
龙九抬眼,稳稳对上大夫人视线,“我看不得,不允许。”不容置疑的语气。
这句话若是换了任何一个人说,都会让大夫人觉得可笑,可由他说出便是不同,非但不觉得好笑,甚至觉得有压迫感。
他不允许的事,若是谁做了,就是与他为敌——他没有说出这一点,并不代表大夫人不能想到。
龙九沉了片刻,道:“四年前天子赐婚,不论事后如何,在当时,夫人不同意那门亲事。如今阿浔流落江湖,我有意娶她,不论阿浔心意如何,夫人似乎也无意成全。”
大夫人先是意外,因为并没料到他已知道她们母女的底细,随即点头承认:“我不同意,宁死也不同意。你既已知晓阿浔先前要嫁的是怎么样的人物,今时就该想到,我断不会同意她作践自己与草莽为伍!”
龙九垂眸,敛去眼中嘲讽才道:“我只是不明白,夫人如今视自己为何人,又视阿浔为何人?”
大夫人脸色一僵。
而龙九的本意却非要她难堪,他继续道:“夫人要阿浔嫁给什么人,龙九就是什么人。我只请夫人不再为难阿浔,由她定夺嫁娶之事。”
话不多,却暗藏玄机。
大夫人反反复复打量着他,目光犹疑不定,之后凉薄笑道:“你可明白,我罚阿浔,不是因为你有心娶她,而是因为她不自重,与你闹得满城风雨。便是由她自己定夺,她也不会嫁给谁。”
龙九勾唇微笑,笑得意味深长,“若她无心,是我的命,我不勉强。而眼下,分明是有人要她心如止水。”
大夫人无言以对,半晌才冷冷笑道:“自进门来便句句诘问,既是如此,方才又何须下跪!”
“夫人养育阿浔多年,龙九理当跪拜。”
你养育了她,所以我尊你敬你。感谢你养育了让我倾心的女子。
而你惩罚她,所以我不留情面。我不能容忍谁对她苛责或惩罚。
前因后果,不过如此,都是为她。
此时,萧陌自西厢房内走出,观望东侧正在建造的宅院许久,才款步走到厅堂门外,听到了龙九告辞之前的话:“来日,阿浔于我,或得,或失,自当再对夫人拜谢。”
萧陌的笑意一闪而逝。
龙九出门时,她凝眸相看。
未见过这般冰冷的男子,亦未见过这般目光冷静睿智的男子,更未见过比他更俊美优雅的男子。
“我的阿浔,也只有这般人物配得起。”萧陌如是说。
话是让大夫人听的。
龙九脚步未有迟疑,阔步离开院落。
穴道自动解开之时,萧珑醒来,之后便又懊恼地翻了个身,继续睡。
一来她是真的倦了,之前在母亲寝室外站了整整一夜半日——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将就着睡,却还没修炼出站着也能入眠的本事。
二来她是觉得无颜面对几位亲人,还不如睡死过去来得痛快。她虽然没看到龙九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却能确定,他一定会让母亲怒火中烧。
是以,她再次醒来时,已近傍晚。
睁开眼便看到龙九坐在身侧,她用膝盖碰了碰他,“没闹出人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