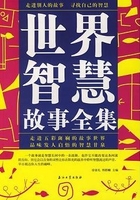发现铁床架子上刻的字纯属偶然。我撩起双层的褥子,久久地端详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留言:也许这是老子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曹旋。不用说,这个曹旋大概就是死在我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上,只是不知他死于什么病。
把视线转移一下,我又找到了一行字:1989年2月28日何季伍绝笔。字迹很浅,不仔细看,就无法看清楚,一笔一画间透着绝望和无奈,那显然是用水果刀刻的,可是握刀的手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而且颤颤巍巍的。
最后,我看到的那一行字简直让我惊呆了,心头突然涌上了一股寒流,“我不愿意再跟病魔缠绵了,我准备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984。”这些大小不一的字,很粗,大概是用吃饭的叉子刻上去的,每个字都像是拿凿子凿上的,笨拙而凶狠。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何许人也,他的脾气,他的秉性,他是采取什么极端的手段来了结他痛苦的一生的。我找来迢迢,跟她打听,她摇摇脑袋说:没听说过病房里发生过自杀事件,再说了,1984年我还小着呢。
我搔了搔后脑勺,看来,打算从迢迢这里得到点什么军事情报,简直是痴心妄想。她的心思压根儿就没在这儿,而是在她那坍得一塌糊涂的爱情废墟上。你的爱情历程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我只好把注意力从刻在床上的留言转移开,关注起她来。
她的两只眼睛像流星一样的闪了一下,又黯淡了下来:没有进展,一点进展也没有,我都懒得再提他了。迢迢耷拉着脑袋,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同情。
你不是正在跟你爱的人交往吗?我叹息一声,一屁股坐到床上,床上的弹簧吱吱作响。其实,我用不着再问,她的饱含忧郁的眼睛就已经告诉了我一切的一切。
那不叫交往,那叫通奸,那叫鬼混!迢迢竖起眉毛愤愤地说,他一点也不爱我,却又要跟我上床,上床还不算,还要把我们在床上的丑恶表演一一录下来,靠。
他这么变态,我见她像一匹呼哧呼哧打着响鼻的马儿一样,两腮抽搐着,不禁问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我下贱呗,我总盼着他有一天良心发现,会真诚地接纳我,可结果,哼!迢迢那张红扑扑的、有少许青春痘的小脸,流溢着绝非做作的屈辱表情。
你跟他摊牌时,他是怎么说的?我掏出烟来,点上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我没敢跟他摊牌,她不好意思似的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说道,我怕我一旦提出要他娶我的要求,他拒绝了我,那怎么办?我就彻底地没有指望了……
这么说,你糊糊涂涂地跟他睡了,却至今没跟他摊牌?我有点哭笑不得,舌尖在嘴唇上舔来舔去,尽量控制着自己别说出过于刻薄的话来。
我知道你要骂我什么,还是给我留点面子吧,不说的好。迢迢也从我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颤颤巍巍地抽了几口,不住地咳嗽起来,我知道,她平时是不吸烟的。
好了,不会抽就别抽了!我伸手把她嘴上叼着的香烟夺过来,丢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不满。
迢迢腾地站起来,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出了病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
听见门板砰地一声响,我这个忧郁症患者的症状又显露出来了——立刻后悔了,为自己刚才对她的恶劣态度。我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我觉得憋得慌,仿佛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于是,赶紧解开衬衣的领扣。
突然,迢迢又折了回来,从门缝里探进了脑袋。我今天晩上就跟他摊牌,既是给你,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她说。我发现,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的眼睛塌陷了下去,两只塌陷下去的乌黑眼珠闪着寒气逼人的目光。
她显然是个迷路的人。
那么,我呢?
听着迢迢的脚步匆匆远去,我仰面倒在床上,脸色变得煞白,额上也渗出了冰凉的汗珠子。我尽量不去想迢迢的麻烦事,却无法制止自己不去想翩翩,枯坐在那里,活像一个戳在庄稼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直到西西回来。
天都黑了,你怎么也不开灯呀?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