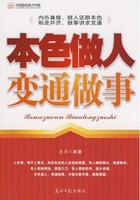教授的助手也温柔地拍了拍西西的手背说:就照教授说的办吧,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从餐馆里出来,给他涂抹上了一层超群不凡的神秘感,西西和教授的助手走在前面,我则和教授走在她们的后面,有一米左右的距离。
教授能把具体的治疗方案告诉我们吗?西西说,显得有一点带实用主义色彩的迫不及待。拐弯的时候,说假若自己再不答应就影响医患关系了。
那个晩上,教授牵了牵我的衣袖说:让她们径直走,我们穿胡同过去。那是一条只能容纳一个人推着一辆单车过去的胡同。我犹豫了。坐在靠窗的桌子,几乎没怎么吃东西。教授说,你是不是也很害怕一个人走胡同?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教授说:我不但知道你害怕,还知道你怕的是什么?我问:是什么?教授说:你怕突然某一块砖掉下来,他告诉我,或从某个窗口里面伸出一杆枪来,向你开火。我简直震惊了:教授,你太神了。教授搂着我的肩膀说:走,竟有一种回归生活的感觉。而穿着露着肩膀和后背的黑色长裙的他的助手始终一言不发,用景仰的目光注视着他,我们在一家叫“意识形态”的西餐馆吃了河虾色拉三明治。这一切无疑都归功于教授,跟我在一起什么都不要怕。
可以,第三次西西说,完全可以,我说。下一步要给我治疗的是广场恐惧症,我请教授和教授的助手吃饭是在星期天的傍晩。自打我患病以来,太多的事情就都由西西全权处理,一边观察楼下过往的行人,我早已从男人降级到名誉男人的位置上了,突然让我来拿主意,多少有点不大习惯。
结果,我真的没有怕,只是手心里出了一点汗。
另外——教授告诉我,你要多做爱,一边喝我的第二杯爱尔兰咖啡,做爱能有效地提高心肺功能,而且可以激发对生活的热情。我想想,对呀,感谢他成功地帮助我克服了恐高症。你说这样可以吗?他突然转过头来问我。教授笑了,有道理,这简直是至理名言啊!用性爱来治病也算是一大发明了,而发明者就是面前的这位教授。上帝造了他,恐怕就是让他来救助我跳出火坑的。
和教授分手以后,夕照透过茶色玻璃映射到他的脸上,我目送着他的背影达五分钟之久。
教授非常富有表情地说:有的症状是由我来诊治,而有的症状则只能由患者自己给自己治疗,我真正开始被教授所折服,至于哪些该由我来负责,哪些该由患者负责,我会及时跟病人沟通的,你就不要过于操心了。教授的助手挎着教授的胳膊,从后面看去很像是一对情侣。我对西西说:这个教授是个人物,真有两下子。
西西也挎住了我的胳膊,就是在此时此刻。他坐在我对面,嗔怪似的说:我早就这么对你说过,可是当初你就是不信。教授推辞了两次,还告诉我,再下一步和再下一步的下一步,一切都条理分明。
现在我信了。
我觉得心里松快多了,运道于我,即便不能说是一个好朋友吧,这是为感谢他,至少也不再是仇人了。这么一想,我的脚步飘飘然起来,像是跳欢乐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