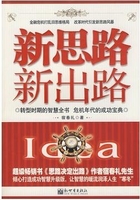傅恒回到京城时,身边只有詹姆斯一个洋人。
到了成都,岳钟琪说老毛病犯了,也不知道是真病还是假病,怎么也劝不住,打了辞职报告就回乡下老家去了。他的那些亲信自然也不愿意跟在傅恒屁股后面,一个个都溜了。回京城的路上,傅恒身边只有詹姆斯一个人,一点儿也不像凯旋的样子。两年前他踌躇满志地离京出征时,那是多么的威风,十六万将士从全国各地向他靠拢,加上岳钟琪手下的三万将士,他手握近二十万的大军啦!现在终于凯旋,回京城的就只有他和一个外国人,谁信!
傅恒能够交给皇上的东西就两样,岳钟琪的辞职报告和雍忠拉顶寺堪布送的神舞面具。松罗木自焚了,羁押松罗木的任务没完成。
皇上本来想对傅恒说几句嘉许的话,毕竟战争结束了,企图覆盖紫禁城的松树化为灰烬,可是心里一点儿也不爽,竟涌动起一股怒潮,差点骂出声来。他离开龙椅,背着手踱来踱去。虽然战争结束了,向皇太后有了交代,可是,事情办得一点儿也不漂亮。怎么就没把松罗木给捉来?花这么大的代价,不就是为了亲眼看看想遮住紫禁城的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吗?现在说自焚就自焚了?实在不过瘾,实在不过瘾得很啊!这个岳钟琪也是,给脸不要脸,不拿太子太保当回事,什么玩意儿!
傅恒正襟危坐,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皇上还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阵后,若有所思地在傅恒带来的面具前停住脚步,把面具拿在手上看。他记起来了,它就是当年乞僧戴的那副面具,难道乞僧真的就是雍忠拉顶寺堪布?当年堪布为何装成乞僧?现在又为啥捎面具来?难道想提醒当年的事?当年又发生过什么事?皇上边抚弄面具边想。
傅恒仍然大气不敢出一口,眼睛怯怯地看着皇上来回踱步的影子。
皇上把面具放回案几,又背着手踱步。
想起来了。当年,乞僧手上牵着一只山猴,口中唱道,“小小山中猴,怎会称霸王?若要称霸王,身肥拖你瘦,身瘦拖你死。”唱了一遍又一遍。当时自己放下架子挽留他住宿,乞僧不理不睬,向牵在手里的山猴说:“今天你也见了主子,休要怪他。说你称王称霸的是他的奴才……”
“山猴,山猴!”皇上站住,喃喃道。
傅恒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不知道怎样应答,屏着呼吸,勾着脑袋,如坐针毡般难受。
“它叫什么?”皇上把面具放回案桌上,指着它问。
“琼鸟神舞面具。琼鸟是他们的守护神。”傅恒低声回答。
“守护神?!”皇上一巴掌把面具扫落地上,几乎同时吼叫道:“这个秃头,敢教训朕!捎这个破玩意儿不就是劝朕当守护神嘛,难道朕是魔鬼?刽子手?”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傅恒鸡啄米似的一阵磕头,怯声说:“堪布捎面具的用意或许是表达皇上和守护神一样。”
“朕是天子,守护神能与朕相提并论?”皇上听了傅恒的恭维话,虽然嘴里这么说,但气明显消了一些。捋了捋龙袍,坐到龙椅上,握着的拳头“咚”的一声落在扶手上。
“臣罪该万死!皇上是苍天之骄子,万物之主宰,小小守护神怎能与皇上相比!”傅恒又一个劲儿地磕头。
“好了好了,能不能消停一会儿?”皇上很不耐烦地晃了晃手。尔后,突然把上身向前倾了倾,问:“烧啦?”
“烧了。”傅恒慌里慌张地重复了一句皇上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烧了什么。
“啊!”皇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火克木,天意!”
“皇上英明!”傅恒也偷偷地呼了一口气,皇上终于绕过弯子消气了。万一这弯子一时半会儿绕不过来,别的不说,傅恒断定首先他的脑袋会从肩上卸下来。
“要不,看看蛮女歌舞?”傅恒乘皇上心情好转,小心提议。
“也好,你不提我倒忘了。”皇上轻轻点了点头,转而正色道:“她们,还有那些匠人,落户扎根休养生息便好,不可视作俘虏亏待!”
“吾皇仁慈,喳!”傅恒唱喏领旨。
第二天早晨,皇上穿了便服,只带了傅恒和几个贴身侍从秘密出宫,向香山骑马走来。
冬天的香山不像山下的京城,虽然红叶不见了,但依然满目青绿,令人神清气爽。皇上兴致渐高,虽然年纪不小了,精神依然抖擞,一点儿也不觉劳累,一路欣赏风景,走到山上的黄寺才下马休息。
黄寺院子不大,进寺献舞的美女只能容下几十个,被选中的恰好是阿果和她的姐妹们。皇上看见美女们,眼睛一亮,龙心大悦,他没见过这种气质的美女。江南美女娇嫩甜润得过分了点,塞北美女又重了些男人味,而眼前的美女们刚而不硬,柔而不弱,天生丽质,自成一美。皇上当然不知道这些美女是由嘉绒藏区特有的阳光、雨露和空气造就的。
皇上发觉美女们的舞蹈服饰和穿法也很特别,别人服饰只穿一套,她们穿三套,随着舞蹈的进展一套一套地脱,充满神秘、诱惑和悬念。最外面套一件黑白相间的披风,英姿飒爽尽显。披风撒手一抛,大襟宽袍露面,体态顿显雍容,气质随之高贵。褪去长袍,色彩艳丽的紧身长袖衬衫和百褶长裙飞入眼帘,雍容高贵刹那间幻化为婀娜多姿。
美女们跳的是献帕舞,这种舞蹈风格古朴,气氛庄重,舞姿典雅,最适宜今天的场合。美女们并不知道皇上在场,跳舞没有任何拘束,跳起舞来十分投入。她们离开家乡两年多,特别思念家乡,一跳锅庄便好受些。领舞的阿果对献帕舞更有特殊感情,献帕舞是东女国时代的宫廷舞蹈,阿妈又亲自改编过。阿妈跳献帕舞时总是把手上的帕子献给阿爸,离开嘉绒藏区这么久了,她思念阿爸阿妈,她还不知道阿爸阿妈已经与官寨一道化为青烟飘散了。跳起献帕舞,眼前就出现阿爸阿妈跳献帕舞的影子,就可以和他们在一起。
献帕舞的舞姿变化多端,穿着披风跳时,先是转圈踏步吟唱古诗,牵手跨步慢舞;尔后展开披风挺胸塌腰跃进,旋转使披风扩散成荷叶状,舞曲高亢激越,将古代东女国英雄们出征的场景烘托出来,极富感染力。穿着长袍跳时,舞曲热烈亢奋,美女们手捧洁白的哈达,舞形变成莲花吐蕊状,把手中的哈达献给来宾们。在古代,献的是帕子,由在家的妇女们献给出征归来的勇士们。哈达献毕,美女们褪去长袍,露出花枝招展的百褶长裙,舞曲顿时欢快起来。急促明快的节奏,富于变化的动作,将美女们的绰约风姿展示得淋漓尽致,庆祝胜利的喜悦感染着每一个人。
皇上对舞蹈只看了个隐隐约约,舞曲也只是在耳畔萦绕而已,他的魂被领舞人勾去了。领舞人身上好似牵出一根无形的丝线,把皇上的眼睛牵住,她往哪里飘移,这双眼睛便跟着转动,随从们第一次见皇上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不过,他们自己都已如痴如醉,不成体统了。领舞人的美不能和其他女人的美相提并论,她似乎从天上来,不带一点儿凡俗气息,是国色天香的那种大美。肤色的黑白、个子的高矮、体态的胖瘦,已经毫无意义,无论以怎样的状态出现,都影响不了她的大美本质。她浑身上下包括每个毛孔都蕴涵着一种天仙神女的风韵,这种风韵无须酝酿无须造作,自然天成,与生俱来。从舞袖踏步展臂扭腰的舞蹈韵律中流露出来,从开口闭口、眨动睫毛、扇动鼻翼、举手投足之间释放出来,从头发的光泽、脸鼻的轮廓、嘴唇的线条、纤长的手指上面表现出来,甚至在绣花叠帕的针脚里、叮当作响的耳环上、舞蹈服饰的皱褶间、腰带彩穗的飘摇中,都似乎蕴涵着这种风韵。献哈达时,阿果正好碰上皇上,尽管她并不知道。阿果双手托着长长的哈达,弯腰低头举到皇上面前,口中吟唱吉祥颂舞曲。皇上闻到一股淡淡的柏枝香味,心旌顿时荡摇,接哈达时情不自禁地顺势捏住阿果的手:“叫什么名字?”阿果轻轻抽回手,微笑了一下,答:“阿果,”又微微鞠了一躬。皇上十分欣赏阿果刚才不卑不亢的应酬,对她更加上心了,更加觉得这辈子没去巡访西南是此生一大遗憾。
阿果被傅恒将军收为干女儿是在皇上去了香山后的第二天,很突然,也很意外。傅恒将军不知道香雪是谁,皇上说就是那个领舞人,他才知道指的是阿果。香雪?对,这个名字取得好!傅恒从香山把阿果领回来时也闻到了阿果身上的柏枝香味,同时想起去大色齐部落受降时漫天飞舞的白雪,白雪吉祥。
“你叫香雪了。”让阿果换上满族服饰后,傅恒满意地端详着说。
“衣裳换了,名字也换呀?”阿果说。
“要换,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女儿,是满人了。”傅恒认真地说。
“满人?满人是谁呀?”阿果从来没听说过。
“皇上是满人,我也是。”傅恒让阿果坐下,自己也对着阿果坐下,神秘地说,“皇上要册封你为妃子了!”
“皇上?真的?你再说一遍!”阿果激动得满脸绯红,站起来搓手摸脸,“他……皇上怎么知道我?”
“闺女,真的是这样。”傅恒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抚摸着阿果的秀发,“皇上和你说过话呢,忘了?”
“说过话?没有啊!”阿果眨着漂亮的眼睛,不停地晃脑袋。
“忘了?”傅恒笑着说,“昨天在山上跳舞时,接你哈达的人就是皇上。”
“他?”阿果吃了一惊,伸了伸舌头,“我还没叩拜呢!”
“皇上一回来就决定册立你为妃子了,”傅恒说,“妃子不能是外族人,才绕一个弯子,先当我的女儿,变一下身份。”
“好,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怎么变都行!”阿果高兴地转了一个圈儿,又若有所思地说:“非得叫香雪不可吗?阿果是阿妈取的名字。”
“香雪是皇上叫出来的呢!”傅恒突然肃穆起来。
“哦!”阿果红透了脸,耸着肩长长地伸了伸舌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