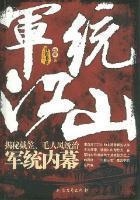举行拴头仪式的日子是雍忠拉顶寺堪布亲自选定的,那天确实是一个好日子,天一亮就飘起雪来,纷纷扬扬的白雪就像天女散花。岳钟琪精选了十一名亲信,加上他和傅将军,十三乘坐骑行进在通向大色齐部落的山道上。这是一条除了商道以外进入大色齐部落的唯一通道,战争发生后,商道不通,只能走这条路。这条路正是著名的噶尔崖山道,路在悬崖腰间,上面千仞绝壁,下面万丈深壑,山道九个关口,个个都是鬼门关,张广泗的两位爱将和五千人马就葬身于此地。如今就不同了,岳将军人马一到,关口立即敞开迎接,守兵们低头躬腰站立路边,温顺得像绵羊,各个关口逐一顺利通过。这时傅恒将军才恍然大悟,当年京城童谣中唱的“一条独龙九道关,九把铁锁锁大门”就指的这条山道和九道关口啊!“张果老汉前去砍,砍烂神斧丢一边,王母娘娘派哪吒,碰断火轮门外边,八百罗汉去砸锁,件件神器弄稀烂”等句中的张果老汉、哪吒、八百罗汉分明是指张广泗、讷亲和阵亡将士的隐语,只不过阵亡的将士何止八百!当年疯和尚说的岳十三,不就是指的今天咱们这一行十三乘骑吗?
松罗木主动投降,两三年打不穿的噶尔崖,十三乘骑只三四个时辰就昂首走过。正如京城童谣所言,钥匙一到铁锁开,砍树不愁神功来。走过噶尔崖,下一道陡坡,再穿一条峡谷,前面就是大色齐盆地。松罗木和大色齐部落所有的头人、寨首早就恭候在这里。他们手里牵着马,排成一行,辫子解下来,一律垂在胸前,神情十分肃穆,这是拴头的意思。十三乘骑下了马,松罗木一眼就认出岳钟琪,把手里的缰绳递给旁边的人,跑过去给岳钟琪献哈达,把自己的额颅顶在岳钟琪的前额,行碰头礼。
“飘雪了,吉祥!”松罗木说。
“飘雪了,吉祥!”岳钟琪回了一句。
“傅将军辛苦了!”松罗木从旁边的侍从手里拿过一根哈达,举过头顶,献给傅恒将军。
“幸会,幸会!”傅恒将军拱手回礼。
傅恒接哈达时,想起大象踩跳蚤的故事,心里酸酸的。抬头一看,眼前站着的人可不像跳蚤,牛高马大,浓眉大眼,鼻端口方,气宇轩昂,确实不同凡响。而且,他的手更不一般,手指间长着薄薄的蹼,鸟爪似的。
松罗木向其他客人都献了哈达后,所有人都骑上马背,向大色齐部落快马前行。
“皇上不是改了名字吗,怎么还叫松罗木?”傅恒在马背上小声问岳钟琪。
“听说都叫惯了,改不了口。他把索罗木的名字送给儿子了。”岳钟琪说。
“此人一直想拴头,”傅恒说,“为啥征讨他们?”
“我也不知道,还想问您呢。”岳钟琪说。
“我又问谁?”傅大人疾首蹙眉,他曾经想到过这个问题,想过之后就没能再细想下去,因为整个过程显得不合常理,缺乏逻辑关系。
“荒唐!”岳钟琪失声笑了,是无可奈何的那种笑。
傅大人猛然转过脸瞥了一眼岳钟琪,欲言又止。
白雪仍在纷纷扬扬地飘洒,像千万张放飞的龙达曼舞,更像千万只白鸽翩翩飞翔。
“他的手怎么会那样?”傅恒想起了松罗木手上的蹼。
“有两个人是那样,另一个是他哥哥,雍忠拉顶寺堪布。”岳钟琪说。
“怎么会那样?”傅恒觉得很奇怪。
“神子。”岳钟琪笑了一下,“都说他们兄弟俩是琼鸟的儿子,琼鸟是嘉绒藏区的守护神。”
“神子?鬼话!”傅恒话虽然这么说着,却想起了官兵遇到的一连串怪事。迷魂沟失踪,沼泽部落牦牛发疯,菩萨沟突发洪水,宝伞山猛兽袭人……觉得发生的这些事儿确实有些蹊跷。
大色齐部落官寨远远就能看见,像一棵古老的大树,兀立于村寨中心。这是一件杰出的石头建筑艺术品,要是在晴天,就能看见它厚重的墙体,锐利似刃的主体建筑棱角,官寨大门上方悬挂的巨大琼鸟雕像,今天雪花飞舞得使它蒙蒙眬眬,看不真切了。走过盆地,来到广场前,大家纷纷下马,进入官寨。
受降仪式在经堂里举行。松罗木向皇上画像磕了三个响头,跪着哭诉:“皇上啊,噩梦今天就结束了,我向岳大人和傅大人拴头,我生是大清的人,死也是大清的鬼。您是文殊菩萨转世的大皇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您知不知道?”在座的头人寨首无一不哽咽歔欷。
“愿佛祖保佑大清江山万万年!”松罗木双手举过头顶,向傅恒和岳钟琪献上一尊金佛,又献上一升黄金。
“这个我收了。黄金留下。我要的礼物是别的。”傅恒接过金佛说。
“大人尽管吩咐。”松罗木说。
“皇上爱慕贵地能工巧匠和善舞美女久矣。”傅恒说。
“我们现在能送的也就是这些了,带多少?”松罗木问。
“各三百吧。”傅恒说。
“大管家,你去准备吧。”松罗木立即安排,并把嘴凑到大管家耳边,细声说,“把阿果也编进去。”
“皇上也想召见你,你也做个准备吧。”傅恒把“押送”说成了“召见”。
“准备好了。”松罗木说,“我本来就想,生不能面拜皇上,死都要梦里叩拜的。”
“不说晦气话了,怎么扯到死上去了?”傅恒想笑一下,可是没笑出来,看来他的心情也不轻松。
“傅大人,我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大土司说。
“请讲!”傅大人说。
“我们这里缺男人,您的兵能不能留下?”大土司说。
“正合吾意。”傅大人说这句话时带着情不自禁的表情。他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征讨这个地方,但接受投降后一走了之他又不放心,这个地方需要有人盯着。于是他本就打算把这些兵作为礼物送给大土司,又担心大土司猜疑,决定过两天再说这件事。
“雪中送炭啊,傅大人!”松罗木学汉人动作,拱手致谢。心里想,他也想过把剩下的兵留下来,难道是让这些人监视我们吗?为何到现在还不相信我们。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什么这么难?
傅恒热衷于改土归流,于是设立了由朝廷直辖的阿尔古厅,后来,改土归流制度在整个嘉绒藏区推行,数千年历史的土司制度至此寿终正寝,松罗木成为嘉绒藏区的最后一个土司。虽然过去万般钟爱千分在意的土司印绶,经傅大人这么一折腾,现在一文不值,不过,他对设立阿尔古厅还是挺满意的,这样才好,免得中间的那些鬼作祟。
阿更现在叫索罗木,父亲把皇帝赐的名字传给了他,却没能把皇帝封的土司传给他,所以阿更不叫土司,而叫守备,是个新名词。土地也不再是土司的了,归阿尔古厅管,由阿尔古厅重新分给种地的人。色齐河两岸的河坝地,大多分给了留下来的官兵,过去各家各户立的地桩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人们一气之下把它拔出来摔得粉碎,不少人搬到色齐部落周围的高山上去了。
这些官兵都是年轻男儿,本地人又大多是孤儿寡母,时间一久,监视人和被监视人便舀一个锅里的饭吃了。这个事儿如果让傅恒将军知道了,他大概会很寒心吧。
留下来的官兵成分很复杂,东南西北的人都有。一开始,语言南腔北调,风俗五花八门,就像石头木块玻璃铜片堆在一块儿,形不成整体,怎么弄都凑不到一块。时间一久,统统融进了本地民俗中,形成被后来的旅行者们称之为瑰宝的色齐河风情。
总之,大色齐部落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大土司的脑子一直围绕一个问题转圈走不出来,就像杨兴的川军和傅恒的清兵走进迷魂沟后走不出来一样。他一直反复问自己,当年带领琼日部落的小伙子们跨入东女国地界,只是为了抢女人,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呢?
傅恒醉心于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一直在此待了两年零两个月都浑然不觉,从大色齐部落出发的工匠和美女们早就抵达京城,被安置在香山。皇上收到傅恒带去的奏折,见到满纸的高兴事儿,十分高兴。一高兴就封傅恒为忠勇公,封岳钟琪为太子太保,并派人催他俩从速返京,他急着庆功。要不是皇上催促,傅恒或许还要折腾下去。
出行那天,留驻的士兵夹道欢送,场面本来够热烈的,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官寨周围各个山头几乎同时唱起了同一首歌:
天空中飘浮着白云,
风儿呀请不要吹散,
天空是白云的家。
草原上蹒跚着羔羊,
鹰儿呀请不要惊吓,
草原是羔羊的家。
河水中栖息着鱼虾,
渔翁呀请不要垂钓,
河水是鱼虾的家。
谁都知道,这是著名的东女国古歌,然而在今天这种场合唱起它时,傅恒一行的凯旋气氛被破坏殆尽,悲壮苍凉的感觉无端地倍增,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天气。”傅恒曾经听过这首歌,现在又听到它时就想起那个山头,想起山下红红绿绿的星点,想起雪夜里密如繁星的火把,心里酸酸的,苦苦的,就想责怪甚至诅咒天气。岳钟琪在傅恒后面,只是干咳一声,没有说话。他是在阿果九岁的时候听阿果唱这首歌的,当时觉得有些奇怪,这么稚气娇嫩的小女孩怎么会唱情感如此凝重的古歌呢?经过这么些年在嘉绒藏区的经历,才似乎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这里的人自古以来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过来的,可能还要唱着这首歌走下去,听,这不是又唱起来了吗?詹姆斯走在岳钟琪后面,听见歌声心里突然一紧,立起大拇指目测到山头的距离,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英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被轰平了那么多的高碉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还唱歌欢送!谁也听不懂他的话,只有他自己知道。松罗木在詹姆斯后面,听见歌声,热泪夺眶而出。从官寨出发时,夫人扯住他的衣袖不许他走。他说,我送他们一程就回,傅将军和岳将军这一走,这辈子不可能再见面了,分别时最后再给他们唱一次东女国古歌。大土司还没来得及唱,歌声便从各个山头飘了过来,他能不感慨万千泪流满面吗?
各个山头继续传来悲壮苍凉的歌声,出行的队伍继续在前进,留驻的士兵继续在夹道欢送。
“请留步!”一位红衣僧人策马奔来,手里举着一样红红绿绿的东西。
“堪布带的,交给皇上。”来人跑至傅恒面前,勒住马头。
那红红绿绿的东西竟是一副琼首神舞面具,傅恒莫名其妙,把它装进马褡里。
这时,人们听见背后半空中传来喊话声,都掉转头看。夫人穿戴一新,站在官寨楼顶招呼松罗木。
“傅大人岳大人,夫人有话要说,我快去快回。”松罗木一边说一边把马头掉回,向官寨奔去。出行队伍停止前进,原地站着等候。
过了一会儿,官寨喷出浓烟,大家都以为松罗木夫妇在煨桑,出远门肯定要煨桑的。但也不对,煨桑应该在楼顶呀,怎么整个房子都在冒烟?又过了一会儿,烈焰腾起,官寨着火了,像火山喷发,熊熊大火染红了半个天空。所有的人都看呆了,竟忘记了救火。救也救不了,官寨是木结构,燃起来就灭不掉。官寨燃了七天七夜,最后只剩下残垣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