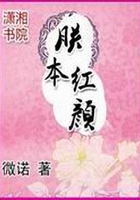“你说……什么?”何老板倏然吃了一惊,抬起眼来,朝谢晚桃望过去。
“何老板,你别装傻呀!”谢晚桃冲他莞尔一笑,“我说,这铺子的租金,我每月给你三两,再多便没有了。”
何老板额头上的汗出得愈加频密,几乎要将手帕浸透:“三两、三两可太少些!别说是现在,哪怕五六年前,平元镇上一间普普通通的铺面,租金也决不至于低到这个地步!何况,二位也都是清楚的,我的铺子无论地段、构造,那都是好得很,头先儿跟你们说定的那个价格,那真是很公道了!小妹子,咱做生意得厚道……”
“何老板的意思,是说我不厚道?”谢晚桃仿佛有点不高兴,一团孩子气地嘟了嘴,“何老板,你这话也太伤人了!我见识短,倒真不知那厚道二字该怎么写,不过想必你心里也清楚,如今你那铺子就如同疫病一般,人人避之不及,在这个时候,我还肯大大方方地租下来,那已经很不容易,很给你面子了!你不感激我,反而数落起我来,我看,你才是真的不厚道呢!”
何老板登时张口结舌,说不出一个字。
何家的日子过得光鲜,这是平元镇上的人都知道的事,但与此同时,大家也都不会忽略一点:这所谓光鲜的生活,全是依靠着何老板的夫人夏氏娘家庇荫得来。这些年,他不知承受了多少白眼,被人在背后戳着脊梁骨地冷嘲热讽,说他吃软饭,他走在街上,无端也会觉得如芒在背,日子着实不好过。
绿柳巷那爿铺子是他多年做小生意攒下的钱买下的,心心念念就想靠着将店铺租出去,多挣些银两,也能在人前挺直腰杆,再不用受那“靠外家”的调侃讽刺。家中出了那样的事,夏如惠整天迷迷瞪瞪,很多时候连他是谁都认不出,原本有意要租铺的人全都跑得一干二净,若眼前这两人肯租,自然再好不过,只是三两……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他赔着笑对谢晚桃和秦千梧低声下气地道。
“没得商量,就三两,再多便没有了。你若嫌少,我也没甚可说,这事就此作罢。”谢晚桃很有点惋惜地摇了摇头。
何老板咬了咬牙,转头求助地看向秦千梧:“秦公子,你看这……”
秦千梧一脸的爱莫能助:“抱歉,租铺子的事,全由我这小妹子做主。我不是不愿帮你,只是实在有心无力。”
“何老板,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谢晚桃不紧不慢地再度开口,“要不要把铺子租给我,那是你的自由,我无可指摘。不过,我若我记得没错,当年你有一位姓罗的小妾,原本怀了你的孩子却意外小产,连小月子都没出,便被人从你家赶了出去,走投无路之际,最终入了勾栏。将你那小妾赶出家门的人究竟是谁,想必也用不着我多说了。如今你家里是乱的一团糟,我真好奇,这事如果再传了出去,会有怎样的后果?”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何老板汗如雨下,这时候却再顾不得擦一下,看向谢晚桃的目光之中竟然添了几许畏惧。
这小姑娘的模样瞧上去一派天真,两只圆碌碌的眼睛里闪烁着明晃晃的光,怎么看也都只是一个孩子,办起事来为何手段竟会如此狠辣?
他忽然觉得很无力,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心口,面上露出一个倦怠的笑容:“便依你吧,三两……就三两,咱现在就把这契约签了。”
“我看,就先签个两年?”谢晚桃看似问询地望了望秦千梧,却并没有等他回答——当然,秦千梧也压根儿就没打算回答,“这两年之内不许涨租,我也不是那起不讲理的人,两年之后,若这绸缎庄的生意好,自然不会亏待和为难何老板。剩下的事,就交给秦大哥与你细办,我先走一步。”
说完这番话,她立刻便站起身来,对秦千梧微微一笑,挤了挤眼,转身走了出去。
店铺有了着落,衣料也都运到,只要再招两个伙计一个裁缝,绸缎庄不日便可开张,谢晚桃方算是搁下了心间的一块大石头。
前世她为了寻夏如惠报那当众羞辱之仇,不知用了多少法子多方打听,将她的底细翻了个底儿朝天,知道她这人表面温婉识礼,实际上却最是善妒,但凡与她夫君有一点关系的女人,她必要收拾得一干二净,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鲜血。
无论是那所谓的“红衣女鬼”,还是在何宅门口见天儿哭叫的老妪,都是谢晚桃让秦千梧去特意找来的,目的也就是要对夏如惠杀人诛心。说起来,这世上的人也真是奇怪,轻易便可害死一个人的性命,却对人死后所化作的鬼魂充满惊惧,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谢晚桃沿着山路缓缓而行,在心中发出一声冷笑。
夏如惠,当初你用那莫须有的罪名辱我,而如今,我用你确凿无误做过的事情来还以颜色,这不仅很公道,甚至可以说,你还占了便宜。你失去的不过是那温婉识礼的形象和名声,明天一早打开门,你仍然能看见那轮红彤彤的太阳,这已经足够你庆幸了。
她一边想着,一边走进谢家院子里,推开西屋的门。
冯氏正在拾掇屋子,见她回来了,连忙迎上前来,拉住她的手腕不无嗔怪地道:“又跑到哪里疯去了?你一个女孩子,成天价不着家,漫山遍野地疯跑,像什么样子?这两日又阴雨连连,要是淋湿了,回头着凉,到时候便又该嚷嚷着浑身难受了!”
谢晚桃亲热地搂住她的胳膊嘻嘻一笑:“娘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也没到处乱跑,就是在陆沧那儿呆了一会儿。再说了,这会子还下着小雨呢,我哥我姐不也没在家老实呆着?要我说,娘就是偏心,见天儿地就只唠叨我一个!”
“你呀!”冯氏又是气又好笑,疼爱地在她脑门上戳了一手指头,“我还不曾仔细教训你呢,你倒编排起娘来了?喏,这两日天雨水多,一早一晚天儿也凉,你爷爷想是吹了风,有些见咳。你也知道他那个脾性是闲不住的,最怕大伙儿把他当病人,死活就是不肯在炕上踏踏实实地歇着。眼下你哥你姐,还有三郎二丫他们,都在上房陪着他说话呢,也算是帮着他解解闷儿。依我说啊……”
“啊,爷爷病了?”谢晚桃眼珠子一转,打断了冯氏的话,“娘,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就去看我爷爷去。”
说罢,立刻撒丫子跑了出去,先到黄木匠家打了声招呼,从他家的枇杷树上摘了两把叶子,然后又奔回谢家,在厨房里倒腾了半天,这才端着一只小碗,小心翼翼地走到上房门口,将脑袋探进去,脆生生地叫道:“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