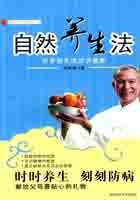夏如惠将谢晚桃从头到脚地看了一个遍,眼神看似温和,却隐含轻蔑之意,并不与她搭腔,径直转身对秦千梧道:“听我夫君说公子姓秦,对吗?秦公子,这位小姑娘是你家里的人?这样小的年纪,生得一团可爱,怎么说起话来却冷森森的?叫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做买卖讲究你情我愿,之前我夫君几次三番地说了,因为我娘家的缘故,不可将这店铺……”
“别废话了,你的店铺我志在必得。”谢晚桃凉浸浸地打断她的话,“反正我是天生的混不吝,玩得起,豁得出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何夫人是娇贵的瓷器,要硬碰我这瓦罐,即使两败俱伤,到最后吃亏的终究是你,该如何行止,还请和夫人仔细思量才是。”
“你……”夏如惠脸色微变,“敢情你们今天是来寻我家晦气的?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道理?”谢晚桃像是听到了世上最可笑的笑话,止不住地抚掌而乐,半晌,方才用利刃般的眼神死死盯住了她,“谁的手段硬,谁就是道理。何夫人娘家富裕,区区几个租钱,你自然不放在眼里,但只怕你夫君,却对这店铺的收入十分看重吧,否则,他也不必着急上火地四处寻买主。你现在将铺子租给我便是皆大欢喜,如若不然,不出五天,我让你这铺子白送也没人要!”
夏如惠杏目圆瞪:“你唬我?!”
“你可以试试。”谢晚桃轻笑出声。
“老刘,送客!”夏如惠目眦欲裂,一拂袖厉声喝道,“我偏生就是不信这个邪,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本领!”
“路是你自己选的。”谢晚桃不待那老头走上前,抢先一步将秦千梧从椅子里拉了起来,“戏开场了,何夫人,希望你尽兴。”
语毕,立刻转身走了出去。
“晚桃妹子,我可否问问,你究竟为何要这样?”
之前谢晚桃和夏如惠对峙时,秦千梧一直在旁边静静看着,始终不曾说话。直到走出绿柳巷,二人在路边停下来,他这才忍不住开了口:“这绸缎庄的生意原本是你的,该如何行事,自然由你做主。只是……你不觉得这样委实有些欠妥吗?”
谢晚桃敛去面上的寒意,回过头去看他,笑得一脸轻松:“秦大哥,妥不妥的,我的确不大懂,不过恕我直言,这绿柳巷你也来了好几次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结果如何?”
“我……”秦千梧语塞,好半天才缓过气来,皱着眉头道,“那你究竟想怎么做?”
“你过来。”谢晚桃冲他招了招手,凑近他耳边,叽叽咕咕吩咐了一通。
“你这个小姑娘……”秦千梧朝后退了一步,“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些?”
“过分?只不过是为了生意,出些小手段罢了,这哪里称得上过分?”谢晚桃闲闲一挑眉,“我真不明白秦大哥为何如此吃惊,我无比笃定,以你的本领,要做这点小事根本是信手拈来,毫无难度。说白了,在你眼中,这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你是何意?”秦千梧目光瞬间转凉。
“真的要我明说?”谢晚桃嘻嘻一笑。
“……我知道了,既如此,就照你说的做。”碍于陆沧的面子,秦千梧无法在她面前发作,好半天,才终于颔首应承道。
“多谢。”谢晚桃冲他一挤眼,一扭头,朝月霞山的方向跑去。
何家的宅子离绿柳巷不远,当天半夜,一个在厨房做事的婆子起身解手,刚刚打开房门,忽听得一阵呜咽悲戚的哭声。
人的年龄愈大,对于鬼神之事仿佛就会愈加相信。这婆子活了五十多年,也算是经历了不少事,饶是如此,在听见那哭声时,她身上仍旧是狠狠地打了个寒颤。
何家的茅房在后院,哭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的。那婆子站在原地愣了许久,原想干脆对其不搭不理,等到天亮再说不迟,无奈实在内急,憋也憋不住,只得壮起胆子慢吞吞走向后院,在心中一遍接着一遍地念咒,希望只是哪个受了委屈的丫头在那里偷哭。
然而,当她拉开通往后院的那道门,所见的却是一副让她魂魄几乎离体的景象。
后院的正中间有一口井,不知什么缘故被弃用了多年,如今是早已枯竭的。借着天空中那一道冷涔涔的幽淡月光,她看见,一个穿一身红衣的女人匍匐在井边,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紧似一声的哀叫,指甲划过冰凉坚硬的井沿,发出咯吱咯吱令人全身绷紧的锐声。
似是察觉有人来了,那女人猛地抬起头,登时吓得那婆子叫了一声。
她的脸上有四五道刀疤,最长的一条,从左边脸颊一直蔓延到右边,横在鼻梁中间。伤疤是早已经结痂了的,变成了深褐色,那张原本应该清秀的面孔,显得狰狞可怖。
“你知道吗?”她咧开嘴,露出森白的牙齿和猩红的舌头,冲那婆子冷冷笑了一下,“我死得好惨哪,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何要落得如此下场?我的骸骨就在这口井里,你帮帮我,让我入土为安,好不好?”
“啊——”那婆子又是一声大叫,双眼一翻,登时厥了过去。
第二天,一个流言在平原镇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祥福裁缝铺的大小姐、何家的二儿媳妇夏如惠,在三年之前,将自己一个名叫做小月的陪嫁丫头,推入井中淹死,在这之前,还残忍地用刀子毁了她的脸。究其原因,也不过是因为她的夫君看上了这个小月,想要将她纳为妾室。
何夫人狠心至此,心窄善妒,竟做下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如今这何家忽然闹鬼,想来是那小月化作厉鬼,来找何夫人报仇来了。
夏如惠得知头天晚上家里闹鬼,心中已然惶惶不安,等到再听到了镇上的传言,便更是支持不住,当即一病不起。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她病倒便告一段落,反而愈演愈烈。每日一到夜深,那红衣女鬼便会在何家宅子里四处奔窜,几乎是所有人,连同那何老板在内,都亲眼看见了她的踪迹,却无计可施,甚至请了和尚道士来做法事,也没有半点作用。
第四天,何家宅子的门口来了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婆。守门人不许她进去,她便扑倒在门口,趴在台阶上一声哀过一声地哭叫,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夏如惠给她的女儿偿命。
有好事者前去觑探,凑到老太婆身边问了两句,得知她便是那小月的亲娘。
那小月是八岁起就被卖进夏家的,谁知道她爹娘长得什么模样?但无论如何,她的出现,仿佛给这传言添加了板上钉钉的力量。
镇上的传言越来越邪乎,原先想要将绿柳巷那间铺子租下来的人,因为怕沾染上晦气,都纷纷打了退堂鼓。
谢晚桃自秦千梧那里,将连日来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地知道个清清楚楚,嘴角浮出一抹得逞的冷笑。
“若我估计不差,那何老板怕是再也坐不住了。明日我随你一同去芙蓉村。”她轻飘飘撂下这句话。
果然,到得第五日,那何老板终于再也无法忍耐,亲自去了芙蓉村,找到秦千梧的家。谢晚桃一早猜到他会来,早早地便等在了那里。
“内人是妇道人家,没有见识,她说的话,秦公子千万不要当真。我知秦公子既对我家里的铺面有兴趣,又那样诚心,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把铺子租给你最是合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还望你二位……”
他话说到一半就住了口,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一个劲儿地擦拭头上源源不绝冒出来的汗。
他又不是傻子,这事儿明摆着是有人故意为之,就为了给他们找不自在,十有八九,与面前这二人脱不开干系,他心中早就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可他能怎么办?难道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们“收了神通”?
大家心中都有数,他素来性子懦弱,未必就有本事能对付得了这秦千梧,倒不如认了栽,将铺子租给他们罢了,让自家铺子早日有了着落之余,也可尽快平息事态,将那些流言压下去。否则,谁知道这些人还能干出什么来?
听了这话,秦千梧还没什么反应,倒是谢晚桃慢慢吞吞地回过头,一脸天真可爱地笑了笑,伸出三根手指,在他面前晃了晃:“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