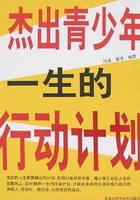一晃数日过去,李月娘做成了一件麻布袍子,针脚细密,裁剪精良,她本来只是想做件披袍,大了小了都无所谓,但那日亲眼见着了白雨松,对他的身高体格心里有了数,就干脆大着胆子做了件袍子。穆清婉去瞧过她的手艺,称赞不已,锦玉却背了人悄悄地告诉她:“李小姐在那袍子里,偷偷地藏了个荷包呢。”
荷包那东西,可不是随便能送的,莫非李小姐对白雨松那位救命恩人芳心暗许了?这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在古代,救命之恩,直接以身相许的不在少数,倘若李白两家门当户对,这倒也是一段佳话,只是以白家的富有程度,只怕是瞧不上以杀猪为生的李家,万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怕李小姐就要伤心了。
因为这个荷包,穆清婉几番想同李月娘谈心,但人家那荷包是偷偷藏的,根本就没告诉她,她若贸然开口,岂不是多事?因此犹豫了好几天,还是把话藏在了肚子里。
又过了一天,李月娘把送给穆家老小的鞋垫也做好了,就连去了乡下的罗姨娘都有份。康氏拿着那鞋垫,很是夸赞了些时候,再看一看自家闺女,又无奈叹气。
这日,穆长光本在衙门当值,特意请假回了趟家,把有关贵人情况的一本册子,交给了康氏和穆清婉,并反复叮嘱她们,要认真看完,仔细研读,免得到时服侍不周,不但拿不到赏赐,反而惹来祸事。
那册子厚厚地一叠,穆清婉凑到康氏跟前看了看,只见头一页上写着,贵人一行三至五人,男女各半,年龄从四十多到二十多不等,仆从数十人,乘车而至,因贵人不喜张扬,接待人员务必不要声张。她请康氏朝后翻了几页,奇道:“怎么没写贵人的身份?”
穆长光道:“贵人此次行事低调,他们的身份,大概只有知县大人知道。”
低调到这种程度?莫非是皇上微服出巡?但大燕国当朝的皇上,还只有十几岁,而这本册子上,年龄最小的,也已有二十出头,看来只是京城一般的功勋贵族罢了。
果然,她所过着的,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穿越小说里那种动辄偶遇天子的奇遇,是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
康氏收好册子,答应穆长光会用心研读,穆长光便又回衙门去了。
康氏对穆清婉道:“等过些日子,就要忙接待贵人的事了,不如咱们今天就陪月娘去白家,向他们家大公子道谢?”
穆清婉道:“娘这主意不错,我们正好去向肖太太请教请教,这贵人所住的地方,该怎么布置才好。”
康氏便让小翠儿去问李月娘的意思,李月娘自从做好衣裳,就盼着去白家呢,焉有不愿意的,当即就跟着小翠儿过来了,问康氏什么时候出发。
康氏寻思着,大家都去白家,独留穆清莲一个人在家里可不好,因此让小翠儿把她也给叫上了。
一行人到了白家,肖太太亲自来接,却把她们引到了校场上,笑着道:“你们来得正巧,我们雨松,正和一位姓聂的朋友比试功夫呢,你们快来瞧瞧。”
姓聂的朋友?穆清婉的脑海中,不知不觉就浮现出聂泰安的那张脸来,待她抬头朝前一看,那正同白雨松打着的,还真是就是聂泰安不假。
校场上,白雨松身着短衣,腰间扎着宽带,一副标准的比武模样,但聂泰安却还是穿着平常的一件旧长衫,只不过把衣襟的一角,扎进了腰带里而已。
这两人,你一拳来,我一拳去,动作之快,让人几乎只能看见个影子,穆清婉虽说不懂这些,但却也看得出,聂泰安并未落败,这发现,让她惊诧无比——聂泰安一个傻子,居然会武艺?!
白雨荷不知何时到了她旁边,指着校场对她道:“我大哥不知从哪里寻来个傻子,非说是他的朋友,可你看他那打法,根本毫无章程嘛,严格一点讲,连拳法都算不上,只是凭着本能出拳而已。”
穆清婉听了她这话,再仔细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聂泰安的打法,和白雨松完全不一样,他是东一拳,西一脚,白雨松打他哪里,他就格挡哪里,简言之,他只是在一味地在防守,并没有进攻。
但是,白雨松是谁?未来的武状元也,单凭能够抵挡住他的进攻,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因而穆清婉对白雨荷道:“聂泰安只是个傻子,能和你大哥比试到这程度,实属难得了。”
白雨荷诧异地看她一眼,道:“你竟替个傻子说话?你们认得?”
她是实话实说,怎么就成了替聂泰安说话了?穆清婉颇感无语,干脆道:“他是我们街坊,就住在我们家那条巷子的巷尾。”
原来是维护街坊邻居,那倒没什么奇怪了,白雨荷想了想,换了个说法:“我大哥连个傻子都没法马上取胜,也真是丢脸,亏他还邀了我们大家都来看。”
这个白雨荷,怎么谁在她嘴里,都不能讨到好去?穆清婉实在见不惯她这副论调,就故意朝四周看了看,问道:“怎么不见二公子?要是二公子下场,肯定三招之内,就把聂泰安给制服了。”
白雨柏?就凭他那副被酒色掏空了的身子,只怕连穆清婉都打不过……
白雨荷尴尬地笑了笑,道:“我二哥又没学过武艺,怎么下场?”说着又懊恼,早知道穆清婉会来,她一定拦着白雨柏,不许他出去鬼混了。
偏这时穆清莲还凑了过来,哪壶不开提哪壶:“怎么不见二公子?”
白雨荷一下子就火了,呛道:“我二哥在不在,关你什么事?”
“我只不过随口一问,你生气作什么。”穆清莲又羞又臊,连忙朝后退了一步。
白雨荷瞪了她一眼,走到旁边去了。
穆清婉看看穆清莲,暗自摇头,这人,居然还挂念着白雨柏,真是死心不改,胆子贼大。
一时校场内比试完毕,乃是白雨松取胜,但他却踮着脚,拍着聂泰安的肩膀道:“泰安兄功夫不俗。”
有什么不俗的,不就会胡乱挥几下拳头么,这谦虚,也太过头了,白雨荷撇了撇嘴,走过来挽穆清婉的胳膊,把她朝校场外拉,道:“清婉姐姐,你今儿来得正好,我们园子里有一株六月柿,已经挂上果子了,我带你瞧去。”
什么六月柿,不就是辣椒么,有什么好看的,等到成熟了,做上一盘辣菜端来,她倒有些兴趣。穆清婉轻柔而坚决地推开她的手,微微笑着道:“我和我娘,还有正事要向你们太太请教,六月柿还是等着再有机会吧。”
“你跟我一样的人,能有什么正事?”白雨荷不肯撒手,她好容易偷偷叫丫鬟去知会黄姨娘,把白雨柏给叫回来了,岂能错失良机。
但穆清婉的态度却十分坚决,见自己摆脱不了她,竟张口叫了康氏来解围,康氏笑着跟白雨荷解释:“我们想向你们家太太请教请教,该如何收拾屋子呢。”
康氏并未明说是贵人将至,但此事白雨荷是知道的,当即惊讶不已——这么重大的任务,穆清婉竟也有份参与?她惊讶过后,转而想到自己,岁数比穆清婉也小不了多少,但肖氏根本没有让她搭把手的意思,显见得这就是嫡出女和庶出女的区别了。她这样想着,心里就酸溜溜起来,撅了嘴,甩着帕子就走了。
“我去劝劝雨荷妹妹。”穆清婉不想看六月柿,穆清莲却想看,匆匆丢下一句,就追着白雨荷去了。
康氏叫了几句,没能叫住,只得随她去了。
肖氏嫌白雨荷没规矩,过来向康氏和穆清婉道了好一会儿的歉,方才领了她们朝厅里去。
到了厅里,分宾主坐下,小丫鬟上了茶点,肖氏把李月娘叫到跟前,仔细打量,问康氏道:“这就是被于家那混小子追着打的孩子?”
“就是她。”康氏想起那日情形,忍不住抹起了眼泪,“真是个可怜孩子,遇上这样的事。”
肖氏也跟着抹起了泪,道:“她还算运气好的,提前得知于家的秉性,把亲事给退了,不然等到真嫁过去,再苦也得自己扛一辈子。”她说着说着,又疑惑:“她爹娘,还没来接她?”
听了这话,轮到李月娘抹眼泪了。康氏小心翼翼地措辞:“许是家里有事,耽搁了。”
再有事,也得把闺女接回去吧,这么大个姑娘了,任由她在外面,就不怕日后婆家诟病?肖氏这么多年的主母不是白当的,一眼看出这其中有问题,不过别人家的事,与她无关,因而也就没有深问。
坐了会子,肖氏对穆清婉道:“你们上园子里逛逛再来,收拾屋子的事,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急不来。”
这便是要把她们支开的意思了,穆清婉当然不会这么没眼力劲,当即拉了李月娘,退出客厅,由丫鬟领着,去了园子里。
一进园门,就见白雨松和聂泰安两人,正沿着小溪散步,聊得十分热络,准确地说,是白雨松兴高采烈地说着,而聂泰安在一旁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