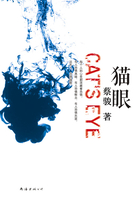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
京都此去任霄城大约几百里路程,慕容缺出发之时,早知会隔五十里备良驹一匹,自己五十里换马一匹,略做停顿,补些水粮,除此之外星夜兼程,恨不能化了弩箭,飞驰而去,省得路上周折。
但陈朵在京都眼线密布,关系网上达天庭,下至贩卒,怎会有他探听不到的消息。慕容缺前行不到百里,就有关卡相候,阻他去路。
那是一片密林,慕容缺驱马行进,渐渐的天色暗沉,下起缠绵细雨来。慕容缺凝神,依稀里听得有马蹄原地踱步的声响,于是拔剑在手,驱了马缓步前行。
只得数步,四下里就有锐器破空声而来,林下微光中,慕容缺承影剑飞舞,一一将之击落,同时也瞧了个分明——十二支淬毒短箭,本属有一面之缘的雁云十二骑。
未及细细思虑,十二匹黑马已自林中现身,内四匹外八匹,围成两轮圆,先是内圈长鞭甩来,鞭如灵蛇,咝咝有声,追着他身周要害。慕容缺踏马而起,剑尖翻飞,方自将那四鞭震落,外圈八鞭却透隙而入,一阵鞭声交错,慕容缺身下坐骑即刻身首异处,整整齐齐被撕成八块。
慕容缺这才知晓,那日对决陈朵,因着主从身份,这白衫黑骑,原来三分力也未使出。
现下缠斗久了,所有绝技施展,慕容缺隐隐领略到这鞭阵威力,原来可守可攻,阵势变幻莫测,暗藏兵家阵法。大约平素操练得紧,十二人配合默契,互补互助,十二份力,倒释放出百份威力来。
慕容缺不敢大意,自保之余,时刻在寻找阵内破绽,但那十二人心念似有根无形绳索栓绑,鞭阵施展,浑如一人长了二十四只手,十二双眼,流转承接,毫无缝隙,而且只守不攻,端是天衣无缝。
起先慕容缺还自诧异为何这鞭阵不使杀招,只是将他围困,斗得久了,鞭上内力雄浑,压迫他呼吸,渐渐的力竭。这才明白,自己气血两虚,遇着强敌不能持久的弱点,对手是清楚的紧。是以鞭上贯注内力,只将他围困,待他内息运转久了,催发伤势,这才使出杀招,力求一击奏效。
心下明了,慕容缺知道不能久战,于是身子凌空,假意内息不继,步法凌乱之余,一卷黄轴自胸口跌落。阵内有人年少气燥,果然上当,鞭改了去向,去卷那黄色卷轴。本密层无隙的鞭阵里,突现了一个天大的破绽。
慕容缺剑光得隙,哪会有丝毫停留,即刻从鞭阵破身而出,威力绽放,如冲破云层的惊雷,袭往那分神之人。
密林昏暗,承影剑本来无形,众人瞧不见,但都分明感应到了那剑意里的凌厉杀气,燕歌行不容多想,从马上踏起,左腕一按,弩箭发出,身子迎往剑尖,遮挡在自家兄弟身前。
“燕七,小心。”他道,那分神之人,显是十二骑中老七。
在这生死关口,人性显露,做不得一点假,他诚意爱惜下属,竟不惜以身代受,倒也是磊磊男儿。
这点心深处的人性光芒,叫持着剑的慕容缺不由三分怜惜敬重,本可夺了燕歌行性命的承影剑,只刺中他右手,叫他此生不能持鞭。回身处,那蓝光弩箭袭来,燕歌行在伤口发力,叫他剑身不得拔出,慕容缺无法,只得侧了身左手夹住箭尖,将它夹为两截。箭尖锐利,在他中指割下细微伤口。
“退!”燕歌行发话,咬牙换左手甩鞭,阻住慕容缺身形,待得众弟兄退去,这才翻身上马,没入丛林。
慕容缺无心追逐,坐骑已被斩杀,只得施了轻功,徒步迈出密林。
出得林来,上到官道,他夺了旁人一匹良驹,只顾朝前扬尘而去。
一两天无恙,无有人拦截,那箭上虽淬了剧毒,但可能伤口太浅,倒也不麻不痒,无甚异样。到了第二天晌晚,慕容缺实在困乏,于是寻了一家乡间野栈,人一沾上床榻,即刻便已睡着。
醒来时,瞧着明晃晃的太阳,他也觉得奇怪,自己向来觉少,这一梦,竟已睡了大半天了吗?起身时一阵眩晕,再瞧床下,赫然一摊血迹,而那不过破了丝线般大小伤口的中指,此刻鲜血汩汩而落,竟似一夜未曾断绝。
慕容缺将身上衣衫扯了一条,紧紧裹住那细小伤口,又点了穴,血势暂缓,但仍不断渗出,片刻后就将布条染红。
此刻旅店外步伐声嘈杂,似是有数十人将他团团围困。燕歌行的声音响起:“旅店杂人都已驱尽,你们只管放箭,他毒已然发作,只需扎上一个小小窟窿,不久就会血尽而亡。”
门外站的,显是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万箭齐飞,密而不乱,一阵扑天尘烟过后,野店早摇摇欲坠,而店内起先还有锐器斩落羽箭的声响,在这三轮箭发过后,也归于沉寂。
燕歌行示意暂停,弓箭手退后,十二骑上人下了马,缓缓步进房内,瞧见慕容缺躺在血泊中,贴近心房处插有一支致命羽箭,身子摇晃,想要站起,却是勉强。
“你功成了,只管取了我性命,去向你主子阿那颜复命吧。”慕容缺闭目,象是放弃挣扎。
燕歌行近前一步,道:“你伤在胸口,三两个时辰之内,怕就会血尽,到时死状极惨。念你前日手下容情,我就给了你个痛快吧。”
这一近前,长鞭还未及甩出,他就已发觉不对。地上血迹虽则触目众多,但颜色浅淡,象是有人在原先有限血迹里加调了水稀释而成。再瞧慕容缺身旁不远处倾覆的水壶,他恍然大悟,急呼身后十一人列阵。
迟了,只迟一步,慕容缺身子迅捷如豹,早扑了上来,翻转他腕,发力处,那弩箭应声射入主人身体。而慕容缺承影剑横置,紧紧贴上了他颈上脉搏。
“退后。”他道,剑逼近燕歌行咽喉半寸,那十一人即刻脸色大变,哗一声让开去路。其中一人最是沉不住气,是燕七无疑,连连摇手。
“别,这毒我们也无有解药,你在他咽喉割一个小口,几日后,他就会没命了。”
燕歌行闻言横扫了他一眼,怨他傻气,慕容缺却自笑了:“你为人仁义,果然兄弟们也顾惜你性命,那好,烦你陪我一遭。”
“劳你兄弟在原地守候,我若发现他们有一人尾随,剑下可就不会容情了。”
言毕胁着燕歌行,跨上那十二骑中一匹,一夹马腹,绝尘而去。
马儿脚程颇快,一路奔驰,只听得风掠过耳际的斯斯啸声。走得久了,约莫一盏茶功夫,马上燕歌行发了话:“这马名叫乌云追,日行千里,你走了这么久,他们是决计赶不上了。”
“怎么,是放了我,还是灭口,拿个主意吧。”
慕容缺勒了马缰,暂缓马速,欲放燕歌行下马,剑方入鞘,燕歌行左手一个长探,将他怀内最要紧的一件物事摸了去。
慕容缺大惊,伸手去夺,燕歌行早翻身下马,两人撕扯之下,绢帛不胜其力,被生拉为两截。
燕歌行瞧了手中一角皇绫,上端正印着玉玺皇印,不由一阵长笑,仰首将那绢帛吞下,朗声道:“上次密林圣旨是假,这次可是如假保换,我看你圣上旨意缺了玉玺盖印,可如何取信于人。”
他行动迅捷果断,慕容缺根本无暇阻止,盛怒下一剑袭来,剑尖离咽喉仍有半寸,但剑气森然冷锐,已将肌肤割出殷殷血来。
“你孤身一人,武艺远不及我,还这样大胆,真是不怕死吗?”
慕容缺厉喝,那燕歌行却自泰然,豪迈之余,隐有三分落索。
“我中了自家无解之毒,日后沙场之上,一点小伤也足以致命,成了废人。报国之心自此全废。死不死的,又有多大区别?”
这话出自肺腑,隐约触动了慕容缺心弦,叫他也是一阵黯然。
同是男儿,站在不同立场,虽是誓死对立,但终难分谁对谁错。
这念想之下,慕容缺收剑上马,回身凝望,一席话,不知是对了燕歌行,还是说于自己。
“报国不成了,也未必要死。”
“家乡故里,你自己小小宅院,总有人念你,痴痴盼你回还。”
终于到达任霄城,慕容缺纵马街头,环顾四周,不由怒意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