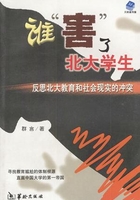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
“只是这酒味太差,难得你锦衣玉食惯了,倒也不嫌。”
陈朵将酒坛放下,只一大口,竟有些微醉:“什么玉食,不过是来日粪土泥沙。所谓锦衣,不过是来日里尸身上裹不住的败絮。”
“酒,好或坏,不都能一醉,又有什么嫌不嫌的。”
慕容缺诧异:“你既无所求,锦衣玉食皆不入眼,那这样苦心营谋,到底图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值得。”
“图什么,说不清,我也不想说。”
“今日里,就图一醉吧。”
陈朵道,接着便是沉默,酒一口口入了肚,情绪却不再受控,慢慢浮上脸孔来。
那是悲伤凄凉,还有自责无望。
在这等滋味里,他醉了,趴在桌角,有泪自眼角渗出,透过指隙,缓缓湿润了桌上朱漆。
慕容缺却自清醒着,他自幼混迹军营,军人气质,酒量本是极佳,这入肚的半坛酒,只能叫他更清醒,更镇定。
这是绝佳机会,慕容缺暗暗靠近陈朵,手按上剑柄。
他醉了,且无有防备,以为自己还是武功尽失。这等斩杀他的机会错过,怕今生都不会再有。慕容缺将剑轻轻拔起,几乎已驾上他颈,却又最终落下。
他扶上陈朵肩头,摇了摇,陈朵挥手:“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慕容缺剑入了鞘,离去多时,他却将头立起,眸里其实还有七分清明。
“慕容缺。”他道,说不清悲喜:“我没看错你。”
然后摇晃着推开桌椅,往那个他其实最畏惧的红墙缓缓而去。
红墙内,有人等他,他的君王,拓拔烈,见着人,一语不发,先将他身上衣衫扯落,没有任何前陈,只是狠狠切入。
不知多久,痛苦才终结,拓拔烈喘着气,意犹未尽。
“这合欢散确实有效,将你菊口收得这么紧,滋味确是消魂。只是苦了你,收得紧,痛得也紧了。瞧这血流的,比上次益发多了。”
陈朵垂首:“奴才不打紧,皇上先歇息片刻,我前日里学了个新花式,稍后可由皇上一试。”
拓拔烈大笑,翻身将他压下:“谁要歇息,新花式,咱们这就试。”
于是两人纠缠,陈朵一味顺从,拓拔烈就将他拆骨拔皮,捻成碎片,他也决计不哼一声,懂得迎合,懂得该放浪时放浪,甚至假装欢愉。
君王终于知足,陈朵勉强立起,方才那姿态冲撞,几乎将他腰骨折断,但他惯于隐忍,没露半点颜色,仍是依着旧历,唤侍女准备,由他亲自服侍洗沐。
在那迷离水汽里,拓拔烈舒泰得几乎睡着,心情难得的好,将眼挑了陈朵发问:“你这等武艺才情,肯委身于我,到底是有所图谋吧?说吧,乘寡人心情好。”
“别来那些虚套,说什么服侍君王,是奴婢几世福德。说真心话。”
陈朵闻言,忙就地伏跪:“奴才已四十有三,现下叛军作乱,平叛主将不力,望皇上应允,许了陈朵平叛。在有生之年,也能建功立业。”
这刻,拓拔烈点了点头,恍惚里,似若有所思。
“功名利禄,天下人图的,无非都是这些,你也不例外。”
“所谓无欲则刚,无所图的人,最难折服拥有。”
“这样的人,我遇着的,便只有他,只有他……”
出了酒肆,在折返路上,慕容缺就觉得有些异样,胃里灼灼烧着,翻江倒海,先是吐,掏空了胃里一切,然后是胃急速抽搐,等那痛蔓及全身,眼前即刻一片黑暗,今日里,第三次短暂失明。
他稳了身形,扶住路边枯树坐下,去摸怀里渡劫散药瓶,却自摸了个空。
这才想起,今早第一次瞧不见事物时,早就将药服尽。
这药,如今已成了吊他气息的救命稻草,缺了,真是连站起的力气也无。
身体里,还有多少潜力,能被这渡劫散激发,支持着活动自如,他已不敢想。练剑的进展,能否赶得上生命逝去的步伐,他也无力左右,所以不去想。能想的,只是如何不似苏菁当日里所言,形容槁枯,让不该伤心的人伤心,最终留下的,都是痛苦记忆。
不知在路边坐了多久,终能瞧见上空云天时,星月早已遍布,苏蔓恰巧寻了来,一路急奔,脸有忧色。
慕容缺立起,等她前来,脚下还是虚浮,于是干脆装了个醉态。
“去了这么久,他没拿你怎样吧?”苏蔓闻见酒气,心已定了八分,扶住他,却仍止不住发问。
“要拿我怎样,还用方才费神救我吗?”
“他心情不好,我赔他喝了酒,两人都醉了,方才在这吐了一地。”
慕容缺答了,由苏蔓扶着向前,苏蔓心事重重,两人一路无语。
返了家,左厢苏菁夫妇已然落灯,原本饭厅连着苏蔓房间,日间被人毁了,当时狼藉,此刻已收拾干净,余了慕容缺的单间,孤零零立在右侧。
慕容缺见状止步,向着苏蔓:“你屋子被人毁了,今日睡我那里吧。我喝了酒,燥得很,正巧在柴房吹吹凉风。”
苏蔓不语,仍扶了他向前,慕容缺手脚无力,只得由着她,一直推开了房门,两人在床榻落座。
起先无恙,过了片刻,苏蔓在床边坐了,慢慢的坠下泪来。
“想听吗?”她道:“我与那人的纠葛,前因后果。”
这里因由,慕容缺早睬得八分,余下的,是外人当不能得知的情感纠缠的细节。
那日千业教里,陈朵在苏莞身体里落了毒,渐渐的她身体萎顿,一日不如一日,最后临终时,被阿那颜一派人将身子拥上圣坛,说是圣女无有后人,圣女之位和圣女血都由资历和根基最深的阿那颜得继。
彼时苏菁和苏父拼着一死,将奄奄一息的苏莞夺回,陈朵在教外出口阻拦,交手中,蓝影剑误入了苏莞身体,那赤子之血透过白衫,落了满地。陈朵心深处终是不忍,纵放他们离去。
苏莞当时没死,怀里,还怀着未成型的苏蔓。这些,陈朵当日并不得知。
苏菁夫妇穷尽医力,也只能叫苏莞诞下婴儿,没能留得住她性命。
“我在娘胎里,受那慢毒侵害,出生时孱弱得似只小鸟,受不得一点风雨。”苏蔓言行至此,哀伤到了极至,但又有一脉温暖,隔了岁月,从回忆里渗出。
“我娘身子不好,神志也不清明,但一直强撑着,直到我被调理好了,能似个正常孩子般吃喝玩耍,那日还突的叫了一声娘,这才离去。
“去时,她跟外婆说。就是天大仇怨,也要压下,让我平静着长大。”
“就长大了,这仇怨也和我无关。”
“没了娘亲的孩子,纵使仇人是自己生父。也要活得快快乐乐,欢欢喜喜。”
“所以。”苏蔓抱住慕容缺肩头,因着有了依靠,感情释放,无所顾忌的泪流:“我有两重性格,本来内向乖巧,但为了娘亲这句话,我得强迫自己欢喜活泼。”
“娘她要我将这仇怨放下,快快活活的做人。但自我十二岁那年无意知道了事实,你说,这仇怨,我还能不能放下?”
“我恨他,没见着时,恨的锥心刺骨。”
“但见了,却又下不去杀手。”
“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最终,苏蔓将这苦痛撕喝了出来,归于平静,慕容缺虽则手足无力,但也咬牙将她紧搂在怀,抚了她一头长发,声声叹息。
苏蔓本是处子,一生里,从未与男子这样亲密接触。这番柔软身子被所爱紧拥,渐渐的呼吸急迫,眸里跌宕起迷离的光亮。
“我将自己给了你吧。就不得厮守到最后,你也得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她道,将唇覆上了慕容缺脸颊,沿着发际线吻起,一直落到了他唇边,一个生涩的无有经验的战栗之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