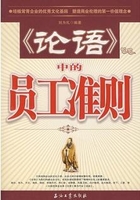!#
舒墨不忍,上前去探她气息,门外有人急呼小心,地上阿那颜却在他回神的瞬间翻身坐起,点了他胸口大穴,然后自腰间抽出八枚金针,送入舒墨身体。舒墨一口鲜血急喷,身子内力道全消。顷刻之间,竟已被阿那颜以渡神劫施针之法废去了武功。
阿那颜自地上站起,仍是一声冷哼,步步逼近阿那然:“我先杀了这贱人,回头再带你回去,舒墨,你该好好想想,你爱的人是谁。”
苏蔓此生,哪见过这样薄情寡义之人,忙俯身捡起阿那颜掉落在地的罗带,护住了阿那然身周。
阿那颜却自一笑,甚至叫了声好,唤门外之人:“阿朵,你寻着了苏菁和圣女血下落,怎么也不知会我一声。落尘丹之毒,唯有圣女血能解。依舒墨所言,这圣女血,就在眼前这女子身上啰。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门外陈朵应声而入,低眉顿首,仍是看不穿有无情绪波澜,人清淡,语声也清淡。
“然表姐,你随舒墨去吧。从此隐姓埋名,忘了自己是谁。”
他淡淡发话,却力有千钧,不容辩驳。阿那颜怒眼相对,他低首,拢了衣袖,微微叹了口气:“就放他们去吧,舒墨已武功全失,就为他曾那样爱过你,放他一条生路。”
阿那然闻言即刻扶了舒墨离去,脚步匆匆,生怕他二人反悔。阿那颜虽心有不甘,但对自己胞弟很是忌惮,只得暗咬了牙,心想这帐来日再算。
两人对持着沉默了片刻,阿那颜心念一转,食指遥对了苏蔓,冷声发问:“阿朵,你背着我寻得了苏菁和圣女血下落,还鬼鬼祟祟不叫我知晓,莫非是想得了圣女血,自己享用?”
陈朵仍是垂首而立,淡淡回应:“我一个婊子,配用那圣女血吗?寻了,自是给你。但若让你知晓,这三人还留得住命吗?”
阿那颜闻言一颤,尖声道:“谁说你是婊子,阿朵,你是我族群英雄,谁敢这么挖苦你,我灭了他满门!”
陈朵摇头:“没有谁说,无需谁说,我本来就是。心甘情愿将自己卖了,还卖给一个男人。”
话语平静,但透着绝望。他走上前来,瞧向苏蔓,没有恶意:“将圣女血留下,你父母和你即刻就得自由,从此和千业教再无瓜葛,我活一日,便保证你们一日不受叨扰。”
然后他转向慕容缺,手贴上慕容缺后背,一股温暖的内息涌入对方身体,叫他痛苦暂缓。
“慕容缺。”陈朵缓缓发话:“你和我不同,你是干净的,因为自始至终,你都不曾遗落尊严。别逃避自卑,如果碰上了,有缘了,你未尝不能重新开始。”
慕容缺扶了门楣立起,回味他话里意味,这是两人间的秘密和默契,共同的苦难,筑就的涩重的友谊,他很感激,从来感激陈朵的善意,但是这点感激,抹不平心中疑虑,他隐约窥见了真相,这真相叫他胆战心惊。
“陈朵,阿那朵,你是柔然国人,还是皇亲,那拓拔烈莫非瞎了眼,居然把你留在身边。”
陈朵轻扶了他,冷冷一笑:“那拓拔烈的是非,又于你何干。他亡国殒命,可不正报了你十数年来被他羞辱之仇。”
慕容缺有些失神,不知如何回应,聂云铮却忽的转身,箭发如电,同指阿那颜和陈朵二人,口中还厉声呼喝:“拓拔烈的国,该亡在我中土人手上,与你等这些柔然蛮子何干!”
阿那颜伸出两指,凌空夹住了白翎箭身,发力将它剪成两段,一段掷回聂云铮心门,一段挡了陈朵眼前箭势,口中啧啧笑着,满是轻蔑:“柔然蛮子?论武功心智,你这中土大侠,哪点比得上?”
聂云铮心高气傲,哪受得了这样羞辱,干脆不闪不避,任由断箭直插胸膛,手上毫不停顿,又是一箭发去,此箭轻灵,用的是巧劲,阿那颜又没料到他会拼死发出箭来,一个大意,被箭贯穿右臂,血流如注。
聂云铮不舍不弃,又凌空发出一枚力重之箭来,势要在阿那颜心门穿个大洞,陈朵一叹,脚下飘拂,去势竟比箭还快,食指在箭尖一点,那箭立刻止步,断为数截。
阿那颜负痛,气急高呼:“阿朵,一个也别放过,包括那什么慕容缺。他前日杀了金叶使,我千里来此犯险,就是因为应承了皇上,要取下此人首级。”
陈朵闻言动容,转身问向慕容缺:“你杀了那金叶使?你可知他是谁?你就没想过,他武功低微,却居此高位,定是别有因由?”
慕容缺回应:“是杀了,他这样为人,我不杀他,也会有旁人想夺他性命。”
陈朵细想后点头:“姐,他贵为长王子,来日继位第一人选,又心胸狭隘,视人命如草芥,你百般撺掇,要他任了金叶使,前来中土建功,就是算定他会有去无回。这番他死了,你如了愿,倒又假惺惺前来帮他复仇,你这算盘,倒是打得响。”
阿那颜冷哼:“无情最是帝王家,我不如此,又哪能生存?你别废话,快取了他性命,我不能在这中土久待。”
陈朵沉默半晌,脸孔逆光,渐有了狠决颜色:“也罢,慕容缺,你杀了柔然国长王子,我是如何也保不住你,不如就此给了你个痛快。”
言毕从袖里抽出一枚短剑来,窄薄剑身,微微泛了蓝光,慕容缺和他相识十数年,却从未见他使过。
他一抬手,意示容慕容缺先出招:“你武功本远不如我,但我敬重你人品,以兵刃相见,这蓝影剑,已二十年没饮过人血,是上古神剑,当不会辱没了你。”
一旁一直不语凝立的苏蔓这刻开了口,森森冷冷,浑不似她:“剑上二十年前最后染的血,是苏莞的吧。可惜,这剑这样窄短,没能一下了断,还留有一段孽债。”
阿那颜好奇,陈朵却是脸色一沉,不讶异,只是心急:“别说,不能说!”
苏蔓颤着双肩,仿似不堪重负:“我不能说什么?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不是要质责你,只是想问问我亲生父亲,你剑上染血,几乎要了我母亲性命,到如今,可心有愧疚?”
陈朵剑低垂了,谜底揭晓,他有些疲累,道:“你何必呢?我在这门外瞧了你,这年纪,这样貌,早睬着了你是谁。”
“有些事,做都做了,愧不愧疚的,又有什么用?我不配你方才那个称呼。你若不说,倒有生机。若说了,就立刻身陷险境。”
阿那颜咀嚼了他们对话里意味,即时恍然大悟:“你是苏蔓和阿朵女儿?阿朵,你莫怪我无情,她断断留不得。前任圣女骨血留存在世,若叫教众和那帮所谓长老得知,我这现任圣女将立足何地?”
“做了她,你反正也绝情过一次,不在乎再多一回。”
陈朵回头,左眉一扬,满是讥诮:“做了她?姐,你当我是什么?婊子,就没有心?就这么眉也不皱做了自己骨血?”
阿那颜不理会这话里沉痛,眼里尽是杀气:“那好,你下不去手,我来。”
陈朵长叹,突然发力,将苏蔓等三人推至门外,嗙一声将房门关却。
“走吧。”他在门里,苏蔓在门外,听得他这样说,虚弱而疲惫。仿佛那门割断的,是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