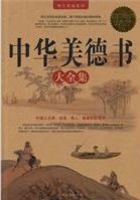!#
梦里,他梦到自己是在荒原雪地里孤身流浪了太久的一匹狼,忽一日春临,自己在温暖的怀抱里睡去,这幸福感觉,叫他锥心刺痛。因为在梦里他也如此清醒,明明白白这只是场梦,终会醒来面对现实的梦。
醒来时,他身子略动,苏蔓已然会意,将他身躯放平,转头向痴了的桓伊,将怀内白玉瓶掏出,急急探问:“这圣药,你服过吗,军内多少人服过,多久服一次?”
桓伊却是痴了,自慕容缺枕着苏蔓肩头睡去,她就一直在这帐下痴站着,整整一夜,还没醒来。
“我不如你,哪桩哪样,也不如你,这样输了,也不算委屈。”她自言自语,根本没听到苏蔓问题,神情竟有些悲壮,有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也罢!”她回身,回复了一贯的飒爽,是要离开帐下,割断这份企盼,却迎头撞上了急急奔来的她的贴身侍从。
“宇文垂受金叶使授意,现已废了东王之位,以他血祭天,正召集大家议事,将军,咱们应该站在谁一边,是不是先该有个主意。”那侍从人颇伶俐,一语指中要害,没半句虚言。
“噢?”她将人引至帐外,怕叨扰了慕容缺休养,边走边是沉吟:“其余三部呢?”
侍从立刻进言:“玄衣部现在受聂云铮统领,他伤重昏厥,醒来后听说慕容将军受了刑,对东王愤慨,但又素来不满金叶使所为,现正中立。白衣部李荣性子憨直,一直信奉千业教,是断不会违背金叶使意愿。咱们若站在东王这边,怕是势单力孤。若从了宇文垂,倒是强弱力判,没什么风险。”
苏蔓内力深厚,在帐内也听闻此言,慌乱中丢下药瓶,疾步来到帐外:“那金叶使叫军内众人服下这使人振奋靡乱的毒药,时日久了,服食的人会久食成瘾,沦为他手中玩物,这等心计,你万万不可助他。”
桓伊听了,自是一惊,将信将疑的瞧了苏蔓,不确信她话里真假。
片刻对峙,帐内却有人揭帘而出,是脸容憔悴的慕容缺,重伤之余,他竟似精力充沛,气息浑厚,伤势已然痊愈。
“在哪里,带我去,桓伊,你愿否助我,若不愿,请保持中立。”他沉声,成竹在胸。
主营帐内,四部统领各带了一队侍从,在帐内对视,显是分了两派,玄衣聂云铮,青衣桓伊,是从了旧属东王。白衣李荣,朱衣宇文垂,是从了金叶使。
聂云铮虽暂时统领了玄衣部,但仍执拗的着一件白衫,脸色苍白,但神情坚定,坚定的是对慕容缺的信仰,方才帐外慕容缺一番话,足确定他拥簇东王的立场。
力量对等,这是场难定胜负的较量,慕容淳被缚了双手,原来在对峙中落败,已被定了以身祭天,这番象是又有了生机,倒也隐约有些英雄气概,将眼对了金叶使,阴沉狠辣,但无一丝畏惧。
“众教。”那金叶使发声,立刻有教众不论立场,投以敬仰追随眼光。他清咳一声,嘴角微微上扬,已有了三分胜算,想着下言,如何带动教众情绪,斜里却突然闪起一道乌光,转瞬已到他眉间,他惊觉,宽袖一拂,身子连同座椅急退三步,那剑却不舍不弃追索而来,内力贯注,一把没入他胸膛,夺了他性命,目标明确,利落干净。
众人哗然,夺取金叶使性命的慕容缺却将剑拔起,抹净剑上血渍,在金叶使怀里摸索,终寻着了一个白玉药瓶。
“圣药?”他笑,剑光过处,挑了帐下一只四处奔窜的老鼠,将药全部强贯入了它口中,片刻过后,那鼠先是极度兴奋颤抖,然后开始疯狂抽搐,在地下倒毙时,已是身子扭曲,死状极惨。
“各位服食的仙药,看清楚,根本是味毒药,若服得久了,服得多了,是会要了性命的。这就是你们信仰的圣教圣使的良苦用心?”
“醒醒吧,列位,这世上哪有什么神明能洗练净化你们的灵魂。”
“你们能依靠的,唯有你们自己而已。”
慕容缺话音未落,帐下已是人声沸腾,有觉得蹊跷上当的,有不肯置信的,那李荣更是急了直挠头皮,望望死了金叶使,又望望死了的老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万千嘈杂声中,青衣部里突然有个尖细嗓音破空而出,那男子抚了胸口,似是刚刚顿悟:“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胸口气急,夜夜潮汗,还常抽筋,莫非是中了毒了?”
话一出,呼应声四起,服了药的军中教众,十有八九都有类似症状,众人惶恐,有的顿足懊恼担忧,有的神情愤慨,至少是对金叶使带来的圣药起了莫大怀疑。
桓伊在这刻将惯使的柳叶双刀抽出,迎空指往正惶恐失措的宇文垂,厉声质问:“人是你迎来的,你又和他贴的最近,莫非你也参与其中,想着推翻东王,毒害军众,叫大家为你药物所控?”
众人本纷乱无有主张,这声厉喝一出,立刻有了泄怒的目标,除了他统领的朱衣部,众人纷纷厉声指责,咄咄要他给个交代,那李荣更是气急,一掌将一张座椅拍烂:“奶奶的,我和你交好,还走了个后门,药服得最多,难怪,我最近夜夜汗出的,象兜头淋了场大雨,你这小子,到底安了什么心?”
宇文垂纵再巧舌如簧,这刻也难说清,正无以应对,慕容淳却已挣脱绳索,直面他而来,扬起双手,示意众人噤声:“宇文将军当日迎金叶使来营,是奉我之命,而他后来种种所为,我想,都是和大家一样,受了金叶使蒙蔽。”
“你说是也不是,宇文将军?”
言落将两束似剑眼光射入宇文垂视野,威严饱含,暗带胁迫。
“正是,多谢东王了解宽容。”宇文垂长袍一掠,单膝跪地,端是个识得时务之人。
营帐外丛林,还保有夏日着了魔似的绿意,但到底是秋,也开始有了萧瑟的势头。
“谢谢你。”慕容淳跟在慕容缺身后,回想方才一幕,余悸仍在心头。慕容缺的果敢谋略,当真是自己不及万一。
“不必。”慕容缺寻了一块青石坐下,语气平和,但到底是疏冷了,没了原先的权权热意:“我想柳云在天,不会允许我看着你去死。”
“这是我欠她的,与你再不相干。”
“东王。”他侧头,甚至是微微笑着,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这情感的羁绊:“看了我后背事物,你想知道,我在这宫内受的凌辱,到底是因着谁吗?”
“因为你,要你活着,干干净净的活着。”他和盘托出,这才发觉,原来真相,远不似想象里那样难以出口。
“你以为我没想过,你这一切,是为了我能活着!”慕容淳听闻此言,象是反被针刺了心窝,言语复又激烈:“这是你的选择,你代我做的选择,你有没有问过我,我愿不愿这样活着,被人凌辱践踏,耻笑欺压,这样不堪的我的黄金年华。”
“慕容缺。”他咬牙:“我恨你恨了一十三年,我是心胸狭隘,谋于算计,我不良善,不懂得体谅你所谓苦衷,不会因你一两句话原谅你。”
“那是因为,没有人教我良善,我在营谋算计,世情炎凉里长大。在那宫里,我要赔尽笑脸,两面三刀的奉承好每一个人,才能得一碗饱饭,得一日安宁。我这样长大,我没有选择。我愿做七岁前的慕容淳,我愿在那刻死去。”
“对不起,你代我所做的这个活着的抉择,我不领情。”
他说完了,憋了一十几年的心头怒气,恨的根源,不是没有可怜之处,慕容缺有些神伤,但不再盲目:“淳儿,痛苦,不该是你恶的理所当然的借口。”
“我错了,不该把你捧上这高位,在权欲的漩流里,看不清自己。”
“以后的路,你自己走。”